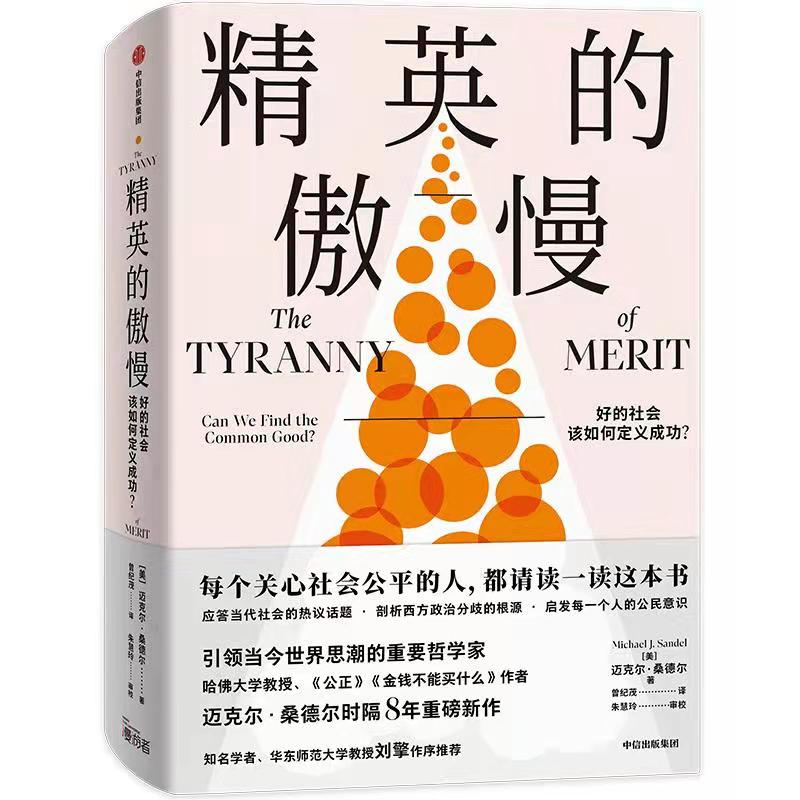
《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
[美]迈克尔·桑德尔著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大学文凭是通向成功的敲门砖吗?赚钱越多的工作,对社会贡献越大吗?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社会,就是公正的吗?当公平的假象造成撕裂与对立,跟随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中重新思考教育的目的、工作的价值与成功的定义,是每一个社会和个体都需要经历的思辨。
>>内容摘编
技术官僚治国与亲市场的全球化
这一失败的核心是美国主流政党在过去40年中构想和实施全球化的方式。全球化的实施在两个方面助长了民粹主义者的抗议:一是构想公共利益的技术官僚方式,二是用优绩至上的方式界定赢家和输家。
技术官僚对政治的理解与对市场的信仰紧密相连——后者倒不一定是不受约束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更广泛的信念,即市场机制是实现公共利益的主要工具。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样思考政治的方式是技术官僚的,因为这种思考方式把公共话语争论中的实质性道德内涵掏空了,把意识形态上有争议的问题当作技术专家处理范围内的经济效率问题来对待。
技术官僚对市场的信仰为民粹主义者的不满搭建了舞台。市场驱动的全球化模式造成了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还贬低了国家身份和政治忠诚的价值。随着商品和资本跨国界自由流动,那些站在全球经济之上的人将世界主义身份视为进步、开明的选择,以替代狭隘的保护主义、部落主义和冲突。他们认为,真正的政治分歧不再是左派对右派,而是开放对封闭的。这意味着对外包、自由贸易协定和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的批评是封闭的心态而不是开放的,是部落式的心态而不是面向全球的。
与此同时,技术官僚的治理方法将许多公共问题视为普通公民无法触及的技术专业知识问题。这缩小了民主辩论的范围,掏空了公共话语的内涵,并让普通公民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被剥夺权力之感。
这一转变起源于20世纪80 年代。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曾辩称,政府才是问题所在,而市场是解决方案。当他们离开政治舞台时,接替他们的中左翼政治家——美国的比尔·克林顿、英国的托尼·布莱尔、德国的格哈德·施罗德——对市场的信仰虽然温和了一些,却更牢固了。他们软化了不受约束的市场的严酷刀刃,但没有挑战里根-撒切尔时代的核心预设——市场机制是实现公共利益的主要工具。本着这一信念,他们接受了有利于市场动作的全球化,并欢迎经济的日益金融化。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与共和党联手推动全球贸易协定, 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这些政策的好处大多流向了顶层人士,不平等日益加剧,金钱的力量在政治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但民主党人在解决这两个问题上几乎都无所作为。自由主义已经偏离其传统使命,不再驯服资本主义,不再让经济权力掌握在民主力量手中,失去了鼓舞人心的能力。
当巴拉克·奥巴马参加2008年的总统竞选时,他说出了一套激动人心的话语来取代技术官僚的管理语言,后者当时已经成为自由主义公共话语的典范。他证明了进步政治可以说出一种表达道德和精神目的的语言。
但奥巴马作为总统候选人所激发的道德能量和公民理想主义并没有延伸到他的总统任期。奥巴马在金融危机期间就职,他任命了若干经济顾问,这些人曾在克林顿执政期间推动放松金融管制。在这些经济顾问的鼓励下,奥巴马对银行予以纾困,但既没有让银行对它们导致危机的行为负责,也没有为那些失去家园的人提供多少帮助。
奥巴马的道德声音减弱了,他尽力平息了公众对华尔街的愤怒, 而没有在政治上更明确地表达这种愤怒。对银行救助计划挥之不去的愤怒,给奥巴马的总统任期蒙上了一层阴影,并最终激发了民粹主义者的抗议情绪。这种抗议情绪波及了各个政治派别——在左翼表现为占领运动和伯尼·桑德斯出来竞选总统,在右翼表现为茶党运动和特朗普当选。
在对再次赢得公众支持重燃希望之前,这些政党需要重新考虑其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官僚执政方式。他们还需要重新思考一些更微妙但同样重要的东西——近几十年来伴随不平等的加剧产生的对成功和失败的态度。他们需要问一问:为什么那些在新时代经济中遭受损害的人会觉得胜利者在蔑视他们?
阶层跃升的话语
那么,是什么激起了许多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选民对精英阶层的怨恨呢?答案始于近几十年来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但并不止于此。广泛的怨恨,本质上与社会认可和尊重的界定发生了变化有关。
至少可以说,全球化时代的回报很不均衡。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国收入增长的大部分都流向了收入在前10%的人,而收入居于后50%的人在这几十年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按实际价值计算,处于工作年龄的男性的年收入中位数约为36000美元,低于40年前的水平。如今,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其收入比收入居于后50%的人的收入总和还要多。
但即使是这种不平等的爆发,也不是民粹主义者愤怒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容忍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认为无论一个人的人生起点是什么,他都有可能从贫穷变得富有。这种对向上流动可能性的信念是美国梦的核心。
基于这一信念,主流政党和政治家以呼吁更大的机会平等来应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对因全球化和技术更替而失去工作的工人进行再培训,增加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消除种族、民族和性别障碍。这些关于机会的花言巧语可以被总结为这样一句口号: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应该能够“尽其所能”向社会上游前进。
近几年来,两党的政客都反复强调这一口号,简直到了念咒的地步。共和党人中的里根和小布什,以及民主党人中的克林顿、奥巴马和希拉里都援引了这一口号。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他在演讲和公开声明中运用这句话超过140次。
现在,阶层跃升的话语听起来很空洞。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实现阶层跃升并不容易。出生于贫穷家庭的美国人在成年后往往会一直贫穷。那些出生在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人中,只有大约5%的人能够进入收入最高的10%的行列,大多数人甚至成为中产阶级都做不到。在加拿大、德国、丹麦和欧洲其他国家,摆脱贫困比在美国更容易。
这与长期以来认为流动性是美国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答案的信念不一致。美国人告诉自己,美国可以比欧洲国家的阶级社会更少地担心不平等,因为向上流动在这里是可能的。70% 的美国人相信穷人可以靠自己摆脱贫困,而只有35%的欧洲人这样认为。这种对流动性的信念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福利制度不如大多数欧洲国家慷慨。
如今,流动性最高的国家往往也是最平等的国家。向上流动的能力似乎更多地取决于获得教育、医疗和其他资源,而不是来自贫困的鞭策,这些资源让人们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成功。
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的激增并没有加快向上流动的速度,相反,不平等加剧让那些处于顶端的人能够巩固自己的优势,并将这些优势传给子女。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名牌大学消除了种族、宗教、性别和民族的入学障碍,此前,这些名牌大学只限于特权阶层的子弟入学。SAT 的诞生源于这样一种承诺,即根据学业成绩而不是阶级和家庭出身来录取学生。但今天的优绩至上几乎已经变成了世袭贵族垄断。
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2/3的学生来自美国收入最高的那10%的家庭。尽管有慷慨的经济援助政策,但只有不到4%的常春藤联盟高校学生来自收入最低的那20%的家庭。在哈佛大学和其他常春藤联盟高校,来自收入最高的那1%家庭的学生比来自收入最低的那50%家庭的学生加起来还要多。
美国人认为,只要努力工作,发挥才能,任何人都可以出人头地,这种信念已不再符合现实。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关于机会的花言巧语不像过去那样鼓舞人心。流动性不再能补偿不平等。任何对贫富差距的严肃回应都必须直接考虑到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而不是满足于设计方案帮助人们爬上梯级间隔越来越大的梯子。

▲作者迈克尔·桑德尔是引领当今世界思潮的重要哲学家,《公正》《金钱不能买什么》作者,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公开课老师。
作者:迈克尔·桑德尔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