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由外国人写的中国年轻人生存状况的纪实作品。
一个刚毕业的美国毛头小子,只身一人来中国闯荡,出没于成都、苏州等新一线以及二三线城市,还走访了部分农村地区,与大量的中国年轻人做了深入交流,真切地了解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生活、工作和精神状态。
在他看来,这一代的中国年轻人所生存的是一个快速腾飞的中国,他们比以前更自信、更有活力、更有个性也更具有创新视野。但正所谓,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快乐和哀愁。
面对新旧转换和呼啸而来的时代浪潮,这些年轻人身上同样也背负了巨大的压力和期望,他们想要不一样,想要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但现实却很可能让他们的梦想戴上巨大的镣铐。
但不可否认的是,后浪奔涌,正是这些新新人群,已经开始走向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中心,他们正在改变着中国,甚至有可能改变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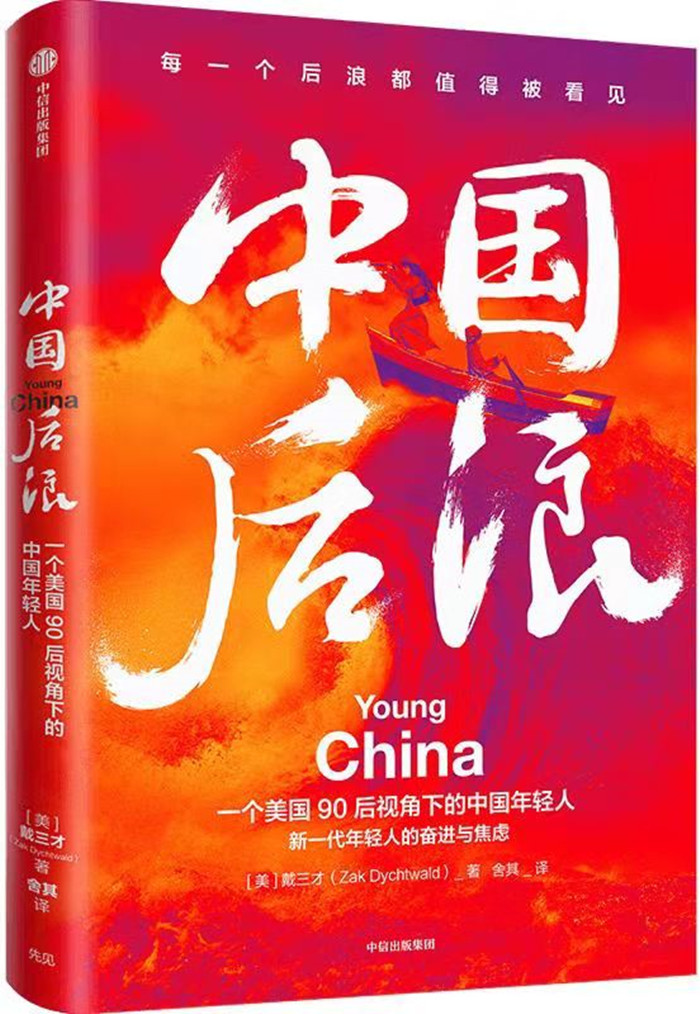
《中国后浪》
戴三才(Zak Dychtwald)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中国年轻人和美国年轻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自《中国后浪》(英文版)出版以来,这是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我在写作和完成本书时,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叙事性非虚构作品会有意地“接地气”,对我来说,也许我跟细节、跟人、跟故事都太贴近,因此反而不识庐山真面目了。
直到我回到美国,重新卷入国家认同危机的旋涡,答案才终于浮出水面。在美国,我们刚开始接受这样的想法:“亲身经历”会剧烈影响你的实际情况和世界观。以种族、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为基础,不同美国人的亲身经历有着天壤之别。正是通过这样的天壤之别,我们才了解到上面的想法。
类似地,也正是中国年轻人的亲身经历塑造了他们独特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与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年轻人,包括我的家乡美国的年轻人,都截然不同。具体来讲,是快速变化的生态系统塑造了中国后浪。他们以“中国速度”成长起来,快速变化的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全国十几亿人的三观中。
“中国速度”影响下年轻人的世界观
我们说到中国速度的时候,一般都是在说建筑。2011-2014 年,中国浇筑的混凝土比美国整个20世纪浇筑的还要多。变化最明显的要数上海浦东,20世纪90年代初期,那里还没有高层建筑,而现在的浦东遍地高楼拔地而起,在古老河流的映衬下闪闪发光。
但是,从来没有人讨论过以中国速度成长对心灵的影响。就跟外滩的河岸一样,这样的直线增长是如何塑造这代年轻人的心灵风景线的? 我说以中国速度增长在全球都独一无二,就真的是独一无二。考虑一下我想在这里提出的“生活变化指数”,这个衡量标准跟踪的是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在人一生中的变化幅度,比较世界各地在同一时间出生的人一生当中经历的经济变量。
作为美国的 90 后(我出生于 1990 年),我经历的人均 GDP 增长约为 2.7 倍,紧跟在我们后面出生的就是数字土著一代,他们只知道数字世界。首先是互联网——我还记得用我们家电脑拨号连上“美国在线”的声音;接下来是手机——世贸双子塔在“9·11”袭击中倒下之后,父母给11岁的我配了第一部手机,这样我们就能随时保持联络;再到智能手机、社交媒体、手机银行、电动汽车、大数据、可再生能源,还有即将到来的基因治疗和太空私人旅行。跟我作为美国千禧一代经历的2.7倍增长相比,中国90后见证的人均GDP增长是32倍。过去30年间,中国这个世界比我那个世界的发展速度快了整整一个量级,这个世界的环境也有如猛湍飞瀑,奠定了他们对家庭、政府、技术、工作、金钱、旅游、食品、童年和变化的态度。
中美过去30年生活变化指数上的巨大差距,并不代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1990年以来,全世界大部分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年轻人,都经历了跟美国水平相当的增长。比如说,1990年出生的印度人经历的GDP增长是5.7倍,而同一年出生的巴西人经历的GDP增长则是2.8倍。即使放眼全球,中国也毫无疑问是一枝独秀,独领风骚。
如果你是1990年出生的中国男性或女性,想象一下这种变化在个人层面上的影响。你出生的中国距离中国改革开放不过十余年,你的父母都在一个农业社会和落后的经济体中长大,而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的村庄变成了小镇,小镇又变成城市,后来又变成了大城市。你还记得你叔叔因为在工厂工作,买了一辆崭新自行车时得意的样子。要不就是,你离开了自己的小村庄,在那里,你的祖父母很可能比你矮了整整一头,因为他们长大的过程中都没吃过饱饭。你搬到了大城市,想找一份计算机编程的工作。在这座城市里,不断流动和扩张已经成为常态。
中国千禧一代出生在一个人均GDP只有300美元的国家,大部分家庭都没有冰箱,家用电脑就更别提了。在30 年间他们见证了一个世纪的变化,这为他们奠定了与世界上其他行动缓慢,有时还走得跌跌撞撞的同龄人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如今,他们的现代生活滚滚而来,与美国人并驾齐驱:互联网,手机,智能手机,社交媒体,手机银行,电动汽车,大数据,可再生能源,还有即将到来的基因治疗和太空私人旅行。
20 世纪90年代初是中国的一个拐点。出生在那个时代,就意味着你只能不由自主地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中演进。90 年代中国剧变的帷幕真正拉开时,邓小平,这位中国现代经济的总设计师,用一句话总结了这个国家的改革开放:
摸着石头过河
外国人很喜欢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表达了中国政府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务实态度,但是很少有人想到这句话向中国人民传达的信息。这是邓小平在用一种古典美的方式告诉这个国家:“我们一边摸索一边前进。”这句话当中还暗含了一层意思:我们难免会跌倒,也准备好了要犯错误,在这些不确定因素出现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成功应对。对中国的十几亿人口来说,过去30年的快速变化带来了同样的信息:要么适者生存,要么大浪淘沙。
中国过去30年的心理环境的独特之处,在中国国内很难充分理解,因为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已故的戴维·福斯特·华莱士曾于2005年在凯尼恩学院的毕业演讲中讲了一个故事。故事里有三条鱼,一条大鱼,两条小鱼。大鱼游过小鱼身边时向它们点头致意,随后说道:“早啊年轻人!你们这儿水怎么样?”两条小鱼又游了一会儿,其中一条才说道:“见鬼,水是什么?”
在塑造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思考方式时,我们的环境有重要作用, 但我们往往都习焉不察。对这整整一代人的人生来说,中国的生态系统在持续、快速变化,这变化有时让人着迷,有时又冷酷无情。
所以说到中国速度的时候,我可不是在说制造业的快速升级。制造业升级也挺牛的,在与日新月异的中国有关的讨论中,这个话题也有其分量。不过,我要说的是4亿多中国千禧一代身在其中的,从全球来看都毋庸置疑、绝对独一份的生态系统——一个按自己的步调前进、以直线速度增长演化的生态系统。那么下一个问题是,中国速度如何改变了中国年轻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中国年青一代与老一代又有什么不同?
世界为什么要关心中国后浪?
世界为什么要关心中国后浪?对地球村公民来说,答案很简单:影响力。中国千禧一代约有 4 亿人,是美国千禧一代的5倍。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的数据,中国年青一代比北美、欧洲和中东三个地方的年轻人加起来还要多。
但是,当世界说到中国时,我们关注的经常是过去:老成见、老政治、老传统、老一辈人。中国的年青一代正走向成熟,他们已经开始引领这个国家强大的经济和政治未来。中国年轻人已经开始影响甚至是定义了他们进入的所有市场,影响了美国人、欧洲人、非洲人以及他们本国同胞的生活。
除了影响力,定义中国年轻人的还有四个主要的“大局”变化。我相信其他方面会在未来几年变得更加突出,尤其是在创新方面。
首先,跟中国老一代相比,年青一代思想开放,也乐于接受外部世界。中国老一代是在一堵文化的高墙背后长大的。我朋友欢欢1990年出生于四川——跟我同年。他父母还记得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村里人经常会挤进他们邻居家破败的房子里,因为房子的土墙上钉着一份挂历。这12张图画(欧洲田野)是村里人对外面那个世界的唯一视角。
而中国年轻的千禧一代,是在观察外部世界的过程中长大的。他们是数字土著。欢欢和他的同龄人都上过十年左右的英语必修课,他是在看美剧、追赶西方时尚、关心西方政治的过程中长大的。我在中国的很多朋友都可以随口说出美剧《老爸老妈的浪漫史》中巴尼的台词,以及马丁·路德·金的名言。
他们也不只是从遥远的地方了解世界。中国年轻人正在越来越多地亲眼看到外面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给全球旅游业带来了一波波振荡。在中国,持有护照的人中有三分之二不到40岁。尽管只有约9%的人拥有护照,中国还是代表了世界上最大的出境游市场,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千禧一代这些人推动的。中国持有护照的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多出1400万护照持有者。美国已经不再是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旅游市场,旅游业必须开始迎合中国。
中国年轻人的第二个决定性特征,是他们白手起家的故事。我有个朋友的父母来自贵州,他们告诉我,在困难时期,他们为了不饿死,还吃过树皮。可资比较的是,同一时期,也就是1969年, 我父母心里想的却是前往伍德斯托克,那里有以性、毒品和摇滚乐著称的音乐节。1990年以来,美国的人均 GDP 增长到原来的2.5倍,这是质的跃升。但在同样的时间跨度里,欢欢看到自己国家的 GDP 增长了30多倍。中国的年轻人在他们的生命中见证了一系列有形的、个人的巨大变化——从乡村到城市,从自行车到小汽车,从板楼到高楼大厦, 而这些变化必然也塑造了他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
第三个特点是,4 亿人之众的“中国年轻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由他们的人口学命运决定的。跟老一辈相比,千禧一代的人口相对较少。这么大的群体,怎么会被认为人数很少呢?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每个家庭平均有五六个孩子,平均预期寿命据估计低至 36 岁。中国那时候的人口结构就像金字塔,底部是年轻人,很宽,顶上是老年人,很尖。中国传统的退休制度依赖于自己的孩子,也就是反哺模式,在兄弟姐妹众多可以帮助赡养年迈父母的情况下,相对来说是可持续的。不过,很多人还是等不到退休就去世了。
今天,中国面临的人口挑战可能会毁了年青一代的未来。金字塔正在倒转。财富增加已经转化为寿命延长,中国老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 76 岁。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意味着今天跟老人相比,年轻人的数量相对较少,往往会形成“四二一”家庭——一个孩子,两位父母,四位祖父母。
中国的经济制造业奇迹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口结构,有很多人做了很多廉价的工作,加上任劳任怨的态度和多劳多得的新制度。中国这代年轻人是独生子女群体,他们不会也不可能给这个世界生产衬衫。
这代年轻人,推动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创新。他们也知道,要么更有创业精神,创造更有价值的就业机会,要么就会在老龄化人口面前败下阵来。这一代崭露头角、坚毅果敢的企业家,将在世界舞台上与美国的创新者一较高下。像微信这样的已经拥有10亿用户的应用,技术上已经比美国提供的应用更加先进。不用退出微信,你就能使用脸书、Instagram(照片墙)、Skype(网络电话)、WhatsApp(网络信使)、Yelp(点评网站)、Venmo(支付应用)、ApplePay(苹果支付)、Groupon(团购应用)、优步、亚马逊等林林总总一大堆应用所具备的各种功能(还包括:干洗,转比特币,预订 KTV 房间,找代驾,等等),所有这些都在同一个超级应用里面。有些青年企业家——尤其是程序员——已经开始产生影响,比如 22 岁的勾英达就创立了一家电商公司“野农优品”,意在将农民和城市居民联系起来,由前者为后者提供绿色农产品,也让农民可以判断产品需求,优化作物产量。整体上看,O2O 模式(线上到线下)也许会促进中国农业产业的变革,并缩小日益加剧的城乡之间的分野。
没有能力照顾老人不仅会从经济危机转变成政治危机,还会造成精神危机。照顾父母,是中国人看重的“孝道”的题中应有之义。做父母的好孩子就等同于做一个“大写的好人”。这代年轻人渴望照顾父母但又几乎完全做不到,因此深受困扰。
很多人都说这群独生子女是“小皇帝”:受到太多关注,被宠坏了。但跟关注一起来的,还有几乎无法想象的压力——考上名牌大学,事业有成,结婚生子,最后能养活整个家庭。虽然确实有些人被宠坏了,但也有很多中国年轻人觉得自己被关注和期望压得透不过气来。中国年轻人花了更多时间上学,力图在竞争极其激烈的教育和就业市场上得到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竞争优势。目前在美国留学的外国学生,三个当中就有一个来自中国,而且绝大部分都是自己全额支付学费。短期内,美国大学的业务会因为中国千禧一代得到巨大提升,但长远来看,这些受到良好教育的学生会回到自己的国家,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
第四个特点是,他们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中国千禧一代见证了他们的国家以人类历史上未曾经见的速度和规模摆脱了贫困。1990年,中国的教育系统开始关注中国的历史成就。这种新的教育方式,再加上这个国家近些年的异军突起,给了他们很多自豪的理由。
他们强烈的自我意识,对以前“现代化”就等于“西化”的观念带来了冲击。有趣的是,跟西方大国的互动越来越多,反而让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不再那么迷恋西方的社会格调。
这代年轻人渴望“自由”。千禧一代把这个词文在胳膊上,写进音乐中。但是,他们期待的自由并不像大部分西方人所期待的那样是从政府的压迫和束缚中解放,很多人都是在寻求从传统期望——到 一定年龄就得结婚,要买了房才能算是“合格”的单身汉,对“成功” 的定义也只围着物质上的收获打转——的压迫和束缚中解脱出来。
现在的年青一代被夹在两座大山中间,一边是父母从传统观念出发对他们的殷切期待,另一边是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压力。比如说,女孩子会听到别人说,她们得花更多时间追求更高的学历才能出人头地,但要是婚结得晚,或是压根儿不结婚,就会被称作“剩女”。男孩子会听到别人说,要赡养父母,要给他们生个孙子,但是在“有资格结婚”之前他们得先买套房,所以到头来成了从父母和祖父母那里举债,而不是赡养他们。他们身上的标签是“啃老族”。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这代年轻人是第一代大体上不用考虑“我们家今天吃什么”这种生存问题的人。实际上,他们这代人在问的是:“我对自己有什么需求?我的家人呢?我的祖国呢?”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在他们这里从生存问题提升到了自我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叫他们“躁动的一代”——定义当代的身份认同绝非易事。
中国年轻人是有强烈个性的一代,他们也是第一代能够决定中国人在现代世界中意味着什么的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最早开始为写作本书找材料的时候,中国互联网上一度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就是“屁股决定脑袋”。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坐在什么地方,每天都有什么人围着你,你对自己周围环境和人、事的看法, 你成长过程中听到过的各种唠叨,都会决定你的世界观,对你的影响会比你自己愿意承认的大得多。
通过本书,我希望帮助外面的世界看清楚,从中国内部看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也希望让中国人了解一个外国人的看法,因为这个人努力尝试深入了解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民,这里已经是他的第二故乡。
——摘自《中国后浪》,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作者:戴三才(Zak Dychtwald)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