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中国文坛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就是一批30后、40后、50后作家不约而同地拿出了新作,比如王蒙的长篇《笑的风》,赵本夫的长篇《荒漠里有一条鱼》,贾平凹的长篇《暂坐》《酱豆》,莫言的小说集《晚熟的人》,张平的长篇《生死守护》,徐贵祥的“英雄山”系列《穿插》与《伏击》,冯骥才的长篇《艺术家们》,王安忆的长篇《一把刀,千个字》等。
曾经的文坛“黄金一代”集中推出新作,这不能不引起业内外的广泛热议。一方面,放眼世界文学史,很多重要作家都在自己的晚年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歌德82岁完成《浮士德》,雨果72岁完成《九三年》,汪曾祺、孙犁、巴金等也都是在晚年的写作中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审美可能性;另一方面,出于种种原因,中国当代文坛少见晚年写作,而此番集中推出新作的作家们,又都是在盛年时期就拿出了最具知名度的作品而因此被视为“黄金一代”,比如莫言31岁发表《红高粱》、徐贵祥41岁完成《历史的天空》、贾平凹41岁出版《废都》……如今,他们有可能为中国当代文坛补上晚年写作这一序列吗?
可持续的写作必须走出舒适区吗?

许多人都认为,晚年写作的价值,很大程度来自作家所表现出的可持续的写作能力。不过,对于什么是可持续的写作能力,学界和评论界的看法并不一致。
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岗看来,能不能形成像萨义德所说的那种晚期风格,即在晚年写作中释放出年轻的活力、体现出更高的创造,是衡量一个作家能不能写出更好作品的标准。他以阿特伍德和麦克尤恩为例,二者都是在七八十岁的年纪推出了元气淋漓的、适应新媒体时代的新作。
罗岗认为,已成名的作家“一定要敢于尝试新的变化,敢于去处理一些不那么驾轻就熟的东西,即便不成功,也是好事”。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作家“衰年变法”,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这不仅关乎能力,同时考验作家的自律,也考验作家周围的评论生态。毕竟成名带来的好处能够让一个作家沿着惯性滑行就可以过得舒适安逸,而我们的文学评论也习惯了对名家过于宽容。他以贾平凹为例,在他看来,贾平凹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作家,有自己看待世界的独特眼光,但是他的每一部新作问世之后得到的都是“交口称赞”,这就会导致他失去对自我的正确认知和评价,从而妨碍他的自我突破。
而在评论家贺绍俊、郜元宝看来,有些作家天生对环境的变化非常敏锐,能够感受到新的东西,并且在自己的写作中体现出来,这当然很好,但如果一个作家本身的审美习惯已经固化,那就不如让他们在自己的惯性里做到极致。虽然对他们个人而言,这样的写作看上去缺少变化,但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来说,则会构成整体的多样性,展现出丰富的文学图景。“世界这么大,意味着文学也非常大。”
具体到对几位作家新作的评价,贺绍俊说,就自己看过的几部而言,“不低于他们以前的创作水平”。郜元宝认为,贾平凹的《暂坐》延续着《废都》而来,《废都》描写的是中年人的苦闷,《暂坐》则试图表达一种老年精神的淡定,虽然现在很难判断是否成功,但还是有值得关注的变化;而赵本夫的《荒漠里有一条鱼》则延续了他一以贯之的写作风格,即在一个卑污不堪的环境中展现人的高贵品质,同时又展现出了全方位的进步,挥洒自如地进行了很多浪漫主义、异想天开的描写。
今天的阅读市场需要晚年写作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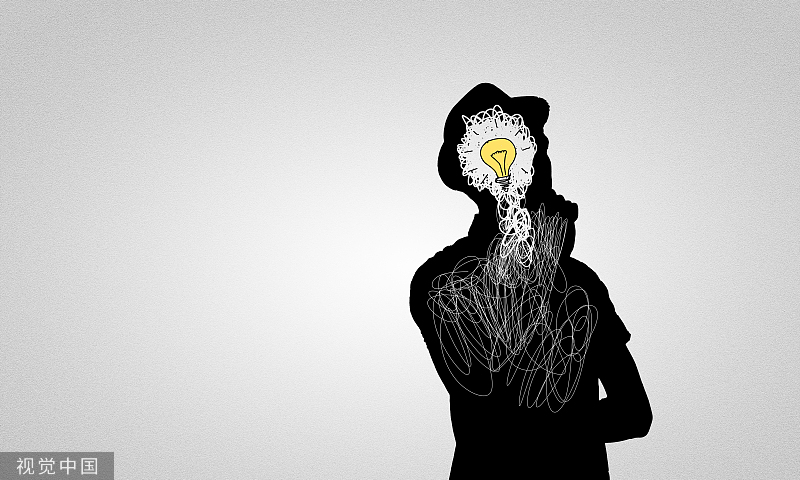
正如一些评论家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最近几十年,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和阅读风向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40后、50后作家,甚至一些60后作家,尽管也在尝试一些新的叙述手法,但他们的关注对象和对世界的看法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过去,势必难以在今天的主流读者中产生共鸣。如果失去了读者,这样的写作还有没有价值?
“当我们讨论读者是不是已经对这一代作家的作品失去兴趣的时候,首先要厘清的是:我们指的读者是谁?”在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看来,文学的阅读已经分圈层了,每一类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不能因为读者不交叉,就认为某一类写作失去了读者。在此基础上,何平认为,当作家进入人生的暮年,会因为稳定的价值观和丰富的人生经验而拥有独属于他们的对世界的把握和感受,这是他们能够提供的最重要东西,是他们在当代文学谱系中所具备的独特价值,无法被替代。也正因如此,晚年写作,或者说成熟写作,从来都应该是一个时代文学里的重要构成。
郜元宝借杜甫的诗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向记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从这个视角出发,即便是那些看上去有些“瞎闹”的写作,也并非没有价值。就写作者而言,青年时的清澄热忱、中年时的理性平衡、暮年时的放飞自我,都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光景,都有值得被倾听的一面;就阅读者而言,“中国文坛一直缺乏老年人写给老年人阅读的作品。然而一个社会的文化产品不能由某一个年龄段单独构成,老年人的想法和感情不被文艺的主流市场关注,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纠正的现象。”
作者:邵岭
编辑:范菁
图片:视觉中国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