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七九年秋天,我以记者身份去四川成都参加“全国生态会议”。一位戴着小白遮阳帽长得像带学生去野外考察的援藏女教师——徐凤翔,激情地讲述她想要在西藏建立一座“生态定位观察站”——哪怕只建一座小木屋。她说对西藏地区的发展如何如何重要,对地球同一纬度线、对全球生态协调如何如何重要。当时乃至现在我都觉得不一定有人等着她的考察成果去实施规划,但我立刻被她的“如何如何重要”迷住了。可能由于血缘遗传因子的作用,我从小向往把自己和“如何如何重要”的事业联系起来;否则就总为闹不清自己为什么活着发愁,或为“接错了线”苦恼。我一生迷恋知道天高地厚而不怕地厚天高的性格。于是在嘉陵江畔,我对徐凤翔说将去西藏找她。她不信,也不在乎,我却上了心,直到一九八二年秋天,我随作家代表团去西藏,在藏南藏北转了一遭,当次日将飞返内地时,我才在一个小旅社的客房里,在汉族的、藏族的,烧饭的、补鞋的,采购的、探亲的一群人中找到徐凤翔,她正闪着大眼睛向大伙讲保护森林。我立即退掉极难买到的机票,随徐凤翔坐在大卡车的前座上进了藏东南森林,与当地驻军派给我们的藏族副连长白玛一起,天天为徐凤翔和她的考察小队在帐篷外敲冰举火烧水做饭,亲眼目睹她每天每天披星戴月早出夜归,数树叶、称树根、查年轮……西藏土地面积一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等于十二个浙江省或两个法国,真不知她这行业要做到何年何月才算个段落。我决定在稿纸上先为她搭一座小木屋——一九八三年植树节前后,我的报告文学《小木屋》。此文结语是:
我们——一个一个、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知识的苦力,智慧的信徒,科学与文化的“朝佛者”;
啊,我们也是一步一长跪地在险路上走着。恁是怎样的遭遇,我们甘心情愿、情愿甘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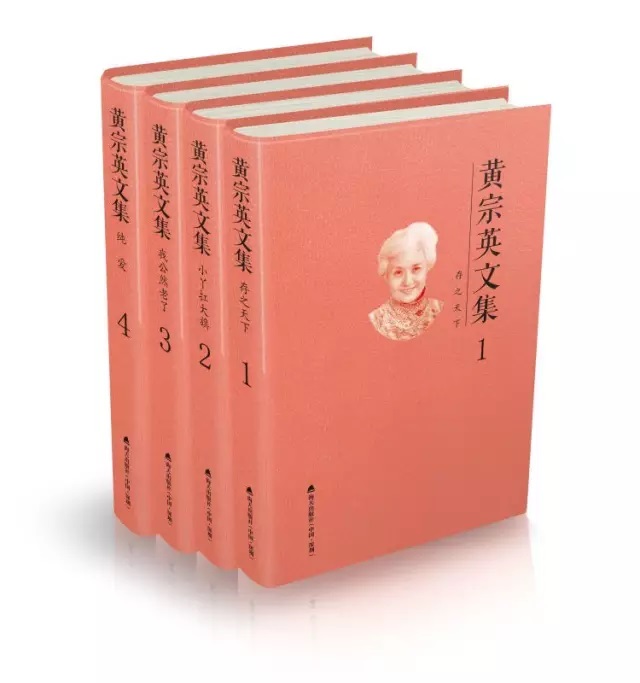
一九八四年五月,为了“小木屋的梦”——为了在藏东南建一座高原森林生态定位观测站,我随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摄制组再度进藏。高原并不可怕。许多队员甚至毫无异样感觉。但毕竟那里的氧气只是内地的三分之一;我们也就愈加尊敬六次进藏,深入密林险境考察的徐凤翔。
电视片《小木屋》以我的报告文学为线索,摄制组没有剧本,我们实地拍摄生态学家徐凤翔和她的伙伴们的森林考察工作。我个人的任务只是让自己忘掉自己曾是个演员,让植物学家们忘掉摄影机,使屏幕上出现森林考察生活的真实情景。《小木屋》将是我国第一部电视报告文学片。
一年以后,电视片中小木屋的图形成为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的前区的象征建筑。
(摘编整理自《黄宗英自述》)
编辑:范昕
责任编辑:卫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