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人如何决定自己喜欢吃些什么?
我们天生就有这样的偏好吗?
或者这些饮食习惯是由我们的家庭、文化、地缘因素,甚至是出于情绪所形成的?
吃,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饮食习惯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家庭与文化、记忆与性别、饥饿与情感等。
英国著名食品作家和历史学家、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思想史研究员比·威尔逊所著的《第一口:饮食习惯的真相》引用了食品心理学家、神经学家以及营养学家的最新研究,揭示“吃的艺术”。

《第一口:关于饮食的真相》,三联书店出版社
2011年,在旧金山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有20多本著作的美食作家玛莱娜·斯皮勒在经过十字路口时被车撞倒。当开始的剧痛感慢慢减轻后,她发现自己还有一处受伤了。对她来说,这个伤可比断胳膊要糟糕多了——头部创伤造成她的大脑嗅球受损。嗅球是大脑中感知气味的部分。也就是说,她再也无法享受美食了。玛莱娜从年轻时就非常爱喝咖啡,但现在咖啡喝起来却没有味道了。
玛莱娜被确诊患上了嗅觉缺失症,这个病症意味着闻不到气味,也同时意味着尝不出食物的味道,因为几乎所有被我们称为“味道”的东西其实都是通过鼻子感知到的。
人们有时候会把嗅觉缺失症说成是“失去味觉”,但其实味蕾本身受损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90%以上的味觉失调症患者都会出现嗅觉减退或丧失的情况。闻不到气味,他们就不会渴望那些永远吃不够的熟悉味道。他们的圣诞节里没有火鸡或香料的香气萦绕,他们的夏天里也不再有草莓和青草芳香的印记。嗅觉缺失症患者常说,这是一种莫大的损失。

玛莱娜·斯皮勒在事故发生几年后,发现自己对味道的敏感度在恢复。有时候,早上喝一杯咖啡更能让她感到快乐。她说,口味能让我们找回那个熟悉的自己:“你的世界里有种特定的味道。你的母亲会用自己的方式煮饭。你已经习惯了生活中的某些味道,一旦失去它们,你就会开始问,我到底是谁?”记忆是驱使我们学习饮食的最强动力,它塑造了我们的所有食欲。那些真正重要的食物记忆往往要追溯到很早以前。你可能不记得上周二的午餐吃了什么,但我敢打赌你还记得儿时习惯吃的饭菜,周末早上的大餐,还有家里面包的味道。这些都是多年后甚至几十年后还会转化成情感力量的记忆。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由他所见所爱的事物构成的。我们常常会回到心中的那个世界,即便是在旅途中,看似生活在不同世界里的时候,也还是会回到那里。”——《意大利之旅》,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著
寻找一种食物,让人产生更强更久的饱腹感,已经成了近些年来营养研究领域的“圣杯”。
如果你想欺骗自己的身体,让它产生更强更久的饱腹感,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喝汤。当我们摄入碳酸饮料等饮品形式的液体热量时,无法产生饱腹感,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液体从嘴里经过的速度太快,还来不及发送信号,告诉胰腺、肠道和大脑,我们正在摄入营养成分。如果我们慢一点,一勺一勺地摄入液体热量,并把它当成食物来看,它就能让人产生很强的饱腹感,甚至往往比固体食物带给人的饱腹感还要强。
一项研究已经证实,喝鸡汤比吃烤鸡胸更能让人产生饱腹感。还有一项研究表明,虽然芝士和饼干的热量比汤的更高,但选择汤为前菜的人要比选芝士和饼干做前菜的人吃的主菜少。汤给人带来的饱腹感可能与它的大容量有关,这就跟混入了空气的奶昔一样。有证据表明,低能量密度食物更能让我们产生饱腹感,汤正好就属于这类食物,只要不是那种加了200多毫升奶油的龙虾浓汤或维希奶油浓汤。我们通常不会考虑食物的能量,每天都会吃重量大致相同的食物。这也就是为什么稀汤比其他食物的热量更少,却更能让我们产生饱腹感的原因。

但汤能让人产生饱腹感,并不全是理性的结果,更重要的还有汤的“概念”。这也是有些书会被称为“心灵鸡汤”的原因。它们也可以被称为“心灵的越南河粉”或“心灵的蛤蜊浓汤”,因为所有的汤都是精神食粮。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认为,用锅煮、用碗盛的热肉汤是特别有营养的东西。汤对饮食者的要求不高。它对你就像对待孩子一样,你会不会用刀叉都没关系。喝汤时,不用切割,甚至也不用咀嚼。每当我们生病时,妈妈都会给我们煮汤喝。辛勤工作了一天后,我们只想像胎儿那样蜷在沙发里。汤就是我们回家的动力。
“所以,当我写到饥饿的时候,我实际上是在抒写热爱……”——《吃的艺术》,玛丽·弗朗西丝·肯尼迪·费雪著
在渴望某种味道的例子中,最让人心酸的还有战俘们对食物的迷恋。普里莫·莱维回忆到,他被囚禁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附近的布纳劳改营时,曾听到战友在梦里呻吟,还看到他们舔嘴唇:“他们梦见自己在吃东西。这是大家都会做的梦……你不仅能看到那个想吃的食物,还能感觉到它就在手里,真真切切的,都闻得到它浓烈的气味。”
在“二战”的战俘回忆录中,大家共同提到的话题除了饥饿,还有饥饿引起的、对过去所有食物的疯狂回忆,他们想象着自己重获自由后能再次吃到这些食物。他们的梦里很少出现长大后在高档餐馆里吃到的食物,更多的反而是儿时吃过的那些食物,还有家里那些油腻的、让人感觉满足和安全的饭菜。一位曾经的英国战俘回忆说,他曾经连续两个晚上梦到“煎蛋和布丁”。他还记得自己醒来时失落的心情,因为“一觉醒来,与他相伴的只有一缕清冷的月光”。

那些“二战”期间被囚禁在远东地区的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战俘们对食物有着一种特别的狂热。在远东囚禁地,战俘们能吃到的配额米饭跟他们想吃的食物差别太大了,这足以导致他们出现轻微的精神错乱。食品历史学家苏·谢泼德写到,日本集中营中的大部分人都“退化到一种幼稚的状态”。他们都幻想着能吃糖果:英国战俘想吃的糖果可能是巧克力手指饼、板油布丁,还有热气腾腾的黄色蛋奶沙司;美国战俘想吃的糖果可能是赫尔希巧克力棒,妈妈做的苹果派,还有魔鬼蛋糕、椰子蛋糕等各种夹心蛋糕。

有些人不愿意跟大家一起谈论食物,因为这会让他们想到自己离家那么远,那种感觉实在太痛苦了。但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关于食物的胡扯成了一种生存机制,帮他们熬过了那些没有尽头的、残酷又无聊的日子。一位曾经遭到长期关押的战俘回忆道,被关押到一年半左右的时候,大家对食物的谈论就彻底取代了对女人的幻想。
有些人表现得更夸张,他们会在碎纸片上写下详细的菜单,甚至还会写出烹饪方法。电影制片人简·汤普森为了制作2012年出品的纪录片《不复往昔》,花了20年时间去采访曾经的“二战”战俘。她发现受访者都曾写过感恩节菜单。这些菜单都是他们根据“儿时聚餐的记忆”重新构想出来的。所有的记忆都是失真的,而且这些人在半饥饿状态下想出来的节日菜单远比儿时真正的菜单奢华得多。中士司务长莫里斯·路易斯被关押在日本期间,因为要照顾自己和手下的士兵感到心力交瘁。为了保证自己“神志清醒”,他写下了一份奇怪的感恩节菜单,里面有弗吉尼亚火腿、酥炸野兔、蔓越莓沙司、雪花土豆、甜甘薯、黄油玉米、奶油芦笋尖、绿橄榄,还有“各种饼干”“各种坚果”“各种糖果”“各种口味的冰淇淋”“各种果酱”以及“各种新鲜的水果”。

“各种”是个令人痛心的词,因为说出这个词的人,饮食已经被削减到非常单一的程度了。监狱是一个能让人充分发挥想象力的地方。路易斯中士这么长时间都没吃任何饼干、坚果、甜食或冰淇淋,竟然还能策划出一顿免费提供各式美食的大餐。他又做起了儿时的白日梦,想象着自己能在甜品店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场景。
战俘们对儿时食物的渴望就像是食物怀旧情绪的夸张版。大家想要找回的不只是味道,还有与味道相关的所有东西,包括围坐在桌旁的家人,被在乎的感觉,以及摆脱责任束缚后的自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也会想吃那些不健康食物,正是因为它可能承载着幸福的内涵。并不是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都有个能做出完美苹果派的妈妈,战俘罗素·布拉登是个“害羞的年轻澳大利亚炮手”,曾被关在日本集中营里三年,他收到姐姐寄来的卡片时非常兴奋。卡片寄了16个月才到他手上,因为不能超过25个字,卡片的内容非常简短。上面写道,“亲爱的罗素,妈妈做的布丁还是那么难吃。我们非常爱你,亲爱的。”布拉登后来说这封信里包含了“我想知道的所有事情”:他的家人相信他还活着,而且“家里人还会拿妈妈糟糕的厨艺开玩笑”。

“瑞贝卡只爱吃院子里潮湿的泥土,还有用指甲从墙上抠下来的白墙皮。她一定曾因为这个习惯被父母或抚养者责骂过,所以她都是偷偷摸摸地、满怀愧疚地在吃这些东西……”——《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儿时关于食物的记忆,比如家人之间的玩笑通常是外人无法理解的。如果我给你一个小盘,里面放上三堆食物,分别是干酪、切碎的苹果和葡萄干,你可能会觉得我有点奇怪,也可能会误以为我想让你吃些低热量、无麸质的食物。但如果我把这盘食物端给我姐姐,她立马就会明白,这是在给她一份好吃的睡前零食。以前我们睡不着,穿着睡衣爬下楼的时候,妈妈就会为我们准备这样的睡前零食。
关于童年食物的共同记忆有助于维系亲情,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那些旅居人士身上看到。他们会用行李箱偷偷装些作料带到要去的国家,用这种形式把“故乡”带在身边。在希腊,人们有时会把这种对故乡食物的渴望称为“燃烧的双唇”。如果希腊人移居到国外,他们的母亲常会给他们寄些爱心食物包裹,里面会装上“牛至叶、百里香、山茶、当地产的蜂蜜、无花果、扁桃仁、硬奶酪和无水黑面包圈”。大学时,我有个希腊朋友叫雅典娜,她和智慧女神同名。她就收到过妈妈寄来的最好的包裹,里面有甜的哈发糕片,还有超大包的、非常新鲜酥脆的开心果。她把这些食物摆在充满异域风情的陶瓷盘子里。虽然雅典娜的宿舍也是一间杂乱的小屋,但莫名地让人觉得她的宿舍跟我们的不一样,感觉她被故乡的食物围绕着,好像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人。

尽管后来在世界各地的超市都很容易买到羊奶酪了,希腊人出门旅行还是会带上它。他们常常是离开家之后才知道自己有多想念这种白色的湿奶酪,这时候他们就非常想再吃一口那咸咸的羊奶酪。威尔士一所大学的一位希腊学者每次从希腊回来都会带一大罐10公斤装的羊奶酪。他说:“我每顿晚饭都会切一块吃。它对我来说就是‘白金’。”
美食作家马克·比特曼曾被人问道,“我们都知道长期吃热狗对身体没好处,吃完还马上会觉得反胃,味道也不怎么样”,那为什么不再吃热狗对我们来说还这么难呢?他回答说,与热狗,尤其是康尼岛上纳森连锁店的热狗相关的记忆是他长大后喜欢的任何食物都比不了的,热狗承载着他的童年和渴望,还有跟姐姐在游乐场玩耍的那个炎炎夏日。如果比特曼不想再吃热狗了,那一定不会是因为他意识到了热狗不是健康食品,也不会是因为他得知热狗中的肉取自那些不幸动物身上最劣质的部分,那必定是因为他的那种情感关联被切断了。
延伸阅读
《为食物辩护》,中信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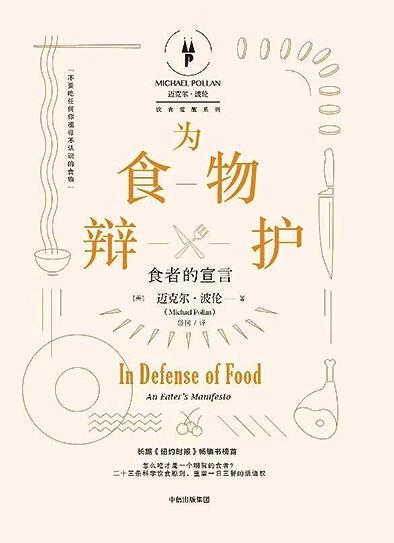
怎么吃才是一个明智的食者?“不要吃任何你祖母不认识的食物”。吃的理由绝不仅仅是吃本身,食物还关系到快感,关乎人际交往,关乎家庭和精神生活,关系到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关系到我们自我身份的表达。传统科学认知的转变带来一种日益流行的饮食失调,你到底在吃什么,吃多少,按照怎样的程序吃,用什么来吃,什么时间吃,以及和谁一起吃,是这个时代的命题。
该书长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
《杯盘之间》,商务印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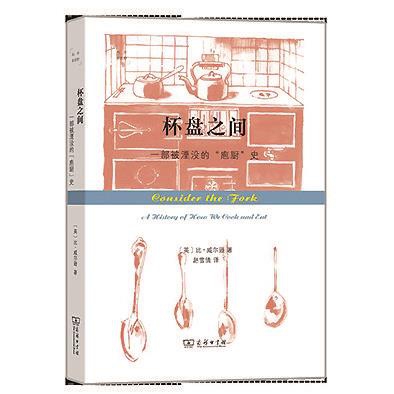
《杯盘之间》探讨了我们所使用的各种厨房用具是如何影响了我们的食物以及吃的方式,以及如何塑造人类的烹饪历史、饮食文化及自我探索的。作者博学多才,以生动的笔触从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角度探讨了使用什么工具以及如何烹调食物在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读来生动有趣。厨房设备和厨房科技与大量的社会变革息息相关,人类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改变并塑造着我们的生活,作者为我们讲述了一段我们未曾关注和审视的历史——烹饪与饮食的科技发展史,告诉我们已为大家习以为常的庖厨工具与实践其实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
《橘子甜不甜,只有脑知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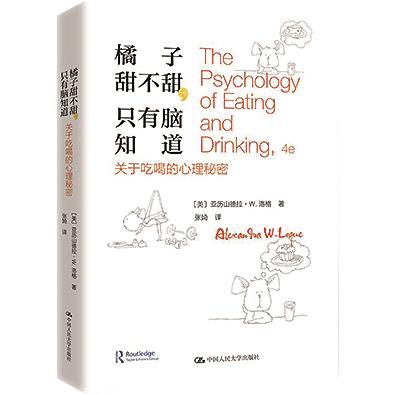
这本书探究了我们如何吃喝和为什么吃喝背后的真相,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从一个更加实用的角度来处理充满争议的饮食问题,而不是对减肥或消除挑食行为给出简单的答案。它以饮食行为科学研究的很新进展为基础,探究了诸如饥饿和口味这样的基本饮食问题,以及这些概念如何影响复杂的主题,比如饮食障碍、酗酒和烹调风格,可以让广大的读者获得关于这些主题的广泛而科学的理解。
《鱼翅与花椒》,上海译文出版社

这本书写的是中国菜的故事,也是一个英国女孩的中国旅行记。“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说,鲜有外国人写中国食物能这样鲜活有趣和精准。从四川热闹的市场到甘肃北部荒僻的风景,从福建的深山到迷人的扬州古城,从恢宏庄严的北京到时尚现代的香港,扶霞说中国已成为她难以改掉的“积习”,在中国的美食版图上走南闯北是她欲罢不能的期许。在《鱼翅与花椒》中,扶霞用自己客观而又新颖的视角探讨饮食与文化,它“与其说是很多西方人了解中国风味的指南,不如说是通过中国食物的窗口,展现当下中国人生存图景的文献”。
编辑:周敏娴责任编辑:邵岭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