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到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掀起的风暴已无需赘述。对东亚女性“受规训的一生”的讨论如星火燎原,蔓延了社交网络,《金智英》不是掀起这个议题的起点,更不会是终点,但她给这个烫手话题添了一捆柴,让女性愤怒的烈火烧得更旺,这是毫无疑问的。

围绕《金智英》这个作品的讨论,则足够耐人寻味,小说出版时,电影公映时,一直存在着一个顽固的“理(性)中(立)客(观)”的声音,认为原作小说的文本太差,够不上文学的级别,“一个在网络空间讨论的话题,犯得上写成一本书么?”
这种观念的存在,恰恰验证了《金智英》呈现的内容:女性要面对的“偏见”不是来自特定的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家庭或工作场所,而是宛如空气一般,针对女性的检视无处不在,哪怕是“讲述”这种行为本身,都要被挑刺“技术不行,修辞太差”。捍卫《金智英》的读者会说:书里的内容能够被写下来,已经够艰难了!这是实话,但这种辩护仍然是露怯的。
放眼世界范围,这些年女性写作的成果能让男性同行和读者颤抖: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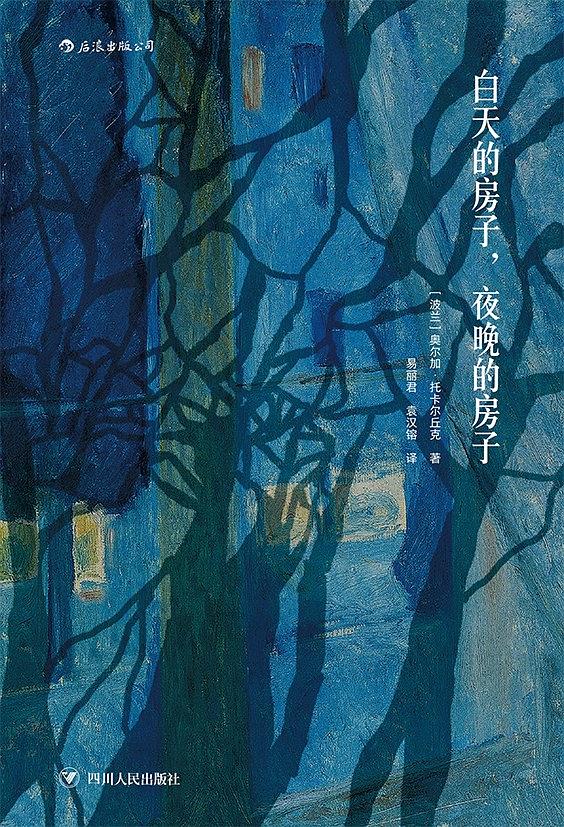
布克奖50周年大选,读者的票数集中给了英国作家莱夫利的《月亮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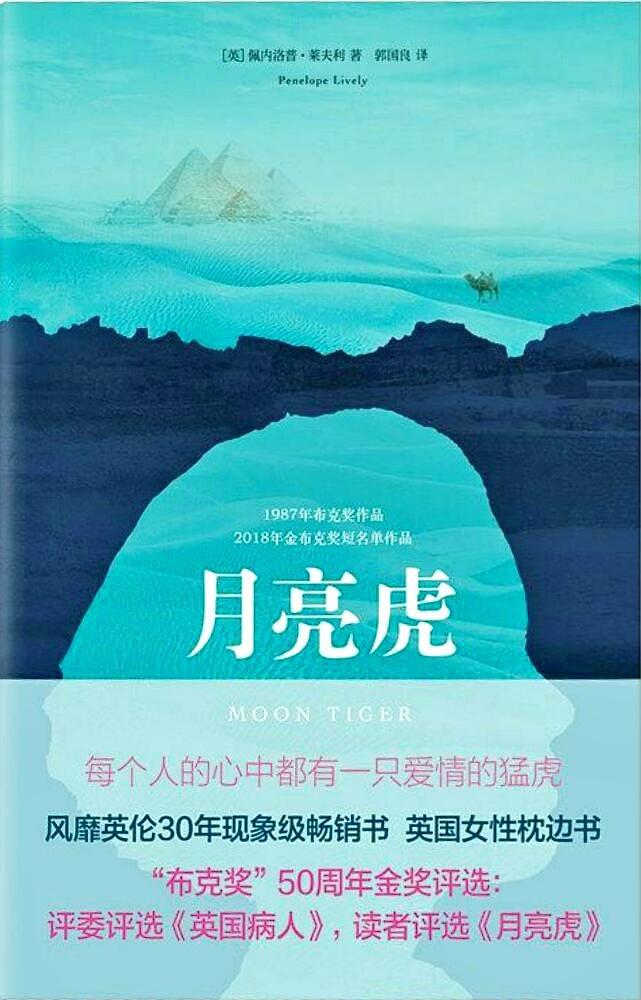
阿特伍德的《证言》和埃瓦里斯托的《女孩、女人及其它》分享了2019年的布克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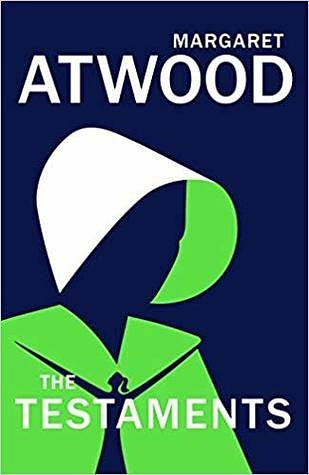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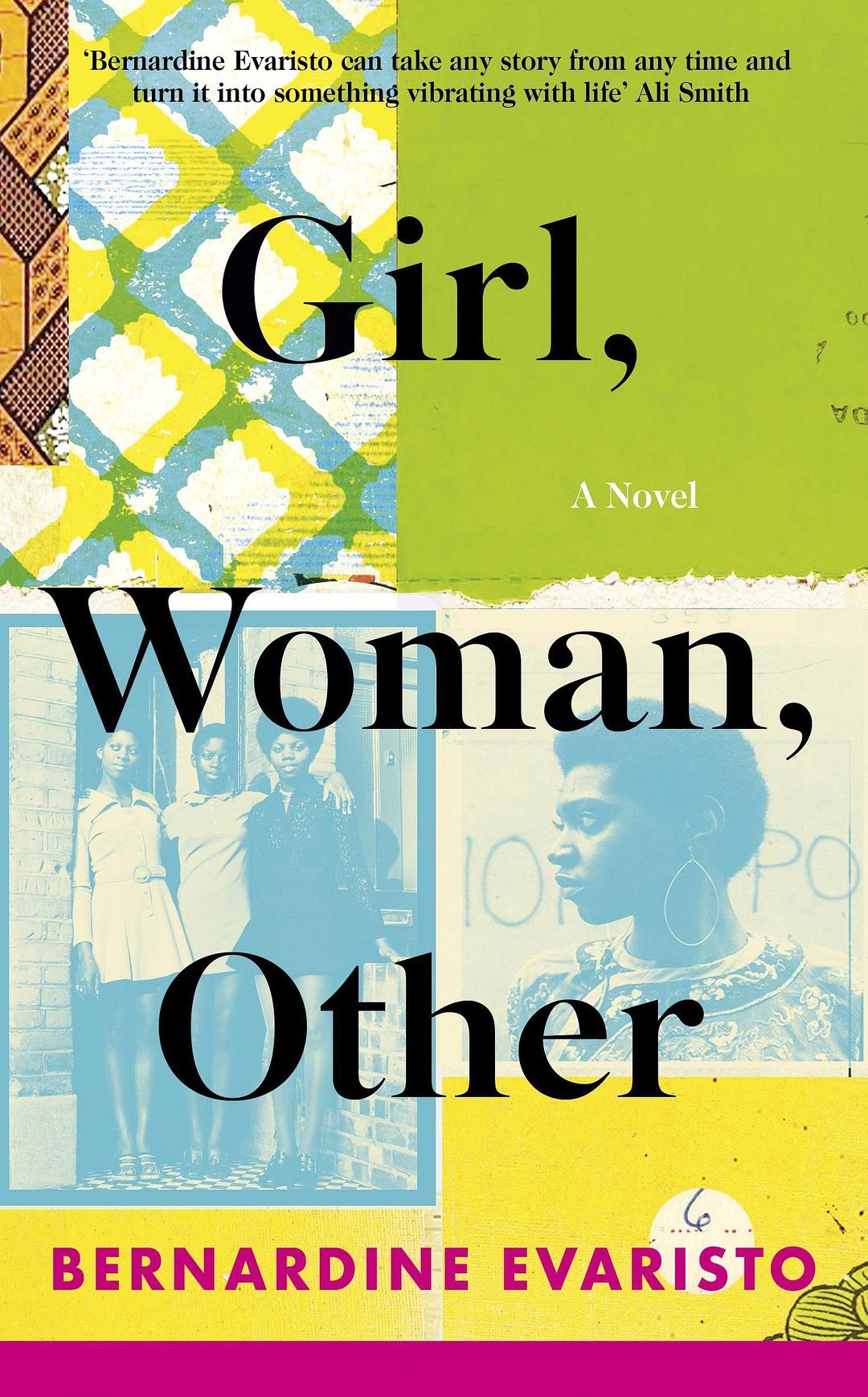
也许,赵南柱和《金智英》无法成为上述列举对象的同类项,因为按照约定俗成的评判度量衡,《金智英》里欠缺复杂的技巧和完善的修辞。然而,《金智英》的“简陋”和“笨拙”引发了关于叙述、关于写作的一个核心命题:文学的呈现,存在着“唯一合法的标准”么?世界不断变化,“文学”的操作方式和评价体系怎么可能维持一种虚无的“永恒”呢?对《金智英》的讨论,存在着凌驾于性别争议之上的“绝对文学标准”么?或者说,对这样一部小说的讨论,怎么可能不基于性别议题呢?

托卡尔丘克在领奖时的演说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叙事是权利,更是权力,如何叙述这个世界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个时代的人们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于,陈旧的叙述既不能呈现现实,也无法想象未来。如果把赵南柱的写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出版仅两个月后选择自杀的林奕含的痛苦命运,以及托卡尔丘克的演讲并置,一幅清晰的关于“写作”的图景会浮现。

对比《金智英》遭遇的专业挑刺,《房思琪》在专业层面是被一面倒叫好的,林奕含在写作的起点上,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哪怕是掌握着评论话语权的男性权威都无法否认,《房思琪》呈现了现有文学评价标准下的完善优雅的技巧,它在修辞层面难以挑剔。
可是,“完美的天才少女”林奕含在去世前8天接受的访谈中,说了什么呢?在那次内容苦涩到让人不忍心看下去的对话中,林奕含问观众、问同行、也问她自己:艺术是不是巧言令色?身为写作者,艺术的欲望是什么?林奕含的绝望在于,她知道自己是被规训的,规训过程中的丑陋和暴力严重地伤害了她,然而当她把创伤体验写下时,她意识到她的叙述方式、她对审美的自觉,竟然都来自那套规训方式,她无法从中挣脱。当她把丑恶的、痛苦的经验转换成美的修辞,一种“被修辞所包围的屈辱”压垮了她,便是小说中怡婷的那句心里话:文学辜负了她们。

文学从语境中来,语言和思维不是抽象的、脱离世界的,男性中心、男权意志决定的修辞游戏规则,怎么能够适用于表达在这个结构中受害者和弱者的声音呢?托卡尔丘克在《温柔的叙述者》这则演讲中,反复地探讨着:有没有故事可以超越沉默寡言的自我监狱,去揭示更广阔的世界,有没有故事能从远离中心的角度看待问题?她说:“一个新的叙述者,不是语法结构的搭建者,而是能够囊括每个角色的视角,有能力跨越每个角色的视野,看得更广,忘却时间的概念。”
林奕含本不该为《房思琪》的“工笔”感到羞耻和自责,她没有错,她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人。赵南柱在《金智英》中的“不工”也不该成为被贬低的理由,这种白话式白描式的写作,构成了一种质朴的反抗。《金智英》这个文本让文学从美学的斗兽场回归了它的“交流生命经验”的使命。作者诚实地讲述着故事,赋予微小的碎片以存在感,这些碎片映照了女性的经验、生存境况和记忆,在简朴的讲述中,文学找回了它的寓言属性——在嘈杂的世界中,金智英的声音找回了她的轮廓,她既是一个生活在特定时代和环境中的人,但她的形象也超越了具体的物质背景和细节,成为“无处不在的普通人”。
《安徒生童话》里有一个故事,一个被扔到垃圾桶里的茶壶讲述它遭遇的残酷经历,继它之后,别的被抛弃之物也逐个开口,这些“废弃品”的默默无闻的讲述,最终汇成奔涌的史诗。《金智英》的价值就在于,她尝试着进入了这个“茶壶的世界”。
作者:柳青
编辑:柳青
责任编辑:邵岭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