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当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执行主席、阿塞拜疆文化部长阿布尔法斯·加拉耶夫的木槌重重落下,“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正式成为中国第55处世界遗产。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被誉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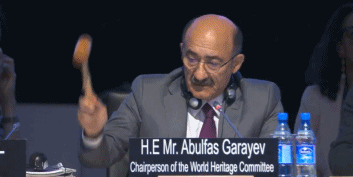
今天在浙江大学首发的“良渚文明”丛书,正是省文物局“面向良渚古城遗址申遗的保护研究成果应用及转化”项目的最新研究成果。这套面向大众的通俗科普读物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含《神王之国:良渚古城遗址》《土筑金字塔:良渚反山王陵》《法器与王权:良渚文化玉器》《内敛与华丽:良渚陶器》《工程与工具:良渚石记》《图画与符号:良渚原始文字》《物华天宝:良渚古环境与动植物》《良渚时代的中国与世界》《良渚遗址考古八十年》《何以良渚》《一小铲和五千年:考古记者眼中的良渚》共11种。
丛书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致力于良渚考古的中青年学者集体编撰,围绕近年来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既有良渚古城遗址的概况、良渚考古的历程、良渚时期古环境与动植物信息,也有介绍良渚文明最高等级墓地的反山王陵、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良渚高等级玉器、供应日常所需林林总总的良渚陶器等。现摘编丛书中《法器与王权:良渚文化玉器》一书书摘如下:
由于乾隆皇帝喜好古物,所以清宫中收藏了大量的古玉。其中有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璜、三叉形器等玉器。乾隆皇帝还常常为新获得的玉器赋诗作文。从其诗文的内容看,玉琮当时被认作是古代扛夫抬举辇车或乐鼓所用的“杠头”装饰。乾隆皇帝的收藏反映了近代良渚玉器的出土情况。
良渚玉器的出土与传世,几千年来未曾间断。最早也许可以上溯到殷商时期的古蜀国。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玉琮,从形制与雕工看,无疑是4000多年前良渚人的作品。这也许是古蜀国传承千年的传家宝,也许是殷商时期新获得的一件宝物,但他们似乎并没有忘记它所代表的神性,因此模仿制作了许多风格相似的玉琮。
至西周以后,世人逐渐不识良渚玉琮的本来面目与意义了。江苏吴县严山春秋时代的窖藏中发现,良渚玉琮被当成了可以再利用的玉料,重新被加工和切割,可见在当时,这些良渚玉器并未被当作古物而加以珍藏。因此良渚人发明的玉琮的神性内涵至此已经失传。
但是中国人对玉的情有独钟却并没有间断,对于玉器的研究更是由来已久。早在近代考古学用物质标准划分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以前,中国东汉时期的袁康就有了类似的划分,他在《越绝书》中记载了战国时代风胡子对楚王说的一段话。风胡子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
袁康的划分与近代考古学根据生产工具质料的发展变化所划分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江苏吴县严山窖藏作为玉料切割的良渚高阶段及顺序十分吻合。就中国考古所揭示的物质文化的发展历史,不仅符合这样的发展顺序和对应年代,而且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也确实存在广泛的用玉现象,存在一个以玉为兵,以玉为礼的时代。
中国的金石学兴起于宋代,以证经补史为目的,因此,金石学十分重视碑刻和青铜器等有文字的古物的搜集与考证。在金石学的著作中,关于玉器的研究,一直属于次要的地位。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中,仅选录了圭、璧等14件玉器。南宋的《续考古图》略有增补。元代朱德润的《古玉图》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的玉器图录,可以说标志着古玉研究在金石学中开始有了独立的地位。
清末吴大澂的《古玉图考》,可谓古玉研究中最为杰出和集大成者。正如他自己在序中所言,“好古之士,往往详于金石而略于玉,为其无文字可考耶”“余得一玉,必考其源流,证以经传”。《古玉图考》在玉器的考据研究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而且配有相当精确的绘图,大多数的图上还注明比例、尺寸、颜色等内容。这为我们将古文献中所描绘的玉器与实物相对应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在《古玉图考》中,有收录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良渚文化的玉琮,这是第一次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玉琮归属到了具体的实物。经吴大澂考证,才使人们第一次认识到这种外方内圆的玉器原来这正是古代经籍中所称的“琮”。虽然良渚玉器在当时还被认作是周汉之器,但就玉琮本身所进行的有价值的学术考证,这应该是第一次。
南宋时期有青瓷琮式瓶和石质琮式瓶,外方内圆,四面有竖槽和突起的横条装饰,显然是模仿了良渚玉琮的形态特征。这间接地说明了良渚文化玉器在宋代就曾出土过,并成为人们喜爱的珍玩。
1936年,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在他的家乡良渚揭开了良渚文化考古的序幕。施昕更先生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也向我们透露出了20世纪初浙江的盗墓之风。报告中称:“杭县所出玉器,名为安溪土,驾乎嘉兴双桥土之上,而玉器所得不易,价值至巨,且赝品充斥,不可不注意,杭县的玉器,据善于掘玉者的经验,及出土时的情形看来,都是墓葬物,可无疑问,而墓葬的地方,无棺椁砖类之发现,据掘玉者以斩砂土及朱红土为标志,也是墓葬存在的一证……所谓有梅花窖,板窖之称,排列整齐而有规则,每得一窖,必先见石铲,下必有玉,百不一爽,每一窖之玉器,形式俱全,多者竟达百余件……”从此可知良渚盗墓者对古墓埋藏特点的熟悉程度,良渚玉器的出土与流失也可见一斑。施昕更先生虽然断定玉器为墓葬中随葬之物,但也未敢确定其与黑陶处于同样的年代,而是将其认作是商周之物。
另据卫聚贤在《吴越考古汇志》(《说文月刊》第1卷第3期)中所记,杭嘉湖地区在20 世纪30年代以前曾有多次古玉出土的线索。据记载,杭县安溪有一姓洪的农民,在清末曾掘到几担古玉。1930年,苏嘉公路桥北端曾出土一批古玉。1937年,在嘉兴双桥发现玉璧90余件。张天方先生在《浙西古迹》一文中也记录了嘉兴双桥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和民国二十三年(1934)曾有两次玉器出土。依现在的考古学知识我们可以认定,这些古玉基本应属于良渚文化,可惜的是当时这些玉器大部分都流散到了海外。可见所谓“安溪土”和“嘉兴双桥土”之说是有其来历的。
作者:刘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邢晓芳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