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9月25日,张炜(左)在哈佛大学演讲,右为作家哈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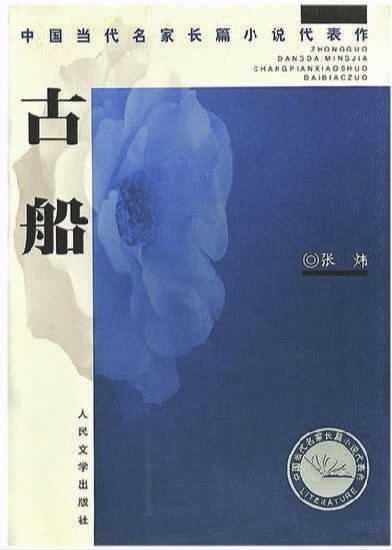
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古船》。

张炜在法国依夫岛留影。

最新长篇小说《独药师》。

张炜与德国翻译家在一起。(均采访对象供图)
本报记者 陈佩珍
很少有一个作家像张炜这样,在诗歌、小说、散文、童话等多个文学领域笔耕不辍且卓有建树。有文学评论家曾经评论:我实在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已经写得差不多而藏着掖着尚未出手者,如同当年突然冒出一部皇皇十卷本的 《你在高原》 一样。
他形容自己每一本作品的灵感来源是“种子”,但是并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立即发芽,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在心里酝酿了好多年。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 《独药师》,和此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 《你在高原》 一样,他在心里酝酿了30多年。这30多年,他不光等一颗种子发芽,在他心里面还有好多好多种子,它们在那里吐芽、生长、成熟。
从1973年开始写作,张炜已经写了44年。在这44年里,他始终坚信:写作者要对这个时代表现出巨大的善意,而不是一般的善意。
“写了四十多年,或许够长了,但有时又觉得一切才刚刚开始,一切都很新鲜也很初步。有大量新作品等待写出来,一时没有精力或没有准备好而已。从事写作这种极复杂的工作,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搞得明白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就是说,到了六十岁左右才刚刚有一点成熟感,可惜身体远不如过去了,再进行巨量的创作是不可能了。这是多么矛盾的一件事,但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从中国到外国,许多写作者都感慨过这个事。心里想要做许多事情,而身体只能做很少的事情,就是平常说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也有人是‘力有余而心不足’,这样会更糟。更糟的事情尽量避免,这已经很好了。”张炜说。
“一直不停地为自己的出生地寻取尊严”
1956年,张炜出生在山东龙口。整个童年时代,他都在龙口海边的树林里度过。他对这个海边树林的一年四季仍然记忆犹新:“春天是密密麻麻的苹果花和李子花,是一群群的蜂蝶和小鸟;夏天有流经园里的河渠、不远处的大海;秋天果实累累,园径上花丛盛开;冬天有遗落枝头的冻果,有高高的雪岭……”这些童年时代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大部分作品的审美方向。
张炜最早开始写作是在初中。当张炜谈起他的初中校长时,他说自己“长久地感激这个人”。
“感激”缘于这位校长热爱文学,在校园内办起了一份油印文学刊物,取名 《山花》。校长号召全体师生为刊物写稿,张炜早期在学校的作品就发表在这份刊物上,并获得过校长的当众表扬。
这对于当时的张炜来说,似乎成了一种生活宽慰:“其实一个人在初中时候的经历,对他确立一生的事业方向和爱好是非常重要的。到了高中或大学也可以,但初中这个阶段似乎更重要。我在初中的油印刊物上发表了作品,那种兴奋,远比后来出版一本书更重一些。那时候不是铅字,是手刻蜡版印出来的,可这都没有关系。在我和同学们那儿,那种墨味比茉莉花还香! 写文章得到校长的表扬,会让自己高兴很多天,于是就不断地写。”为了让自己能写出与大多数同学不同的句子,他除了在家看书,就是想方设法从一切地方找书看。
中学毕业后,张炜来到了“胶东屋脊”———栖霞。“栖霞和龙口尽管隔得不是特别遥远,可是地理风貌差异很大。从小在海边长大,突然来到山里,生活很不习惯。我有几年在整个半岛上游荡,是毫无计划的游走,到处寻找新的文学伙伴。”张炜说。
在栖霞的山里,张炜生活里主要的“玩伴”就是书籍:“所以对那时候读的书印象深刻,接受的影响也比较大。后来书多了,条件好了,书对我的帮助倒好像没有那时候大。最喜欢的是鲁迅的书,再就是俄罗斯作家的书。”
1978年,张炜考上烟台师范专科学校 (今鲁东大学) 中文系,来到烟台读书。这个时期他和同学一起创办了芝罘文学社,油印出版了文学刊物 《贝壳》。毕业后他来到山东省档案馆,并参与编选了三十余卷的 《山东历史档案资料汇编》。这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从龙口到栖霞,再到烟台,最后定居在济南。他一直没离开齐鲁大地,他说:“我常常觉得,我就是这样一个写作者:一直在不停地为自己的出生地寻取尊严和权利的人,一个这样不自量力的人;同时又是一个一刻也离不开出生地支持的人,一个虚弱而又胆怯的人。这样讲好像是有些矛盾,但又是真实的。我至少具有了这样两种身份,这两种身份统一在我的身上,使我能够不断地走下去,并因此而走上了一条多多少少有别于他人的道路。”
《九月寓言》 的后记里张炜曾写道: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一个人长大了,走向远方,投入闹市,足迹印上大洋彼岸,他还会固执地指认:故地处于大地的中央。他的整个世界都是那一小片土地延伸出来的。
生命的寻找,总是有着巨大而永恒的“诗意”
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张炜热”要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古船》 的问世。《古船》 以胶东小镇洼狸镇自土改至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史作背景,展开了镇上隋、赵、李三家族间的恩怨。张炜以一个古老的城镇映射出当时的中国,这本书被誉为“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
张炜谈及 《古船》 时曾说:“我的第一部长篇曾让我深深地沉浸。溶解在其中的是一个年轻人的勇气和单纯———这些东西千金难买。”
《古船》 之后的 《九月寓言》,无疑是张炜小说创作的另一个高峰,有人甚至认为 《九月寓言》 是张炜的巅峰之作。《九月寓言》 描绘了一个海滨小村的几代村民,在艰苦岁月里的劳动、生活和爱情。小说里的肥、赶鹦、红小兵、金祥、脏女人、庆余、小驴、盲女、赖牙……似乎在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与世隔绝地展示着他们的生活。最初的村里人是懦弱自卑的,可当庆余像在梦中得到真传一样将已经发霉发酸的地瓜制作成了拯救整个小村人的黑煎饼时,整个小村的基调都变了。他们不再怯懦,黑煎饼成了他们生活中力量和勇气来源。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谈到张炜这两部重要作品时说:“张炜的《九月寓言》,苦难依然存在于小村人的生活中,但是我读 《九月寓言》 最强烈的感受却是生存的欢乐和生命的飞扬,《古船》 里那种透不过气来的紧张、压抑之感被一扫而空,而代之以自由流畅纵放狂歌的无限魅力。为什么会有如此迥然不同的艺术效果呢? 在某种意义上,张炜慢慢‘接受’了苦难。”
2010年 《你在高原》 出版,文学领域又迎来了一次“张炜热”,张炜也借由这部中外小说史上篇幅最长的纯文学著作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这部作品展现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的生活经历。
“这可是了不起的、绝非可有可无的一代人啊。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理想和幻觉、自尊与自卑、表演的欲望和牺牲的勇气、自私自利和献身精神、精英主义和五分之一的无赖流氓气、自省力和综合力、文过饰非和突然的懊悔痛哭流涕、大言不惭和敢做敢为,甚至还要包括流动的血液、吃进的食物,统统都搅在了一块儿,都成为伟大记忆的一部分。”张炜在谈到这一代人时说。
张炜的小说一个显著特点在于,描绘了很多流浪汉形象,从 《古船》 中的隋不召到 《九月寓言》 中的小村人,从《柏慧》中的山地老师到 《丑行与浪漫》 中的刘蜜蜡,还有 《外省书》 中一生奔走的海边老人史珂,各种人物出于不同的原因走上流浪之路。《你在高原》 系列小说,流浪依旧是他一以贯之的主题:《家族》 中的宁珂,《橡树路》 中的庄周、吕擎,《荒原与纪事》 中的曲涴老教授,以及整个小说中的主人公宁伽,都具有流浪气质。
“东方人是农耕传统,不是西方的骑马民族。所以在西方,流浪汉小说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中国近年来有了流浪汉小说,其实并非是对西方的模仿,而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和反映。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有了乡民打工者的大规模往返,移居的人变得空前之多。生活的急遽变化也增加了不安定性,人们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状况极大地改变了。”张炜解释。
从哲学的层面来看,张炜认为流浪汉小说是客观世界在创作者心镜上的映像:人的心灵是处于周游状态的,每个人最终也会离开。人生只是一次或多次的长旅,所以写到生命的流浪,其实正有着根本的深刻在。我们的文学总是歌颂安居之福,这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种诗意的寄托。流浪是辛苦的,但这种的“寻找”的状态,总是有着巨大而永恒的诗意。
张炜有一个朋友,他家中的显著位置总是放了一个旅行箱,好像随时都要出差一样。这是可以理解的,他的生活虽然也算安定,但踏上旅途的几率还是很高的。大概是一种生活习惯之类,使他把生命的冲动、心底的潜意,就这么赤裸裸地、象征性地搁在了家中。
然而,被读者多少忽略的一本长篇小说 《刺猬歌》,对张炜来说却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可能是 《你在高原》 体量过大的关系,作为文学现象很容易被人注意到。《刺猬歌》 还没来得及回味和咀嚼,《你在高原》 就出版了。
有文化评论认为:“仔细看,《刺猬歌》里每一个动物、每一个精灵都有出处,都能够从现实层面解释得通,不是简单的荒诞。困难在于它是一个现实感很强的、从逻辑和语境上说得通的那么一个怪异的传说。如果毫不负责任地‘穿越’,一会儿变成马,一会儿变成神仙,一会儿又变成妖怪,那叫画鬼容易画狗难。《刺猬歌》的难度,在于它是一个朴素的神气故事。”
纵观张炜的作品,故事背景一直是他心中的“野地”———胶东半岛上。他觉得,写作者始终与大自然保持紧密联系,不一定就能变成一个质朴天然的作家,但起码有助于他的成长:“一个人总是专注于一些人事争执和社会层面,虽然十分重要,却不能脱离生命活动的大背景,这个大背景就是自然天籁。社会力量再强大,在大自然面前仍旧是十分渺小和脆弱的。我们对大自然闭上眼睛,它的决定力也仍旧存在。”
写了四十多年,张炜越来越感恩写作所带来的疲惫感。他把“写作”比喻成“劳作”:“劳动总是有魅力的,可持续的,任何工作都有辛苦有快乐,但充实感和饶有兴趣,才能保证几十年做下来。写作是一种劳动,更是一种极富创造意义的劳动。亲手创造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些生活,这当然会让人兴致勃勃。每个人对待事物的热情是不同的,持续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持久的热情,一定是有较大的热爱在内部支撑,这种热爱既源于某种偏好,也源于对一种意义的理解和追寻。写作者应该是极有理想和责任心的人。”
“书院精神应该是知识人的梦想”
2002年,张炜创办了万松浦书院。当时国内的书院并不多,张炜想通过建设书院尝试对现代大学批量教育模式的弥补。
万松浦书院每年都有很多学术活动,并出版了许多研读古典方面的著作。值得一提的是花了七年时间编著的、中华书局出版的 《徐福辞典》,这是万松浦书院近年来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
“徐福是一位奇特的历史人物,见于正史,并化为广泛而悠久的民间传说,形成了一个民族的心史。这个人连带了一段独特的中国历史、民间隐秘,具有形而上之思,是进入某些领域的一把钥匙。这个人仅仅作为新大陆的探险家,比起一直令欧洲人骄傲的哥伦布要早了一千多年。他出海之因、之意义,还有其他,都值得我们当今去好好研究。这是一个拥有多方面贮藏的、挖掘不尽的宝库。”张炜说。
研究徐福不经意间成为张炜写作的一门功课。在张炜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 《独药师》 里也提到了“徐福”这个人物,撰写和编辑 《徐福文化集成》 的经历对张炜创作 《你在高原》也十分重要。
除了文学创作,持续的阅读也是他的精神生活重要组成部分,年轻时,他一直坚持每天阅读量不少于五万字,现在仍然也不少于三四万字。重要的阅读时间里他会关闭手机。
他说:“一个写作者年轻时阅读国外的文字会比较多,随着年龄的增长,必将对中国古典越来越重视,并自感时间的紧迫。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人来说,大概可以说外国皮毛已得,传统宝藏却早已远离。问题非常严重,这已经是网络数字时代里很难解决的一个文化难题。”
《楚辞笔记》 《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都是张炜近些年阅读古典文学的记录。在他看来,这就像“一个人如果老了,就越来越爱看京剧了”一样,人会自然而然地靠近文化血脉里的东西。
“书院精神应该是知识人的梦想。做事不能怕麻烦,需要一点耐心、还需要一点公益心。我想在我有生之年让万松浦书院成为真正意义的书院,我如果不在了,我也希望这个书院因为做得很扎实,形成了传统,延续下去。”张炜说。
在张炜读书的时候,他喜欢文学,热衷于创办文学社和编刊物,那时候,任何一个有影响力的短篇小说或散文都不会被忽略。但是当前社会,文学刊物和文学作品越来越多,他认为重申文学的标准仍然有必要。
“文学当然不会因为载体的繁多而消失标准或改变标准。文学是语言艺术,首先要有精湛的语言表达,有言说的深刻个性和魅力。就小说来说,还要有人物思想故事诸方面的表达。当然,对于文学作品的感受力,每个人是不同的,这既有先天的差异,又有后天的修养之别。不过审美力的缺失,知识也难以弥补。所以我们有时会看到一个读了许多书、拥有高学位的人,反而缺乏基本的文学阅读能力,这种情况真的是经常发生的。”张炜说。
“林野生活本身就是一部大童话”
张炜的 《松浦居随笔》 获得了第二届“琦君散文奖作品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他说:“‘质朴天然’其实是对散文的最高赞美,大致上也是对文学的最高赞美。写作要秉持这样一种原则才好。”
如果仔细观察,近年来,张炜创作了越来越多的童话作品。《半岛哈里哈气》《少年与海》 《寻找鱼王》 《兔子作家》,他的作品开始从反思沉重的历史转变为寻找某种“质朴天然”的原始状态。
提及这种转变时,张炜说:“童话在文学作品里是比较纯粹的一种文体,它往往与纯文学的理想十分接近。童话不光是给孩子看的,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比较喜欢。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应该是成年人手里经常捧读的,他们会对这些文字着迷,像儿童一样恋恋不舍。”
随着网络数字时代的信息复杂化,泥沙俱下的声像制成品扰乱视听。在张炜看来,写作者进入单纯明了的少年情怀,是一种难得的生存滋养。
“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也不会总是写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故事。写作需要想象力,而想象力是没有边界的。作者不是一只兔子,也不是一只猫,却能够细致而逼真地理解它们,再现它们的生活。这的确依赖于一个人对人性深度的理解,依赖其丰富的人生经验。生命与生命的情感模型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这需要写作者去用心揣摸。”张炜说。
对于没有经历过苦难的当代年轻人,张炜认为要写出深刻的作品也不是没有可能。他说:“深刻表现在许多方面的。生命在每一种状态每一个时段中,都有其深刻的一面。人的想象力是奇妙的,这是一种天生的能力,但要随着后天的经验而生长。先天和后天是生命的两大空间,这两个空间的连接方式就是生命本身。人活着,空间就在加大和延展。所以说一个经历了无数事物的阅历深广的人,想象力应该是强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脑子没有发生退化的话,老年人应该是更有想象力的。而想象力是写作中最可信赖的好东西。”
张炜在生活里也热爱动物,他和家人收养了15只流浪猫和2只小狗,他觉得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眼睛里所蕴藏的隐秘是我们一生诠释不尽的:“动物的问题是人类不可回避的大问题,对许多人来说,它们是极为重要的存在。它们提醒我们以不同的视角和眼光去打量这个世界,从而对日常生活有个准确的判断。对动物冷漠或残酷的人,需要时刻与之保持距离并警惕着,因为这些人一定会摧残我们的生活。”
在古代,龙口是大片沼泽,再往前追溯,就是古人所说的“人民不胜鸟兽虫蛇”了。在张炜出生时,那是海边的一片很大的林子,人烟稀少,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莽野;现在,荒野消逝的速度很快,高楼林立,汽车穿梭,环境污染到了目不忍睹的地步,跟大自然唇齿相依的那种关系不再复返。
“人从小与植物动物亲密无间,会培养出不同的情怀,而且还将决定和影响他一生的审美特质。如果说童话是文学纯洁无瑕的结晶,那么林野生活本身就是一部大童话。睁开眼就是灿亮的星空,是树林和动物,是畅流的河水,这才是诱人的生活。”张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