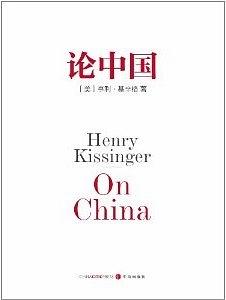
《论中国》(中信出版社出版)是美国前国务卿、“政坛常青树”亨利·基辛格唯一一部中国问题专著。书中分析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传统,从围棋文化与孙子兵法中探寻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模式,特别是试图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决策机制,以及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中美建交、三次台海危机等等重大外交事件来龙去脉的深度解读。
中方潇洒的态度
我们中午时分抵达北京机场时,来迎接的是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也就是被毛泽东要求分析中国战略选项的四位元帅之一。这象征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新的中美外交关系的支持。元帅带我上了一辆中国国产轿车,车里拉上了窗帘。我们去的是坐落于北京西区一个公园里的钓鱼台国宾馆,这个地方本来是皇家的垂钓处,四周有围墙环绕。叶剑英建议我们稍事休息,说4小时之后,周总理会到国宾馆来欢迎我们,并进行第一轮会谈。
周恩来亲自来看望我们,这真是莫大的礼遇。根据外交程序,东道国一般会在政府大楼里接待来访的代表团,特别是如果双方负责人的头衔差距这么大,更应如此。(我这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头衔相当于副部长,比周总理低了3级。)
我们很快发现东道主为我们作的时间安排非常宽松,简直叫人难以置信。这好像是表示,在隔绝了20多年之后,他们并不急于立即就达成实质性的协定。我们原定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大约是48小时,不能延长,因为我们得去巴黎谈越南问题。我们是乘坐巴基斯坦总统专机来北京的,而我们也无法控制专机的时间安排。
看到行程安排,我们发现除了在周恩来到达之前的这一段休息时间以外,中方还安排了4个小时让我们参观紫禁城。这样,48小时中已占去了8小时。第二天晚上周恩来不能陪我们,他要见一个朝鲜政治局成员,时间无法更改———也许不改时间是为了给我们的秘访打掩护。再去掉两个晚上16小时的睡眠时间,这两个20年来没有实际外交接触并曾兵戎相见、后来又险些再次动武的国家就只剩下不到24小时的时间可用于这第一次谈话了。
实际上中方只安排了两场正式谈判会议:第一场安排在我到达的那一天,从下午4点半到晚上11点20分,共7小时;另一场是第二天,从中午到晚上6点半左右,大概6小时。
可以说,中方如此潇洒的态度给了我们一种心理压力。如果我们无功而返,尼克松当然会大丢面子,他还尚未把我这趟密访告诉其他的内阁成员。如果两年来与中国的外交来往中我们所作的分析是正确的话,若美国派团赴华一事遭挫,那么,促使毛泽东邀请我们访华的紧急情况就可能会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对峙对双方都不利,这正是我们去北京的原因。尼克松急切盼望能够将美国人的视线从越南上面转移开来,毛泽东则决心迫使苏联在攻打中国之前能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中美双方都明白这次会谈事关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周恩来与基辛格(资料图片)
初识周恩来
周总理到达时,我们象征性地握了手,后来尼克松到中国以后,他与周恩来又在公开场合重复了这一象征性动作。之所以说这是个象征,是因为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国务卿杜勒斯曾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中方对杜勒斯的傲慢失礼耿耿于怀,尽管他们嘴上经常说那件事无关大局。
周恩来是我在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他个子不高,风度翩翩,目光炯炯,表情丰富。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压倒谈判对手,能凭直觉猜到对方的心理活动。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担任总理已有差不多22年,与毛泽东共事已有40年。他已成为毛泽东与毛泽东为之规划宏图的人民群众之间重要的纽带。他把毛泽东的远大理想化为具体计划。同时,他还因为给毛泽东的过激之处降温———至少是在毛泽东满腔豪情容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这么做———而赢得了很多中国人的感激。
在我跟周恩来的交往中,他含蓄、敏感的风格帮我们克服了曾互为仇敌的两个大国间新型关系中的很多隐患。
当时,我和周恩来在绿呢面的桌旁坐下时,上述的这一切都还非常遥远。我们坐下后,谈的是有无可能走向和解。周恩来请我这位客人先讲。我想好了,避开我们两国有分歧的问题,只从哲学角度谈中美关系的演变。我用了华丽的辞藻来做开场白,我说:“有很多游客来过这片美丽的土地。对我们而言,这又是一片神秘的国土。”这时,周恩来摆了摆手打断了我,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3个月后,我第二次去中国时,周恩来欢迎我们的态度就好像两国的友谊已经根深蒂固了一样。他说:“说起来这只是第二次会谈,但是我把自己所想的都对你们讲了。你和(温斯顿·)洛德先生对这一点很清楚,但是(戴安娜·)马修斯小姐和我们的新朋友(指我的军事助手乔恩·豪)不大清楚。你们可能认为中国共产党有三头六臂吧?但是,瞧,我和你们一样,是个可以与之理论并坦诚交谈的人。”
作者:基辛格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张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