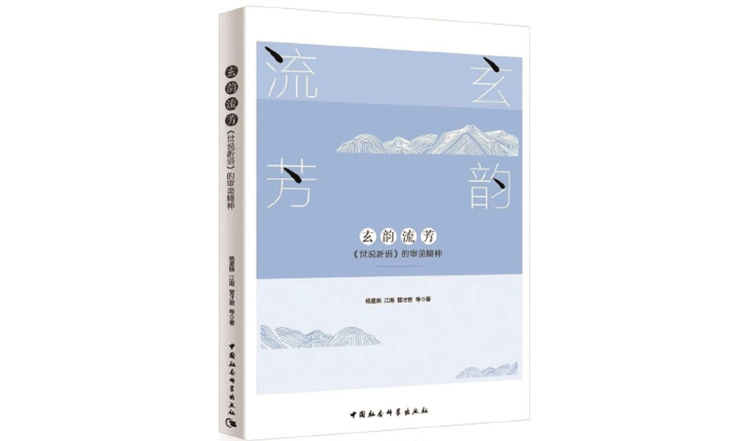
《玄韵流芳》
杨星映
江南管才君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日本京都是一个美丽如画的城市,就像一个巨大而鲜花盛开的花瓶。在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枕草子》中,清少纳言写道:“今日,高栏上搬来一只大的青瓷花瓶,插了许多枝五尺许长盛开的樱花,花儿直绽开到高栏旁边来。”这段话写于日本正历五年(994年)。然而,《千年古都京都》的作者高桥昌明写道:“平安京正历四年开始流行瘟疫,死尸堆满街边,往来行人皆掩鼻而过,乌鸦野狗食之饱腹,尸骨填满小巷……呈现前所未有的惨状。”我读到这一段记载,被“历史的美与真”这个课题所深为震动。我想到的是建安年间的那场瘟疫,想到的是在战乱与杀戮时代,那一幅以美为追求的魏晋风度与晋宋风流。
当我们回望中国蜿蜒起伏的悠久历史,历数中国史上那些动荡黑暗的时期,魏晋必以党锢祸端、黔首恫瘝而位在前列;然而当我们历数中国文化史上那些灿烂夺目的阶段时,魏晋人的卓然超逸、风神远韵,无疑也攫取了后人的目光。《世说新语》这本名著最可贵之处,即在于,它非常唯美,又非常真诚。“唯美”,是说魏晋时期严酷的社会环境,非但没有夷平世人的精神活力,没有使人的灵魂自由向死亡与灾难的威胁屈膝,反倒在其中孕育了优美精妙的文章、超远淡泊的人格,孕育了山水自然的欣趣、深邃博奥的玄理;“真诚”,是说《世说新语》里面没有回避苟全性命、发明一种学说为自己辩护、作为处世策略的清谈政治,没有回避纵情越礼、放任形躯的窳败士风,没有回避“自然与名教不同,本不能合一”的时代难题,没有回避那些“既享朝廷的富贵,仍存林下的风流,名利双收而无所惭忌”的达官真相,尤其是没有回避崇尚虚无、不以国事为务,最终导致了一个时代一个王朝倾覆的历史后果。那么,美与真,又是如何被完整地结合在一本书中呢?以对清谈领袖王衍(夷甫)的评价为例,《世说新语·轻诋类》桓公入洛条云刘注引《八王故事》云:
夷甫虽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婴,当世化之,羞言名教,自台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四海尚宁,而识者知其将乱。
同书同类同条刘注引《晋阳秋》云:
夷甫将为石勒所杀,谓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
即是真实、真诚记录了魏晋风度的后果,当事人也有临死前的悔悟。
同类同条又云: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尔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
袁虎“率尔”之对,表明魏晋士人的风流传统对历史不承担责任;而接下来桓温用一头只会吃东西不会做事的千斤重的大牛终被宰杀的命运,讽喻王衍与袁虎之辈,正是对这一传统的“轻诋”;而对王衍辈的“轻诋”,恰恰表明《世说新语》之“新”并非全新,它的真诚正在于它承认历史自有真实的一面,这一面必然是对魏晋风度所代表的美的否定。所以,《世说新语》一方面津津乐道地发明一种新的话语即“语言的桃花源”,这是它“新”之所在,另一方面又非常清醒地知道,这些士人在历史上输得很惨。这是我们在读《世说新语》时最要注意的,它并不只给我们看人生与世道的一面,而是整个地给我们看。刘义庆以及他的朋友们,把他们的趣味、追求、玩赏、标榜、批评、嘲笑,以及他们的犹豫、怀疑、甚至暧昧,全部展示给我们看,让后人有欣悦与感动,也有警惕与反省。历史本来就是在美与真的二元悖论中前行的。
当然,这本“名士教科书”,对于中国士人传统影响最大的,不是它历史省察的一面,而是它美感精神的一面,俨然为中国美感与抒情传统的一个源头。星映教授等三位学者将这本书命名为《玄韵流芳》,正是着眼于“流芳”后世的审美精神传统,而略去了不堪回首的当年往事。而“玄韵”是怎样的美?
是相坐谈玄、忘乎昼夜的精神欢悦之美,它见于一场场的名士集会,见于一次次的月旦之评;是清虚真率、不惮生死的人格之美,它见于嵇中散于东市的《广陵》一曲,见于王右军东床坦腹之举;是山水之美,它见于陶渊明笔下的南山田园,见于谢灵运诗中的山桃野蕨;是艺术之美,它见于《洛神赋图》的轻云蔽月,见于《兰亭集序》的健秀遒美。魏晋的精神美充贯于《世说新语》1000余则故事里,渗透在其中1500余名人物的生命里。鲁迅这样评价《世说新语》:记言“玄远冷隽”,记行“高简瑰奇”。“高简”是与名教相对的“自然”,是真心、真情、真性的随处流露,是精神的解脱和自由;“瑰奇”是“独立人格”,是人能摆脱外在的束缚,发挥生命的自主性,既不臣服于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政治强权,而显露于外的智慧美、人格美、精神美。“玄远”是以老庄思想为骨架,企图调和儒道的玄学之思,是澄怀味道,也是形神超越、宠辱皆忘、独与天地相往还的形上之美;“冷隽”是心镜之澄澈空明,是语言的写意简约,更是藏在一切美的事物背后的刘义庆和他朋友们那一双双冷隽的眼睛。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世说新语》都不仅向我们传达了属于那个时代灿烂的、别样的美,而且,若要品味华夏文化的“简约玄澹,尔雅有韵”,若想走进吾国士人心灵之幽深处,则《世说新语》不可不读。
战乱四起,神州陆沉,清谈亡国,虚无害道。面对美的绽放与美的毁灭,刘义庆和他的朋友们,究竟是如何想的?为何在这般不稳定的环境中对人的本体进行再发现,对人的天性进行再肯定呢?在杨星映教授等三位作者看来,至少有两点值得考虑:一是大的历史逻辑。人物品藻的标准由“德行”向“风度气韵”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对人的认识,由政治性的人物品藻向审美性的人物品藻的转变,这体现出魏晋时期“个人”的觉醒——人们开始发现自身的美,开始在大自然中发现与自己人格相通的风神远韵。一部伟大的书,正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历史嬗变的新信息、新走向而加以收集记录的著述。另外一点,三位作者意识到了,却没有加以特别强调。我愿意更进一解,即“由生命之有限而翻转上来的无限性”。当初曹丕撰写《典论论文》的初衷,即直接面对死亡之痛与怕,因瘟疫流行、友朋伤逝而生的感叹:“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越是乱世,越是生命短暂有限,越是珍惜如流星般划过夜空的生命之美,特别在一个美的精灵已经在民族心灵中醒过来的世纪。因为懂得,所以珍惜。从幽渺无边的宇宙时光中,魏晋人有幸分得了那么一瞬,却将它变成一段闪闪发光的、可以永恒的一瞬。牟宗三先生曾语:儒家所悟,一言以蔽之,人生虽有限而可以无限。我们可以接着说,历史虽无情而可以有情,生命虽幽渺而可以灿烂。是为玄韵,是为流芳。
作者:胡晓明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蒋楚婷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