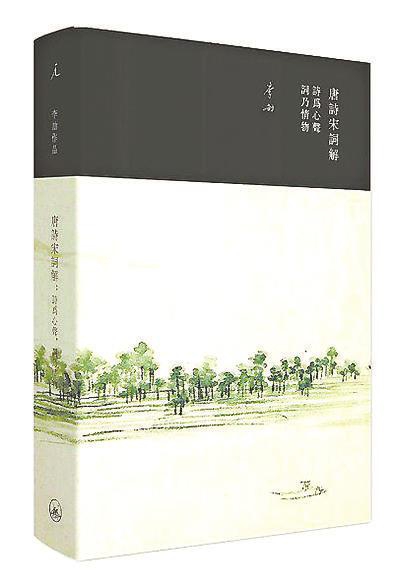
《唐诗宋词解:诗为心声,词乃情物》李劼 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近几年,传统文化在华夏大地渐成复苏趋向,日见盛象。“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无不折射出这样渴望“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全民心境。
读诗,让浮躁的现代人与失去的原乡和远方离得更近些,但在李劼看来,上千年来的诗论词话过分偏向意识形态的浸染和导引,不仅直接导致众位诗人、词人被标签化、脸谱化甚至污名化,而且间接将国人的诗性修养、美学趣味等一一带偏——后人在阅读唐诗宋词时,多停留在考较词句间的政治意义(即社会性),反而忽略了梳析其人性(即诗词作者通过嬉笑怒骂所透散出来的或顽劣、或沉郁、或浮薄、或刚毅等种种性情),甚至严重误读了诗词的言外之意。《唐诗宋词解》中的李劼,笔锋犀利,激昂难止,想常人所不能想,言常人所不敢言,其撰著此书的目的,可以说是给唐宋两朝那些名声赫赫的诗家、词家们勾描了一幅玲珑有致的“众生画像”。
如副书名所言,李劼主张“诗为心声,词乃情物”,在他看来,立足史家以治唐诗的陈寅恪先生多考据历史细节,常以家国情怀、功名利禄等来衡量列位诗人,如此单向度的点评方法少了些可亲可爱的人情味。因此,从写作方式来说,李劼把大家名句杂糅在琐碎且复杂的人性中,带我们通过只诗片词,钻探诗人、词人们那无比广袤、深邃的内心世界。“唐诗的初唐气象,与其说是气象在诗歌上,不如说是气象在诗人上”,此言应证李劼绝不就“诗”论“诗”,而是由“诗”观“人”,打心眼里,他是瞧不起那些封建王朝的御用文人的,只有那些拥有七情六欲、无比真实的诗家、词家才值得他点赞。
“诗风的明媚,源自心胸的敞亮”,所谓我手写我心,诗如其人,人有人品,诗亦如此,读诗是为了咀嚼“诗品”,通过李劼的导引,我们可以得窥骆宾王的骨鲠高傲、贺知章的放浪形骸……李劼的眼光不可谓不毒辣,其对人的分析也颇为有趣:唐太宗有头脑,但无性情可言;宋徽宗有性情,却没头脑;唐玄宗既有头脑,又有性情,恰是他的诗意性情,才是解开盛唐诗歌奥义的历史密码。王维与孟浩然两两相较,人生观、价值观植入各自的诗词中也颇为有味——孟浩然的寂寥,是牵挂着庙堂的寂寥;而王维的“孤烟直”,才是沧桑之后的孤寂和落寞。所以,王维能够看无见空,孟浩然只能无以见空入空。
在李劼看来,千年来的史家和普通民众,读词和论词时,皆不以情为意,蔑视人之常情。所以,李劼要撕破唐宋名家们的另一副嘴脸:与官家的意识形态系统离得越近的诗词家,越发追求“诗言志”,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是反人性、钳制情感、压抑自由之美的,所以,唐宋八大家被儒家道德伦理绑缚得太紧,后代将韩愈捧得越高,反而证明士风一代比一代更为堕落。李劼精准地点出:权力是“文学的毒药”,这可以拿杜牧为证,樊川居士喜欢在谈论政治生活时掺入女人元素,动辄把江山与女人捆绑起来,而他对于女性,只有欲念而无柔肠,貌似多情却无情,所以写恋情写不过内心纯净的温庭筠。
如白居易在 《与元九书》中所言,“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诗、词都有其生就的语境,皆以“情”为中心,在情与诗词的转换过程中,李劼构筑出眼观之境、身临之境、身心俱境三层境界,一个“情”字,彰显出诗词众家不同的层次、心胸和况味。由此观之,大晏小晏的情是傲娇的情,他们总保持旁观姿态,虚构情愫,更凌驾于“情”之上,所以词作只能浮于表面,未能让人感觉荡气回肠。而只有达到第三个境界,才能形成天人合一,进而写出令人震撼的慈悲、悲悯的气度、高贵的心胸。简言之,有人情味的词人才能写出好词,人情味是灵性,也是教养。中国传统诗学是肯定和张扬人情的人文诗学,也是强调诗人主体作用的主体诗学,所以,从以上路数来看,李劼应当被划入中国诗歌理论的“诗缘情”派,他的观点与陆机在《文赋》里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两相对应,无论是“触景生情”“因情造景”,还是“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不过是技术手法的不同,追求的都是“物象关情”,不过,在笔者看来,从理路上说,李劼发展性地将“诗缘情”升级到了另一个层次:“诗人缘性情”。
在书中,李劼将王之涣、李白、王昌龄分别唤作“黄河少年”“陇西少年”“边塞少年”,其实,他的笔墨间就弥散着一种少年意气,富有意趣和才情,他痛恨浮夸造作,崇尚真情实感,尽管不少观点有待商榷,但《唐诗宋词解:诗为心声,词乃情物》写出了李劼的一家之言,这种不落窠臼、敢于挑战权威的独立精神,实在是做学问必须的品质。因而,对打小就被各种语文教材里的官方释解所包裹的国人来说,本书或可引发读趣和文思,并在另辟学术路径方面辅以有益借鉴。李劼无意改写诗词史,但他的眼光,锐利且清晰,带我们看清文采熠熠、群星闪耀的诗词史的夜空,令我们明白:读诗词,始于读人,也止于读人,读诗词是文学,读人是经世,乐趣横生,竟有别样滋味。
作者:潘飞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金久超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