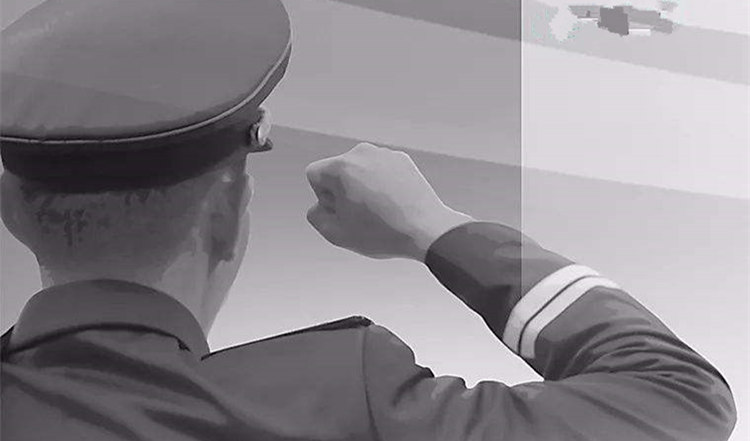
海男的新作《野人山·转世录》(《作家》2018年第六期)是一部关于时间和历史、遗忘和生命的小说,作者选择了二战时期中国远征军的故事,在处理的时候采取了较为私人化的方式。小说通过一群因各种原因走上旅途的旅行者重返野人山的经历,穿插了对当年战事的回忆,在主旨层面表达了战争的残酷及其给人类个体带来的无尽伤痛,也表达了对老兵的致敬、对坚韧生命力的敬畏和对遗忘历史的痛心。
《野人山·转世录》在结构安排上有两条线,历史和当下;叙述者则扮演了双重角色,在现世是一名作家,而前世的她则是一名战地记者。当现世的作家与经历过那场磨难的人们相遇时,作者把自己想象成亲历者,完全沉浸其中。小说的第二条线是一群旅行者重返野人山的故事,在旅行途中一步步揭示出那段经历的残酷与悲壮。小说没有对战争正面展开书写,而是通过一个特殊的身份进行回溯——通过几位老兵的相遇来写那场战事。这群远征军人最终留下了什么,是收藏家收藏不完,也是旅行者探索不完的。
小说主要叙述了几位老兵的故事,看似独立,实则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遭遇。旗袍女子周梅洁、牧羊少年的爷爷黑娃、收藏家的父亲,以及重返野人山时在野人部落所遇见的老兵,这些人的故事通过前世的回忆与现世的遭遇一点点浮现出来。小说对战争的正面描写较少,而是通过坟墓、记忆、讲述,将那些残酷的画面点点滴滴呈现出来,比如关于运送粮食的描写,关于收藏家爷爷身体里的子弹,关于野人部落老兵失去的腿与臂等,都是如此。而关于周梅洁的书写贯穿始终。在叙述者的前世里,周梅洁因战争期间与丈夫离散,被带到缅北做了慰安妇,战争带给周梅洁的恐惧一直存在于她的心上,她能走出野人山,却无法走出自己心中的魔山;在叙述者的现世里,旗袍女子周梅洁开启了新的生活,并选择了自我遗忘,而叙述者也选择隐去她痛苦的遭遇,但是很明显伤痛是无法真正被遗忘的。
海男的写作往往以个体化的情感介入宏大的历史之中,比如之前的《热带时间》。《野人山·转世录》中作者也采用了较为私人化的方式来处理这段宏大的历史,无论是自始至终的超现实书写,还是具有文体意识的小说文本本身都是如此,神秘书写与非自然叙事贯穿全书。小说中有一个场景,就是重返野人山的一群人在描述各自的前世,想象自己的前世,还有野人部落老兵描述关于轮回的奇异事件,这种非自然的书写在这样的主题中并不突兀。同时,这也是一部文体小说,海男自诩三分之一是诗人,三分之一是散文家,三分之一是小说家,而这部小说刚好既有小说的情节,也有散文化的文笔,更有诗的意境。在《热带时间》中作者将诗歌排印在小说中,而这部《野人山·转世录》则是诗和小说融为一体,浑然天成。这种小说的诗性化与海男的诗歌散文创作不无关系,近期她发表的长诗《幻生书》有很多意象和书写也涉及到了《野人山·转世录》的主旨。
这更是一部记录历史、祭奠魂灵之作。海男长期生活游走在云南边境,恰好是这段历史的发生之地,也许正是经历了多次的漫步与思索才换来了这部小说。尤其是转世轮回观的介入更能凸显小说的哲理性。这不仅仅是对战争的书写,更是从人性的角度思考人生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从开篇两名女子走出野人山所创造的生命奇迹到全文结束时关于生命力的论述,作者始终在表达一种生命的坚韧品性,这也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时代精神。
战争的灾难与悲苦是无法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的,作者对这些遭受战争变故的人物的命运进行了深度书写,对他们的遭遇进行了全方位呈现。当下战争题材被反复书写,但很多仅仅是蹭题材的写作,而海男这种代入式书写则体现了一种虔诚的写作态度,既铭记了历史,更反思了现实。
作者:刘小波
编辑:李伶
责任编辑:周怡倩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