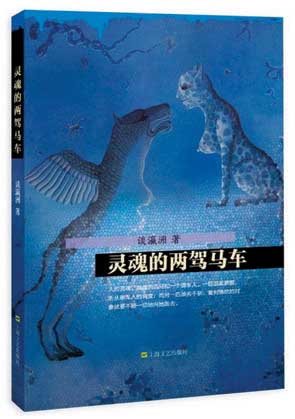
《灵魂的两驾马车》谈瀛洲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王宏图
在我为数不多的朋友里,谈瀛洲是很特别的一位。由于家庭成长背景、性情气质等方面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我从1997年和他相识起,心中便滋长出天然的亲近感。很多时候,不用夸张喧嚷的语词,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便足以使我们心领神会。我们俩同在学院中,又都有从事文学创作的爱好(有时它演化为执念),这更拉近了我们间的距离。
谈君早先专攻莎士比亚,又多年教授英美戏剧课程,在世纪之交的数年间一气创作了《梁武帝》《王莽》《秦始皇》三部大戏,其主人公都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君王,其功过是非一直聚讼纷纭。作者笔力雄健,字里行间萦回着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麦克白、理查三世等人的流风余韵。此外,谈君还在小说方面颇多用力,其新作《灵魂的两驾马车》最早的稿本是用英语写成的。这真可谓一次跨界的写作,他试图用一种异域的语言展示本土丰沛繁杂的生活经验,在语词与意象的交错互换撞击中孵化出奇特的美学效果。
单就情节而言,《灵魂的两驾马车》并不出奇,甚至有些狗血:少年得志的名牌大学教授胡长根与女作家文艳不期而遇,随即产生了一场危险的恋情,这使得他原本的家庭岌岌可危。尽管经过漫长的情感折磨,胡长根和妻子素芬力图重修旧好,但素芬在心灰意懒之中携女移居加拿大。而胡长根则往返于大洋两岸,疲于奔命,心力交瘁,陷于进退两难的死胡同。
然而,也正是在这貌似乎狗血的情节中,谈君写出了为一整代人共享的经验:令人迷惘心酸的中年危机。它和青春期的躁动不同,由于年龄的增长,使人不再有勇气理直气壮地喊出“谁的青春不迷惘”,但它又萌蘖于人的两度青春。和年轻时的一无所有不同,胡长根们经过多年打拼,总算事业有成,攀上了等级阶梯的上层,但扪心反省,陡然发觉自己孜孜以求的生活(事业和家庭)原来是那么苍白无趣,改弦易辙之心油然而生。然而,到了这个年龄,他们瞻前顾后,早已失去了年轻时的果敢决绝,虽多了几分成熟,也失去了义无反顾的豪迈之气。因而胡长根才会意识到自己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在当下这个时代,一个人很容易钻进死胡同,然后就卡在那里不能动弹,最后连行动的意志也完全失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病相怜的人们可以说,我们都是胡长根。
在全书临近结尾处,谈君用了不少篇幅,引用柏拉图对话《斐德若》篇中驾车人、两匹马的相关比喻,力图展示人类灵魂复杂错综的图景。而胡长根最后的犹豫不决也成了柏拉图的这一话语的鲜明例证。面对先前的学生、现在的年轻同事谷薇爱的表白,胡长根一方面战战兢兢,心存恐惧,一旦接受她的爱,将给他原本已残缺的生活带来难以控制的大变局,而新一轮情感的折磨与冲突在所难免;另一方面这似乎又是他重获生机、重新感觉到做人的滋味的惟一机会。结尾时我们看到长根对谷薇说出“我留下”,但人们发现他是用干涩的声音吐露这一心声,不禁为他能坚持多久而产生疑惑。也许今晚他是留下了,但第二天第三天……也许不多久,他又会重新回到妻子素芬的身边,一切如旧。因而,这是一个开放的结局,更是一个不确定的结局,充满着种种变数。
在陪伴胡长根走过那一长段情感的炼狱之后,人们不难发现,他之所以会长时间地陷于死胡同之中,就在于丧失了行动的意志。行动意志的缺失心然导致在人生的关节点上缺乏选择的决断力量。我们可以寻找出众多的理由为胡长根辩解,但究其根本,这也是现代文化孵化出的苦果。我们不像古代的先贤那样尊崇正义、节制、虔敬等德性,个体的感性欲求成了至高无上的价值,因而我们失去信仰的依托,首鼠两端,进退失据,踯躅徘徊。这既是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病症。要改变这一切,也许只有要一点野性,一点赌徒的狂热与鲁莽,像里尔克如下诗句所言,用更广阔的心胸,来容纳世界的种种变迁与动荡:
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
——我赞美。
但是那死亡和奇诡
你怎样担当,怎样承受?
——我赞美。
……
怎么狂暴和寂静都像风雷与星光似乎认识你?
——因为我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