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瘦鹃早年写过大量的言情小说、剧本和电影,翻译过外国文学作品;晚年在花木丛中享受劳动和审美的人生,又就园林艺术花花草草写下了大量的小品文字,鸳鸯蝴蝶之缠绵悱恻一变而为花花草草的沁人心脾。
老派江南才子周瘦鹃(1895—1968)乃一代奇才,他不单是知名度极高的作家、翻译家、编辑,又是资深园艺专家——他在上世纪30年代以其余力略仿古人画意创作的盆景,就轻而易举地获得过上海国际性花会的锦标。
周先生早年写过大量的言情小说、剧本和电影,为鸳鸯蝴蝶派“五虎”之一(其他四“虎”是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张恨水),拥有广大的读者,其“粉丝”的数量比起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名家来要多出许多;他早年翻译的欧美短篇小说,得到过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后来又译出过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其中有不少成了畅销之书;他编辑的几种刊物如《礼拜六》《半月》《紫罗兰》等等,皆名闻遐迩,风行一时;他为《申报》先后主持过名牌副刊“自由谈”“春秋”,亦办得风生水起。一个文人只要做好其中一个方面的事情,即足以名家,而周先生却以其瘦弱之躯为几项高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1949年以后,社会和文学全都发生了巨变,鸳鸯蝴蝶、哀情惨情那种老一套显然是不行了,刊物和报纸副刊也都不是先前那种编法,周先生的强项失去了用武之地,于是他明智而不动声色地将工作重点转向全力经营他的生活生产基地“紫兰小筑”,为时未久,这里即名声鹊起,成为园艺、盆景工作者心目中的绝顶高地,宾客盈门,络绎不绝,他老先生也得以在花木丛中享受劳动和审美的人生,比历史上著名的隐士陶渊明要滋润多了。
而周先生的大本领又不止于此,在亲自栽花种草之余,他又就园林艺术花花草草写下了大量的小品文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结集为《花前琐记》《花花草草》《花前续记》《花前新记》《行云集》《花弄影集》等六本小品随笔集,集外还有大量的文章,凡此种种皆由鸳鸯蝴蝶之缠绵悱恻一变而为花花草草的沁人心脾,并继续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周先生这些小品随笔集绝版已久,现在要搜寻齐全,殊非易事;近日的一大盛事是中华书局今年2月推出了一个新的汇编本,囊括《花前琐记》等六书,而总名之曰《花花草草:周瘦鹃自编小品文集》。整理此集的是当今以优质高产著称的苏州才子王稼句先生。这份新的汇编本校订精细不苟,水准甚高,印制亦清雅大方,与所收之美文相得益彰。一卷在手,馨香满室,令人获得审美的享受和愉悦的休息。
周先生小品随笔的内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除了漫谈我所喜爱的花木事以外,也谈及文学艺术,名胜风俗,等等,简直是无所不谈;一方面歌颂我们祖国的伟大,一方面表示我们生活的美满”(原本《花前琐记·前言》,汇编本《花花草草》第4页)。
这里无所不谈的重点在于下列四个方面:花草、游记、民俗、文艺。
花草盆景是周先生的最爱,他那私家花园“紫兰小筑”(外人称为周家花园)创建于20世纪30年代之初,其来历他曾经详细介绍过:
早年在上海居住时,往往在狭小的庭心放上一二十盆花,作眼皮供养。到得“九一八”日寇进犯沈阳之后,凑了二十余年卖文所得的余蓄,买宅苏州,有了一片四亩大的园地,空气阳光和露水都很充足,对于栽种花木颇为合适。于是大张旗鼓地来搞园艺了。……以后几年,我惨淡经营的把这园子整理得小有可观,又买下了南邻的五分地,叠石为山,掘地为池。在山上造梅屋,在池前搭荷轩,山上山下种了不少梅树,池里缸里种了许多荷花,又栽了好多株松、柏、竹子、鸟不宿等常绿树作为陪衬……一年四季,差不多不断地有花看看,有果可吃了。(《花前琐记·花木之癖》,汇编本《花花草草》第62页)
这样的风水宝地花花世界,在后来的苏州,以至于更广的地域,大约只此一家,到现在以至未来都似乎难以复制。在这四亩五分的园林里,花草树木、盆景水石,丰富多彩,美不胜收,文坛耆宿随便写一点,便成妙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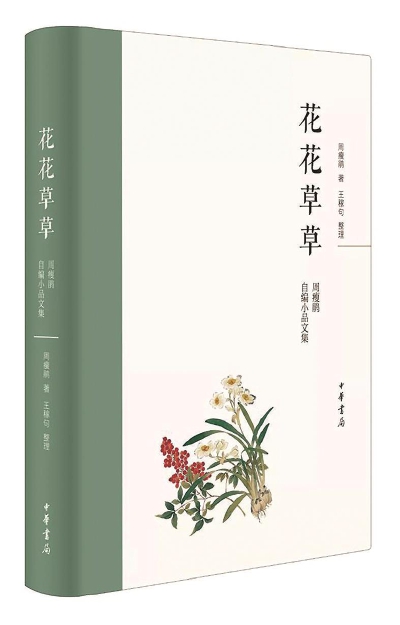
周先生在传统的江南社会生活里浸泡过很久,他又是非常关心世俗风习的,所以谈起民俗来,亦复头头是道,趣味盎然。《上元灯话》《端午景》《乞巧望双星》《送灶》诸篇,娓娓道来,皆为绝妙好辞。
周先生的游踪虽不甚远,主要是苏州本地和附近的无锡、宜兴、扬州、上海,略远一点也就是浙江、安徽、江西、广东,但游兴甚浓,极有审美眼光,文字亦颇佳妙。地不在远,人到则灵。这一方面的华章,比较集中地见于原本《花花草草》的第二辑和《行云集》,又散见于其他各集。偶有重复(如《花前新记》里有一篇《石公山畔小勾留》,到《花弄影集》中又有同题之作,内容大同小异),当年是收在不同的集子里的,未足为病。
文学艺术在周文中所占比重不算大,但颇有值得关注者,这里涉及陶渊明、白居易、陆龟蒙、唐伯虎、弹词《红楼梦》、越剧《梁祝》、昆曲《十五贯》、杂志《礼拜六》、苏联电影《黑孩子》等等,皆多有可观。涉及鲁迅者除专篇的《一瓣心香拜鲁迅》之外,又曾说起1956年10月他与许广平见面时的对话:
当晚在十一层楼上会见了神交已久的许广平先生,她比我似乎小几岁,而当年所饱受到的折磨,已迫使她的头发全都斑白了。许先生读了《文汇报》我那篇《永恒的知己之感》,谦和地说:“周先生和鲁迅是在同一时代的,这文章里的话,实在说得太客气了。”我即忙回说:“我一向自认为鲁迅先生的私淑弟子,我觉得我这一枝拙笔,还表达不出心坎里的一片景仰之忱。”(《花前新记·上海大厦剪影》,汇编本《花花草草》第319页)
《永恒的知己之感》(《文汇报》1956年10月13日)一文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而作,主要讲他早年得到鲁迅夸奖的往事。当年他的译本《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报送教育部审查注册时,得到了很高评价,其评语是由教育部官员、通俗教育研究会骨干鲁迅草拟的(其弟周作人亦有贡献),该评语先报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核,再由教育部批准,于1917年9月22日以教育部指令的名义发表(后载于《教育公报》第四年第十五期,1917年11月);9月24日又发出了由教育部次长、通俗教育研究会会长袁希涛签发的“褒状”。周瘦鹃非常重视这份荣誉,自己早年的工作得到过鲁迅的高度评价,他终身感激不尽。
此事无论在鲁迅还是在周瘦鹃,都是很有意味的文化掌故。笔者曾经专门讨论过此事(详见拙作《与鲁迅有关的几部书·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2期),这里就不去多说了。
整整一百年前,鲁迅还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1919年11月1日)上向鸳鸯蝴蝶派作家喊话,建议不必写那种表达“哀情惨情”的小说,多介绍些外国文学中的优秀作品,这样于读者才有益。他在文章中热情地呼吁道:
江苏浙江湖南的才子们,名士们呵!诸公有这许多文才,大可译几叶有用的新书。(《热风·“随感录”六十四·有无相通》)
劝鸳鸯蝴蝶派才子译书,并非突发奇想,因为鲁迅知道他们是有能力译书,并且是做出过成绩的,不久前他予以高度评价的周瘦鹃译本《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就是眼前的一个实例。
鲁迅希望鸳鸯蝴蝶派转轨,当时该派中也确有几个人(如刘半农等)转了过来;但周瘦鹃当时没有转。周先生的转轨要等到全国解放以后,也不是转入文学翻译,而是转到了他早就有很大兴趣、有坚实基础的园艺方面。
解放以后由著名作家而转轨成功的高人主要是两位:北有遁入文物服饰的沈从文(1902—1988),南有隐入花草盆景的周瘦鹃。比较起来,周先生转的幅度小一点,他没有离开文学,只是转换了题材和文体;后期沈从文先生则离文学很远了——他转轨转得更彻底,也可以说更明智。
沈先生隐遁于故宫的午门之内,地点虽近政治中心,却藏得深;周先生虽然归隐于远离朝市的“紫兰小筑”私宅,却因芳声远播,宾客不绝,实际上隐得甚浅。沈先生熬过了“文革”,而周先生则未能,竟于1968年8月12日深夜投井而死。
幸而那种“史无前例”的荒唐早已成为过去,在他含冤去世50年后,其自编小品文集六种得到很好的整理,重新与读者相见。凡是美好的东西,总会像上品的盆景一样,老桩铁干虬枝,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作者:顾农(作者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文汇理评部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