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大门在清末被欧洲人洞开之后,国人先是在器物层面上“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求自保。但是,这种策略随着甲午战争硝烟的散去而归于失败。与之不同的是,一些知识精英试图从精神层面进行反省与图新。其中之一是通过文献译介以及教育与研究而对西方经济思想进行传播。当然,这种传播也具有选择性,摸错了路数和走岔了方向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有些是已觉之痛;但是,更值得警惕的是“未觉之痛”。
历史地看,西方主要国家出于战略考虑,往往选择性传播其经济思想,以营造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人最近百来年里通过多个途径传播西方经济思想,在全面抗战之前的民国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最近30多年各形成了一次高潮。这些传播也具有选择性。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应该以适合真实的需要为旨归,对看起来完美而实际上有害于当时发展的经济思想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以避免“未觉之痛”。
思想传播具有选择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思想的选择性传播自觉或不自觉地打上了人为的烙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国家出于战略考虑而对思想资源进行有目的地采择和宣扬。对此,无论专门研究思想史的人,还是与之有涉的任何其他人,都必须加以注意。这里我仅就西方经济思想选择性传播史简要地谈两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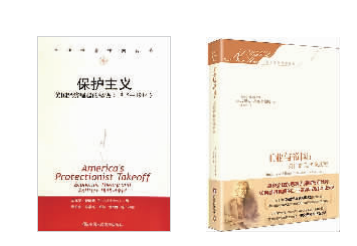
西方:英、美、德的选择性传播
对于最近200多年世界历史的发展,英国、美国和德国都曾产生过方向性影响。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并且,在与经济有关的政治和军事等方面,无论令人欣慰还是使人痛苦,都已成为记忆中最深刻的部分。英国、美国和德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国内资源禀赋和国际经济环境等条件,彼此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它们之间的竞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崛起都是围绕国家间竞争而展开的。在人类社会,只要还存在国家,大国崛起与守成就是不谢幕的主题;国家间竞争的战略考虑融入大国及潜在大国政治家的思维模式,经济思想的传播具有选择性也就不足为奇。
1、英国。不能否认的是英国崛起与这个国家持续几百年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存在直接的关系。特别是从工业革命开始至19世纪中叶,英国借助《航海法》《谷物法》和保护关税等重商主义政策,通过国家干预成就了无可匹敌的工商业霸权。按常理说,重商主义作为英国崛起的国家记忆是会被大书特书的,但是,历史总有出人意料的地方。
这就要提到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以及它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判若云泥的际遇。在这本著作中,斯密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线,串连起关于国家财富及其原因的一整套观点,编排有致,褒贬分明。但是,这本著作中几乎所有的观点,都不是斯密原创的。另外,既然拿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主线进行串连,就有必要表明如下态度:英国过去几个世纪通行的以及当时仍在采用的重商主义政策违背了自然而又自由的原则,它们是错误的和没有必要的政策。从上述角度来说,斯密对于经济思想的贡献,不在于发现和阐述了具体的经济学原理,而在于对经济思想体系进行了最初的构建与纯化。
斯密的《国富论》甫一出版,就在大众层面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例如,到他去世后一年即1791年,该书在15年里发行了5版,共约6750至7250册。但是,一种经济理论若要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的高度,非得被主要的政治人物接受并且在一系列重要的政策上体现出来不可。而事实却是:在英国议会辩论中,在《国富论》出版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也即1800年以前,斯密的话很少被引用(他在经济学家当中仅排在第九、第十的位置),诸如洛克、休谟、配第等人的语录才是政治家们惯常引用的。不过,随着英国工业、外贸和海军等势力进一步增长,这种格局发生了变化——自19世纪初开始,斯密语录被引频率上升了,《国富论》逐渐被神化到了经济学圣经的高度。
《国富论》出版半个世纪之后,英国在重商主义政策支撑下已经建立起足够的力量和自信,政策上向经济自由主义转变正是合适的时机。通过这种转变,英国的战略目标演变成了塑造一个以自己为中心而与外围国家共同构成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英国处于有利的分工地位和占优的分配格局。当然,这一切都是缓慢进行的。英国经济政策的表现是:从1826年开始关税率逐渐降低;1840年代相继废除了《谷物法》和《航海法》;1860年与法国签订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全球第一波贸易自由化浪潮得以开启。与上述政策转变相伴随,英国以国内自由竞争与国际自由贸易的名义,向全世界传播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希望他国与之相向而行。
2、美国。建国之后究竟以怎样的经济思想作为发展战略的指导,杰斐逊的以农立国派与汉密尔顿的工商立国派曾经产生过激烈的争论。杰斐逊与汉密尔顿都是了解斯密经济思想的。但是,杰斐逊看重的只是斯密经济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对美国发展农业和自由贸易情有独钟;汉密尔顿却与之不同,不仅看重斯密经济思想中的分工和市场等学说,而且根据美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英法崛起的历史经验以及与欧洲列强竞逐的现实需要,还看重斯密在《国富论》中大加挞伐的重商主义政策,并且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提出了美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和具体手段。总体来看,在美国崛起时代(1789年至1913年),尽管在学院派经济学中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占据了主流地位,但在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层面上,保护主义却得到了长期坚持。
这里所说的“美国体系”,主要包括关税保护、内部改善和国家银行这三个方面。其中除了国家银行政策(从杰克逊总统第二任期到1913年美国崛起以前)未予落实之外,关税保护与内部改善政策却是一以贯之的。其中,关税保护既为促进美国国内自由竞争提供了有效的庇护,又为以改善交通运输为主要方向从而实现美国国内产品、人员和资本的便利流动提供了财政支持。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主导的全球第一波贸易自由化浪潮中,美国并未与之相向而行,即也选择自由贸易政策,而是从南北战争开始一直与之背道而驰,即选择保护主义政策。通过大约30年努力,美国终于在1890年代取英国而代之,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并且,大约在1913年实现了全面崛起,随之迈入了“踌躇的霸权”时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时代才告终结)。
重要的是,“二战”之后的美国也像19世纪中叶的英国一样,取得霸权地位以后就采取了转向自由贸易的策略,其背后的战略构想其实是一样的;与之同时,在向其他国家传播经济思想的时候也与之类似,即以经济力量、政治手段和话语权等作为推手,争取它们与美国一样在国内培育自由竞争、在国际行使自由贸易政策。例如,“华盛顿共识”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它将自由贸易放到一个不容质疑的高度并且披上了道德的外衣。美国卖力地向其他国家宣扬自由贸易,其实是具有维护美国霸权的大战略考虑的。再如,成立于1973年的美国传统基金会在一份《使世界变得对美国安全》的报告中认为,自由贸易是美国五大利益之一(其他四大利益分别是领土与领空安全、防止大国威胁、获取资源和海上航行自由、保护美国公民生命与财产免受威胁),它是美国最好用的武器,破坏自由贸易是对美国全球重要利益唯一的非军事威胁。当然,在自由贸易大势下,美国并没有放弃保护主义理念,而是在“公平贸易”名义下策略性地对之加以利用。
从美国采用保护主义政策实现崛起、在守成阶段转向自由贸易政策并且向他国传播经济自由主义这一过程中也可看出,经济思想的选择性传播是国家间竞争的一种策略性手段。这种手段是通过学术组织、各种媒体、学历教育、国际条约等予以实施的。
3、德国。直到19世纪早期,德国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联邦国家,邦国间关口林立、交通不便、度量衡不统一。1834年的关税同盟使德国内部的竞争性市场开始形成,此后德国又实施了以大规模铁路建设为主要手段的经济发展计划。在俾斯麦手里,德国在1870年实现了统一,1879年实施了保护关税制度(尽管关税率比欧洲其他国家的低一些)。德国在国民教育和技术发展等方面也做出了持续并且富有成效的努力。其结果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德国与美国一道引领世界潮流,一跃而于20世纪初年成为欧洲经济之执牛耳者。这一切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经济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李斯特在德国一度也很受尊敬,被视为伟大的爱国者。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经济崛起之后,即使在德国,李斯特的经济战略思想也越来越少地被提及了。这当中
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有些学者认为李斯特的经济战略思想对德国走向纳粹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至于不便于大加宣扬。二是德国实现崛起之后,李斯特的经济战略思想已经不再适合于德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了,以至于即使在学术层面上对李斯特的研究兴趣也逐渐消失了。这也难怪,因为李斯特对于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只是认为斯密经济学仅适用于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即国家经济已经实现崛起,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已经具有足够的竞争力这样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斯特经济学其实是属于发展经济学的。三是由于德国经济崛起之后,其强大的根本正在于拥有超凡的工业能力,而李斯特经济学重要特点之一又是通过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来获得作为国家生产力主要体现的工业能力,这一招如果被其他大国学到手,势必对德国形成挑战。因此,德国也与英国、美国一样,喊的是自由贸易口号,甘愿让使国家获得光荣的本国经济学家即李斯特的经济思想归于沉寂。
在西方主要国家,出于国家战略考虑,经济思想被选择性地对外传播;在学术层面,经济思想的待遇也未尝不是如此。例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取得主流地位后,这派学者就再也容不下对立的意见,哪怕是对保护主义的同情了。英国人约翰·穆勒是19世纪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那个时代的标准教科书。但是,他在这部书中认为对幼稚产业实施短期保护是合理的。这就招致了同行的反对和鄙视,以至于不得不做出妥协(尽管他内心仍然认为幼稚产业保护是自由贸易的一个真正例外)。
中国:清末以来的选择性传播
中国大门在清末被欧洲人洞开之后,国人先是在器物层面上“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求自保。但是,这种策略随着甲午战争硝烟的散去而归于失败。与之不同的是,一些知识精英试图从精神层面进行反省与图新。其中之一是通过文献译介以及教育与研究而对西方经济思想进行传播。当然,这种传播也具有选择性,摸错了路数和走岔了方向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有些是已觉之痛;但是,更值得警惕的是“未觉之痛”。
1、1949年之前的选择性传播。在严复翻译《国富论》之前,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已有了零星的传播。但是,真正称得上是系统性传播的,却要数严复以《原富》之名对斯密的《国富论》进行的翻译和批注。这里,我要说的是他为什么选择《国富论》而不是其他西方经济学著作进行翻译。
1877年至1879年,严复在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他在课业之余,亦广为涉猎西方思想和文化。当时的英国,无论学界还是政界,遵循的都是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即使在美国,虽然政界较少受斯密经济自自由主义思想左右,但学界与英国相差无几)。当时正是英国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时候,英国人是把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国家富强的思想基础而对外进行传播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深感甲午之痛的严复,抱着一颗国家求富求强的拳拳之心,翻译了《国富论》。那时,他是没有条件追问更加深刻的问题的,即在西方经济思想中,究竟哪些学说才最适合于中国的求富求强,中国之求富求强,究竟需要遵循怎样的经济战略思想,等等。严复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还没有翻译到英国,严复在翻译《国富论》之前,可能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英国是在重商主义政策的支撑下实现崛起的,美国是在保护主义政策的庇护下实现崛起的,日本是在由本土激进重商主义与欧洲重商主义糅合而成的明治维新政策的支撑下实现崛起的。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在崛起过程中采用的经济政策,正是斯密在《国富论》中大加反对的。也就是说,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来说,严复翻译的《国富论》并不是真正有用的西方经济思想。这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未觉之痛”。
直到1927年,李斯特的传世之作才以《国家经济学》这个题目由王开化译为中文。那时的中国,大抵形成了马克思经济学、斯密经济学与李斯特经济学相互竞争的局面。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不用说斯密经济学,即使是李斯特经济学,其赖以发挥效力的前提也是不成立的——本质上属于发展经济学的李斯特经济思想要能发挥促进国家经济崛起的作用,一个必要的前提是国家统一并且具有独立的制定对内对外政策的能力。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些都不是真正具备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面抗战之前的民国时期里,中国形成了一个传播西方经济思想的热潮,相关的翻译和著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翻译的主要有:韩纳(Lewis H. Haney)的《经济思想史》(臧起芳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日]出井盛之的《经济思想史》(刘家鋆译,上海联合书店,1929年);托托门兹(Totomientz)的《经济思想史》(卫惠林译,民智书局,1930年);[俄]鲁平的《新经济思想史》(陶达译,好望书店,1932年);斯班(Othmar Spann)的《经济思想史》(詹文浒译,世界书局,1933年);斯科特(William A. Scott)的《经济思想史》(李炳焕、黄澹哉、黄俊生合译,黎明书局,1936年)等等。国人自撰的主要有安绍芸的《经济学说史纲要》(世界书局,1930年);蔡庆宪的《经济思想小史》(大东书局,1932年);金天锡的《通俗经济思想史要》(神州国光社,1932年);朱通九、金天锡的《近代经济思想》(黎明书局,1932年);郑毅生的《经济思想史》(世界书局,1935年)等等。就1949年之前而言,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赵迺抟根据20年讲演精华辑成的《欧美经济学史》(正中书局,1948年)。这是我国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最精当的著作。例如他锐利地指出,重商主义在19和20世纪对欧美的法律与政策仍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即使从现代经济理论的角度来说重商主义政策也有无可厚非的地方。这就不仅与重商主义流行于16至18世纪的欧洲的传统认识形成了分野,而且与只有经济自由主义才具有道德和学理的合理性的主流认识形成了分野。
总体而言,建国之前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所具有的特征是:在懵懂之中,全盘接受西方主流观点,这种“觉而未觉”的状态,本身就包含了极大的危险性。这里,“觉而未觉”是指:已觉得要向西方学习经济思想,但是在向西方学习什么样的经济思想这个问题上,眼中却又只有“主流”,而很少进一步追问西方的主流经济思想是不是真的适合于当时的中国,以及什么样的经济思想才是当时中国所真正需要的。
2、1949年之后的选择性传播。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对西方经济思想总体上是持批判态度的。其中,最著名的教材要数鲁友章和李宗正主编的《经济学说史》(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这种选择性可能与如下两个方面有关:一是认为价值问题乃经济学中心问题,而西方经济思想中存在诸多非劳动价值论的学说;二是苏联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而西方经济思想是以市场理论为基础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30年里,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再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而其渠道一变为四了。一是通过引进原版、翻译或自己编写《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教材以及教学而进行的传播。这个传播渠道的受众面非常大,不惟经济学专业,高校学生几乎都不难接触到。二是通过引进原版、翻译或自己编写《西方经济思想》和《外国经济学说》等教材以及教学而进行的传播。这个传播渠道的受众面较小,主要涉及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三是专业人员针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时,广泛使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而进行的传播。四是其他社会人士通过各种途径碰触西方经济思想而实现的传播。上述第一个方面,讲的几乎完全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它抛开了与经济思想史、经济政策史和经济史的联系,更不用说比较客观地说明经济思想的演变路径及其与各国经济阶段性发展的需要是否适合等历史与现实问题了。于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选择性特征,即基于个人自由的西方主流经济思想,在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几乎占据了主要地位,而这样的经济思想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契合起来,对此却没有给予足够
的关注。这也会产生“未觉之痛”。比如说,很少再去思考如下问题:自由贸易是否会将中国锁定于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使中国在国际经济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以至于在国际经济格局中一直位居外围?中国应该怎样构建对外经济战略,才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和国家竞争力提升?
有鉴于此(但不限于此),最近几年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通过种种努力,尽量去除西方经济思想传播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成分。比如,对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在崛起时期采用的经济政策等加以挖掘和整理,同时译述外国学者与此有关的优秀著作。单就翻译的作品而言,就包括了[美]迈克尔·赫德森的《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等等。这些工作是对过去一段时期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失当的选择性传播做出纠正的有益努力。其主要目的是还原历史真相,尽可能避免前面提及的“未觉之痛”。遗憾的是,这样的工作开展得还不够,产生的影响还没有达到预期。
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并不是想说从西方经济思想库中能够找到某种或某些理论,只要做适当的时空挪移,就可直接用之于确立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和战略手段——如此重要的工作,只有靠中国人自己去完成;而是与之相反,即中国人在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一方面,可以从西方经济思想中汲取有用的成分,另一方面,不要对西方经济思想做不当的选择性传播和吸收,以至于偏离了真实的需要。总之,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曾经说过的话,即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对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吸收,也应作如是观。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教授,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重商主义传统与新形态研究[17BJL021]”资助)
文: 伍山林
编辑制作:范菁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