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居家求学(二十三)
我在业余时间学习、研究散文。进入当代散文的阶段后,陆续买了各家的集子,多年前就读过了。这些朴素的散文集,现在就放在书柜里,从出版时间说,是真正的旧书了。但是,在整理藏书时,我把许多书拣选装箱送人,却舍不得清理杨朔、秦牧、吴伯箫等前辈的作品集。如果以金钱衡量,这些小书不值钱,也没有增值的潜力,现在愿意读的人也不会多。我迟迟不能“断舍离”,只能说明我和这些小书有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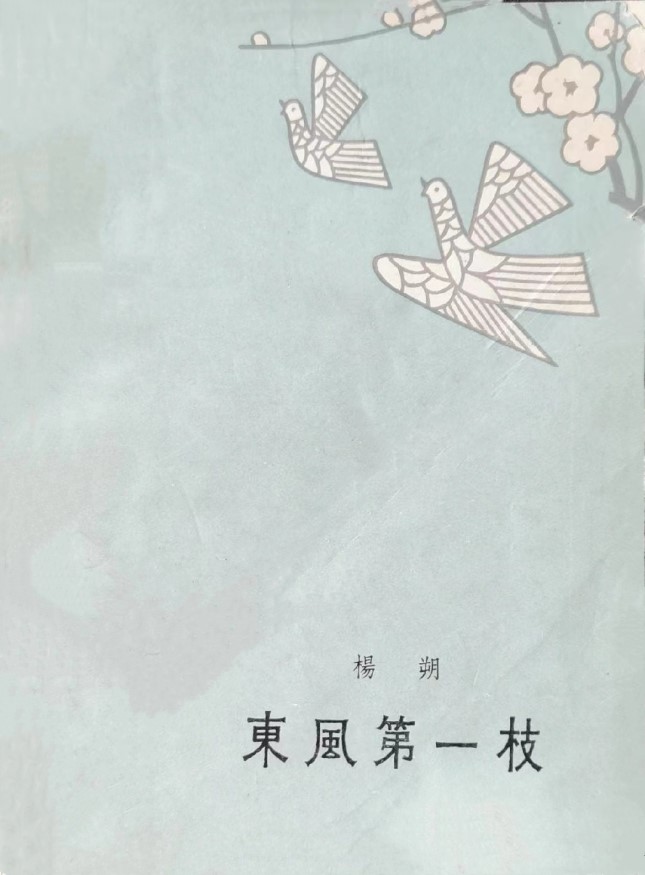
杨朔的多篇作品曾入选语文课本,凡是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对之并不陌生。他的作品,好读好教,是训练作文的好教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散文作品不仅在课堂,在社会青年中也有大量的读者。站在今天的高度,再回头看他在那个时期创作的散文,我们当然会指出他作品的不足之处,还可以写出更严苛的评论。我学习、研究过他的全部作品,曾给天津的《散文》杂志写过一篇读杨朔散文的心得,分析他的创作思路和艺术手法。我那篇短论没来得及说,杨朔这一代知识分子,是在革命队伍里进行过长期的思想改造的。他在克制自我的思维中,把小我融入大我,在锦绣河山里嵌入劳动人民,以诗情画意讴歌新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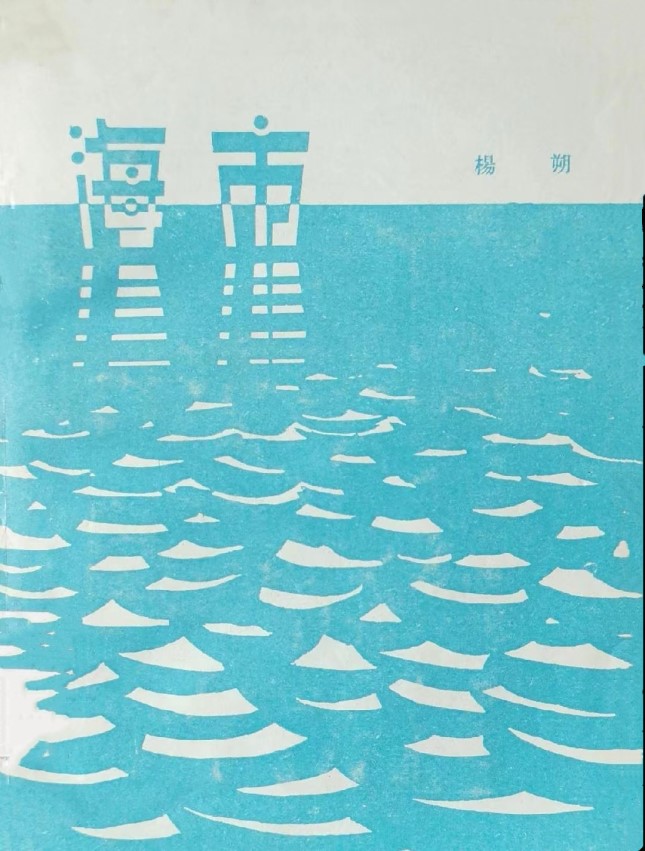
他说他是以写诗的方法写散文,这是对散文的高要求,最重要的是,身置新时代,歌之舞之,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杨朔是个高雅、整饬、文质彬彬的人,读丁宁《幽燕诗魂》,可略见他的潇洒风度。我有一年去沈阳,一个朋友带我去拜访马加,马的夫人谈起杨朔,笑着告诉我:“我们去他家,他家里摆着好多外国的玩意儿。”杨朔长期在外事部门工作,经常出国,那些外国的“玩意儿”无非是国外赠送的纪念品。杨朔琢磨这些精致的外国玩意儿,在艺术品里体会散文的形式和内容。他的作品中,凡是以海外风情为题材的,都写得自由洒脱、多姿多彩。我读他的作品,很容易学到他的写作手法,但他的全部作品里体现的高尚的情操,我是要学一辈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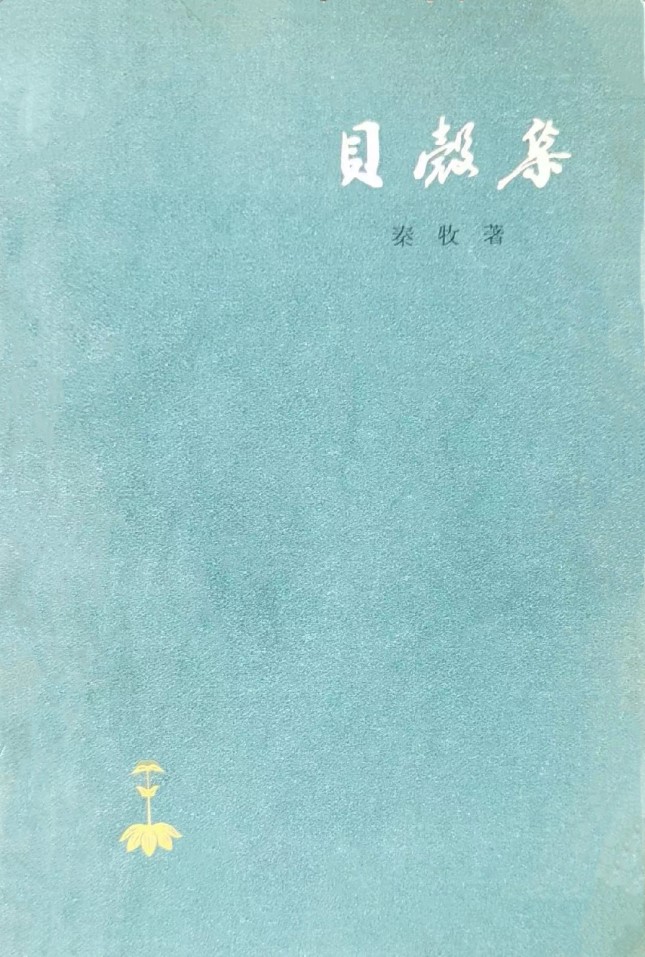
秦牧的散文,是标准的、优秀的报章时文。他能紧跟形势,快手写出一篇文笔犀利、潇洒自如的随笔。时政性、知识性、战斗性,在他的许多杂文随笔里溶为一体,而且富于亲和力。如说继承,他是从鲁迅的杂文学的。他向读者介绍过他写作的经验:“每个人把事物和道理告诉旁人的时候,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这里采取的是像和老朋友们在林中散步,或者灯下谈心那样的方式。我在这些文章中从来不回避流露自己的个性,总是酣畅淋漓地保持自己在生活中形成的语言习惯。我认为这样可以谈得亲切些。”他心里有读者,以交心的方式写文章,以本来面貌示人,绝不以牧师的口气教训读者。这也是从鲁迅那里承续的:我时时解剖别人,但也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作为当代散文的大家,秦牧的风格就在这些不大为人注意的地方。我孤陋寡闻,不知现在还有没有人读秦牧的散文?

《记一辆纺车》是吴伯箫的代表作。吴伯箫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且在会议上有个发言。他的这篇代表作,通过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增强了革命必定成功的信心,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文化工作者,也在劳动中来了一场精神的洗礼。这篇作品,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优秀教材,也是抒情叙事散文的范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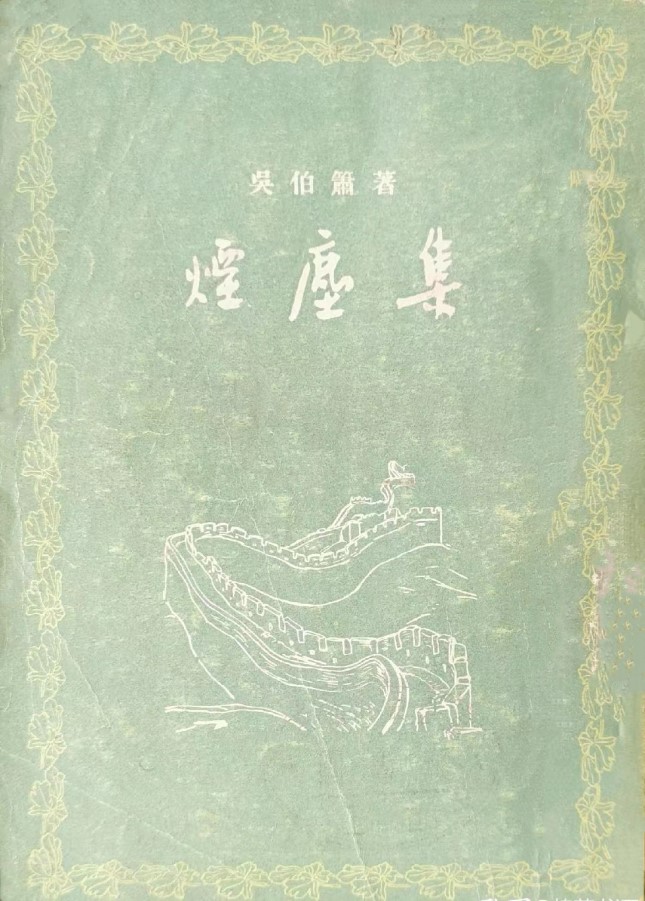
在《北极星》跋里,吴伯箫回忆起这样一个经历:
我参加了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座谈会开了三次。记得第二次以后的哪一天,我从延安南门外去杨家岭接洽工作,骑了一匹马。工作接洽完了,从杨家岭出来,远远望见毛主席同两位同志从延河岸边散步回来,正走上渡口通大道的斜坡。这时候我有些踌躇:立刻跑到毛主席跟前去呢,还是牵马在道旁等毛主席走过呢?都觉得太突然。这踌躇是一刹那的工夫。就在这一刹那间,毛主席仿佛知道了我的心情,已经叫着我的名字挥手招呼了。我便立刻跑到毛主席跟前去,握了手。毛主席问了我的工作情况,还谈到我在座谈会上简短的发言,说:就应当那样讲。
吴伯箫记述的这一段史料,也是他散文创作的政治的、历史的背景。领袖和一个普通的文化工作者的亲密关系,通过吴伯箫的记述,留在了新中国的文学史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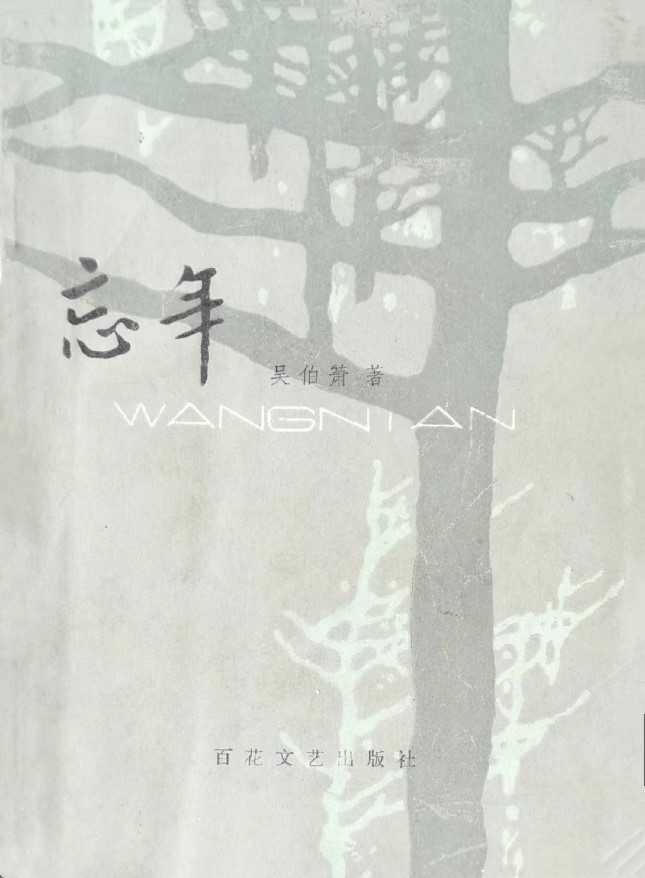
杨朔和吴伯箫,都是按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的方向进行文学创作的。秦牧是华侨,视野更宽阔,在创作思想上,他也回归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的大方向,不过,他的作品更属于城市读者和报纸的一时之需。这三位前辈的散文作品,影响了一个时代,引导了读者的文学趣味,提高了青年的写作能力。回头看,三家的散文作品,已进入历史的长廊。今天的读者和作者,大多数人已超过这些前辈,已经攀登泰山的几千级台阶。回头看,当他们凌绝顶时,怎能忘记自岱庙一路登山,抬脚迈上的第一级台阶?
旧书难舍。
>>作者简介:
卫建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著有散文随笔集《寻找丹枫阁》《陈谷集》等。
作者:卫建民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