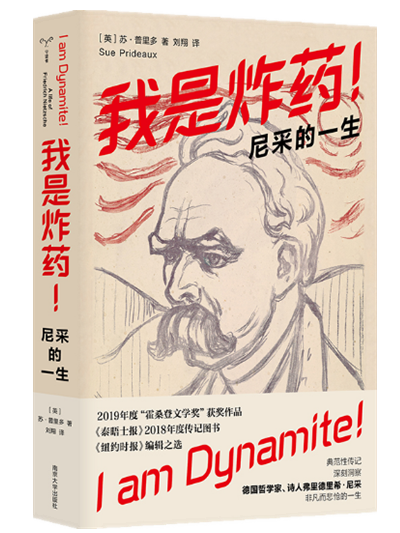
《我是炸药!——尼采的一生》
[英]苏·普里多 著
刘 翔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其自传性著作《看哪这人》的《我为什么就是命运》一文中,尼采以顽固的自信道出了他的命定性:“我知道我的命运。有朝一日,我的名字将与对某个重大事件的记忆密不可分——某种地球上空前未有的危机,一场最深刻的良心冲突,一项与人们迄今所相信、所要求、所奉为神圣的一切相悖的决定。我不是人,我是炸药。”果如其言,尼采如今已是伟大的哲人王,他的哲学思想也在人类文明的圣殿中熠熠生辉。
《我是炸药!》的作者苏·普里多以冷静客观的笔调,呈现了尼采卓越而又悲凉的一生。这部传记刺破了这位哲学巨擘的面纱,描绘了一个真实生动、丰富多样的尼采形象。根据尼采“所有哲学都是自传”的理念,记录一位哲学家的人生,必然无法脱离其著作和思想,作者将尼采的人生与作品巧妙地融合起来,讲述了他的生命历程是如何催生出一部部富含理性与沉思的哲学著作,以及这些哲学著作又是如何构成了他一生中最为绚烂多彩的人生风景的。
尼采极为喜欢品达《皮西安颂歌》中的一句诗:“认清你之所是,成为你之所是。”一个人对个体命运和宏大主题的追寻与探索,其实也是对内心自我的反复审视与观照。自我是外部世界的桥梁,只有认清了自己,才能走出洞穴,成为真正的自己。尼采身为牧师之子,成长于一个虔信基督的家庭,本应承继父辈道路的他,却逸脱于既定的路线,不仅大胆宣称“上帝死了”,还成为了“西方历史上最坚定的敌基督者”。在这一过程中,阿图尔·叔本华和理查德·瓦格纳是塑造尼采哲学观的两位重要导师。
叔本华是对尼采产生深刻影响的哲学家之一,甚至被后者称为“我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教育者”“我的先驱”。他是公认的悲观主义哲学家,也是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和宿命论者,尼采曾疯狂痴迷于叔本华的哲学,并从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除了叔本华,瓦格纳也是尼采的“偶像”。两人于1968年11月相识,31岁的年龄差,使得瓦格纳更接近于尼采生命中的“君父”。在尼采担任巴塞尔大学语言学教授期间,瓦格纳恰好定居在相距不远的卢塞恩湖畔的特里布申别墅,出于对叔本华和音乐的共同热爱,以及对无神论的深刻认同,两人开始了频繁的交游。正是在这期间,尼采写出了第一本著作、献给瓦格纳的《悲剧的诞生》(原名为《悲剧从音乐精神中诞生》)。
但最终,两人在尼采心目中都滑落为“偶像的黄昏”。尼采在成为己之所是的道路上,都是先仰望、继而跨越了这两座高耸的大山。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在洞察了“理性与本能、生活与艺术、文化世界与人类”之后,提出了著名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日神体现在雕塑、绘画、建筑以及梦境之中,与叔本华的“表象”相对应,其原型为太阳神阿波罗;酒神的原型为狄俄尼索斯,体现在音乐和悲剧艺术中。尼采一直自称为狄俄尼索斯的门徒,他是最高烈度的炸药,是精神的飞行者,是逝去上帝的继承人,在迷醉与狂喜的状态宣告了上帝的死亡,并在雄厚的地基上筑建起了崭新的哲学大厦。1879年,尼采辞去了巴塞尔大学语言学教授之职,开始以一个漫游者的形象行走于欧洲的土地上,尤其是在尼斯、锡尔斯-玛丽亚和都灵三地,他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家园和哲学思想的孵化地。
1888年9月,尼采回到了都灵,这座让他感到年轻、健康、充满活力的城市。1889年1月3日上午,当尼采在大街上看到马夫用皮鞭抽打他的马时,瞬间陷入了失控。他冲上前去,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那匹马,然后瘫倒在地。尼采疯了!他已不再是狄俄尼索斯的门徒,他就是狄俄尼索斯。
天才与疯子,或许中间只隔着一部杰作。写下了多部哲学杰作的尼采,实现了天才与疯子的统一。尼采的疯狂,并非瞬间的崩塌,在《曙光》中他已表达了对疯狂的渴望:“啊,赐予我疯狂吧,来自上苍的力量!只有疯狂才能使我真正相信自己!”这段1880年写下的句子犹如谶语,预示了尼采后来的命运。这捆威力无比的炸药终于爆炸了。而在《我为什么就是命运》中,有句话同样让人动容:“我非常担心有一天人们会称我是‘神圣的’。我不想做圣人,宁愿做傻瓜……也许我就是一个傻瓜。”后来的事情则是:从来没有一个傻瓜被置于如此神圣的地位,除了尼采。
尼采信徒众多,有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里尔克、安德烈·纪德、詹姆斯·乔伊斯等作家和诗人,还有希特勒、墨索里尼这样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尼采的超人哲学被别有用心之徒改造之后,为侵略战争摇旗,为种族清洗张目。在本书中,作者为被污名的尼采进行了有力的辩护,指出了尼采的思想是如何被歪曲和扭解、进而沦为刽子手的道具的。
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迫在眉睫的战争危机助推了尼采哲学的传播与接受,纳粹政权更将之引入己方阵营。在尼采死后,他的胞妹伊丽莎白垄断了尼采作品的著作权和尼采思想的解释权。作为一个反犹主义者,伊丽莎白与纳粹沆瀣一气,任凭他们从尼采的思想库中拣取为强权开路的理论武器,加剧了尼采哲学的污名化。对于这种不堪的局面,作者不无感慨:“成为政治理论的来源,从来就不是尼采的目的。对他的滥用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只对作为个体的人感兴趣,而不是作为一种牧群动物的人——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牧群。”“对尼采而言,可悲的是,战胜自我的需要被公然扭曲为战胜他人的需要,以至掩盖了他以如此辉煌而挑衅的方式提出永恒问题的能力。”
殊不知,在1884年尼采致伊丽莎白的一封信中,他已经预见了可能的结局:“也许有朝一日,会有完全不够格且不合适的人动用我的权威,一念及此,我就深感恐惧。但这是人类每一位伟大导师必经的痛苦:他明白,在一定的条件和时机下,他既可能成为人类的灾难,也可能成为人类的福音。”有此种遭遇的又何止尼采一人?柏拉图、霍布斯、卢梭、康德等思想巨人皆在其列。哲学是一门“危险”的学问,毋宁说,真正危险的是对哲学的断章取义、肆意歪曲。
尼采的一生很难用一部四五百页的传记悉数叙说,但苏·普里多仍用《我是炸药!》证明了这种可能性与必要性。作者精准抓取了尼采生命之河中的清流与湍涛,为尼采描绘了一幅遒劲有力而又生动逼真的画像,其中有他为追寻世界的真理而持续的思索,还有他为获取内心的平静而不懈的行走;有他把上帝拉下神坛的决绝与无畏,还有他将哲学送上云端的笃定与智慧。
作者:付杰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