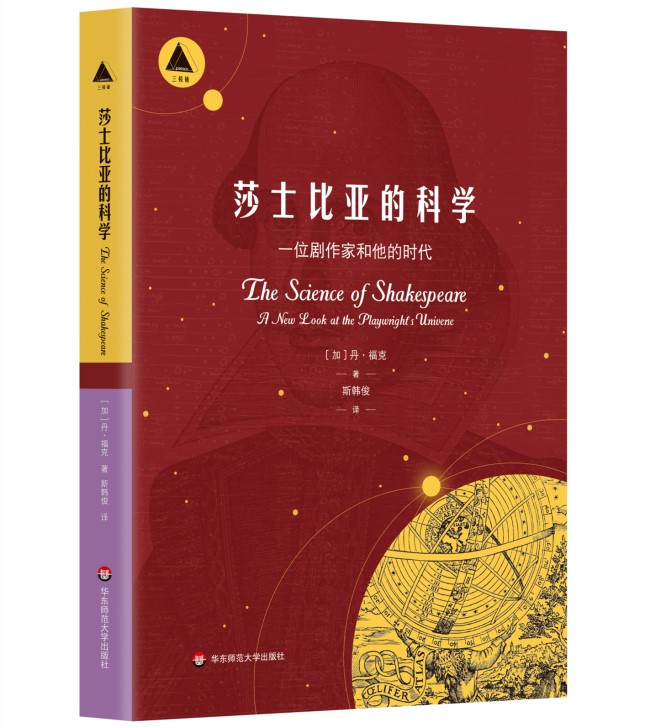
《莎士比亚的科学:一位剧作家和他的时代》
[加] 丹·福克 著 斯韩俊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万物之中皆有科学,莎士比亚的作品亦是如此,他笔下的角色,以一种现代读者似乎很陌生的方式与宇宙联系在一起。莎士比亚生活在一个有关新发现的时代,从天文学、物理学到与生命科学相关的占星术、炼金术、魔法,作者丹·福克化身为一个向导,带领我们重新阅读莎士比亚,观察剧作家对科学发现是否感兴趣,这些知识又如何体现在他的作品中。
>>内文选读:
消逝的众神(节选)
《李尔王》无疑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最荒凉的一部。不仅仅是所有人都死了——《哈姆莱特》中已经出现过这种状况;《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以其血腥程度超越了《李尔王》——而且在《李尔王》中,附带的损害更高得不可估量。似乎正义、道德和意义都与主角们一同消亡了。当李尔带着考狄利娅那无生命气息的尸体出现在舞台上时,观众们肯定认为他们已经跌到了谷底。塞缪尔·约翰逊无法忍受该剧的结局,称它违背了我们“自然的正义理念”。约翰·多佛·威尔逊写道,在《李尔王》中,“恐怖在恐怖的基础上堆积,怜悯在怜悯的基础上堆积”,这使它成为“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人类苦难和绝望的纪念碑”。托马斯·麦克林顿评论说,在整部戏剧中,莎士比亚“一直在思考生活能给人类带来多少痛苦,他们又能忍受多少痛苦。现在他想知道悲剧能走多远以及观众能接受多少”。当其他剧作家停下脚步或折回时,这位《李尔王》的作者继续前进。麦克林顿说莎士比亚“坚决地把我们带到深渊的边缘,甚至更远”。也许剧作家前进得太过了:1681年,纳厄姆·泰特给出了该剧的另一个版本——一种温和的重写,其中考狄利娅得以幸存。在接下来的150年里,这是人们更喜欢的版本,直到19世纪初的几十年,莎士比亚的版本才再次被人们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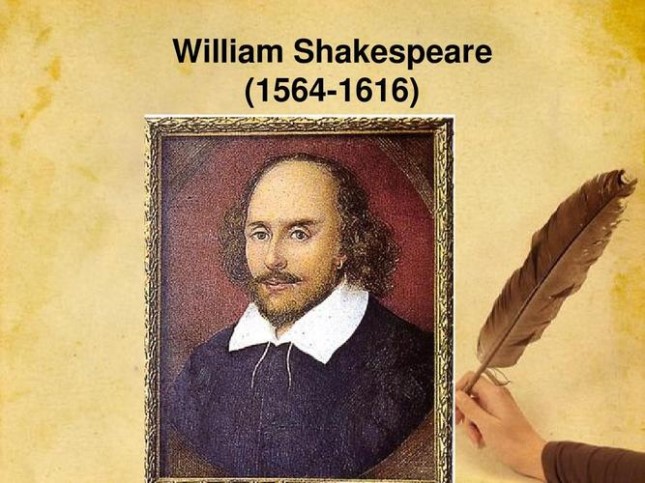
人类需要或渴望少量必需品——空气、食物、水和性。但我们也渴望公正。看到一个被冤枉的人受苦,我们心中充满愤怒;听到有人做了坏事却逍遥法外,我们心中充满了愤慨。司法不公让我们抓狂。实验表明,即使是非常小的孩子也有正义感:当一个行为不端的木偶得到奖励而不是惩罚时,他们会变得暴躁,而如果让孩子负责分发奖励,他会奖励一个“好”木偶而不是“坏”木偶。粗略来说,我们天生希望好的行为得到奖励,做坏事的受到惩罚。当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对公正的渴望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事实上,我们如此渴望公正,以至于它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有时候,即使公正并不存在,我们也能感知到它。我们把它加入到对自然的解读中,想象宇宙本身有某种道德的一面。心理学家认为,在我们的大脑中存在着一种认知过程,它经常让我们想象世界本身就是公正的——人们“得到他们应得的”。我们的语言中充满了这样的日常用语,反映了这种想象“宇宙正义”确实得到了满足的渴望:“他罪有应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甚至“业力”。心理学家给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起了个名字:“公正世界理论”,有时也叫“公正世界信念”。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心理学领域产生了大量关于公正世界信念的文献,最早是由梅尔文·勒纳在20世纪60年代做了开创性工作。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所说,这个理念是“好事往往发生在好人身上,而坏事往往发生在坏人身上,尽管事实显然不是这样”。我们进化出这种思维方式的确切原因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但心理学家怀疑,就像多年来被发现的许多其他“认知偏差”一样,这种思维方式赋予了一种生存优势。我们最好的猜测是它强化了一种观念: 我们控制自己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会产生可预测的后果。正如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所言:“公正世界信念似乎提供了一种心理缓冲,用以应对严酷的现实世界以及个人对自己命运的掌控。”
不幸的是,坏事确实经常发生在好人身上。哈姆莱特王子所说的“命运之箭和凶险之箭”在选择目标时很少有区别。勒纳告诫说公正世界信念是一个“发明”;他关于这一问题的著作名为《公正世界信念:一种根本的错觉》。但它的影响非常真实,而且常常相当令人反感,包括倾向于将人们遭受的苦难或伤害归咎于他们的命运。因此,一些人会不遗余力地寻找一个理由,任何理由都行,来解释为什么受害者的不幸命运是他们应得的——为什么那些成功的人配得上他们的好运。公正世界信念还有另一个负面影响: 让我们怀疑科学证据。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面对大量的和越来越多的证据,一些人还是抵制气候变化是人为的这一观点,因为这与他们所认为的公正世界相冲突。正如马修·范伯格和罗伯·威勒所言,承认全球变暖“威胁到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信念,即世界是公正、有序和稳定的”。莎士比亚从未在伯克利教过心理学——但他似乎在四个世纪前就有了这些想法。至少,他认识到存在一个天生的公正世界的想法难以置信。他要么知道、要么怀疑宇宙没有道德的一面;事情就只是发生。有些时候,目睹这一切令人不安,好事发生在坏人身上,还有更糟糕的是,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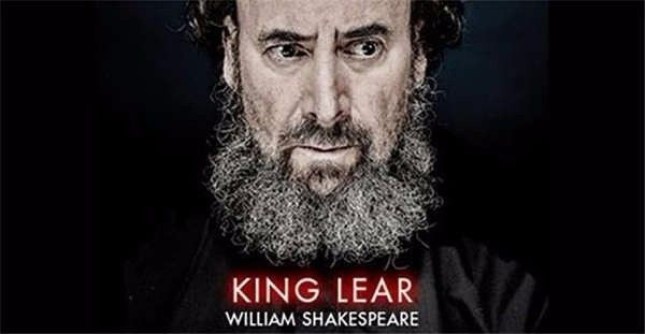
没有哪里比《李尔王》更深入地探讨了宇宙正义的概念。“自然”这个词在《李尔王》中的使用频率比其他任何一部戏剧都要高,正如大卫·贝文顿所断言的,这部戏剧本身就可以看作是“对立的自然概念争斗的战场”。正如托马斯·麦克林顿所说,这部剧是对“自然本质”的调查。它问的是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宇宙中。一个是“在本质上道德的,规定利他主义,社区式,有限制和理性”的宇宙,而另一个更新的观点认为“自然是一个非道德的系统,鼓励利己主义和肆无忌惮地使用武力及狡诈来实现自己的欲望”,人们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答案并不令人欣慰。塞缪尔·约翰逊曾问《李尔王》是不是“一部恶人横行的戏剧”,看起来的确是那样。恶人常逍遥法外,好人则无利可图。看过这部剧的人都不会忘记葛罗斯特的失明,这肯定是文艺复兴戏剧中最残忍(甚至令人作呕)的场景之一。但是,请注意其中一个仆人在目睹了康华尔对其受害者造成的恐怖之后所说的话:“要是这家伙有好收场,我什么坏事都可以去做了。”正如贝文顿所指出的,仆人们“提出了令人不安的问题,也就是如果犯罪不受上帝惩罚,必然会导致普遍的混乱”。同样,在《奥瑟罗》中,众神也没有惩罚伊阿古,所以威尼斯当局必须弥补宇宙正义的缺失:“我们将要用一切巧妙的酷刑加在他的身上,使他遍受种种的痛苦,而不至于立刻死去。”这听起来更像是复仇,而不是正义,但它确实如格林布拉特所写的是“一种修复受损道德秩序的姿态,尽管并不充分”。诸神似乎也同样对《麦克白》中的主人公不感兴趣,但至少在剧中标题主人公遇到了对手,而看到麦克德夫扛着麦克白被斩下的头颅走上舞台,我们感到很满足。但在《李尔王》中,众神,如果他们真实存在的话,似乎是在朝另一个方向看。在莎士比亚时代,教会经常谴责戏剧不道德,但是《李尔王》展示了比不道德更糟糕的东西。它暗示着一个既不公正也不是不公正的宇宙,在这个宇宙中,除非我们自己采取措施来建立公正,否则它就完全不存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可怕的无道德的宇宙。
爱德蒙——葛罗斯特伯爵的私生子,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大反派之一。关于这个《李尔王》中的角色令人惊恐的地方,是他成功了:他坚决地作恶——他极其乐意伤害别人来实现自己的自私目标——而且他侥幸逃脱了惩罚。贝文顿写道:
《李尔王》真正让人感到恐惧的是,围绕“自然”展开的争斗似乎对爱德蒙有利,其程度如此之深、持续时间如此之久。正如他所理解的,他自力更生的信条使他比那些轻信于社会秩序中道德约束的人具有战术上的优势。他认为道德规范只是神话的一部分,权力结构通过它来控制社会,所以他觉得没有理由不去撒谎、欺骗或以其他方式压倒那些阻碍他实现无限抱负的人。确信没有神来奖赏和惩罚,也没有来世来承受永恒的痛苦,爱德蒙以不懈的精力和高超的战术不断前进。
正如乔纳森·贝特所言,爱德蒙与艾伦、伊阿古和理查德三世一起,是一组莎士比亚提供的“华丽舞台上毫无歉意的反派”人物。但爱德蒙不仅仅是一个聪明、精于算计、控制欲强的反派,也是一个怀疑论者。我们已经看到(在第十章)他拒绝相信占星术,拒绝接受他父亲信奉的迷信,但他也——正如贝文顿在上面段落中暗示的那样——完全愿意拒绝死后生命的观念,甚至拒绝神本身。
作者: 丹·福克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