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事、某人或某种未来怀有渴望和依恋,便意味对其保有一种乐观的情感。它意味着你相信,或愿意相信,这些事物和人能让你接近某种美好,能赋予你意义。
但有些乐观却是残酷的。
你追求着那些磁石般吸引着你,承诺让你的世界变得美好而有意义的东西,你渴望一种“美好生活”。但你不断向其靠近的过程,却在事实上损耗你、折磨你、摧毁你,让你恰恰走向了你所渴望的“美好生活”的反面。这时,乐观主义是残酷的。它让你永远渴望,永远失望,永远在无望中保持希望。
“残酷的乐观主义”,贝兰特这个概念深刻的悖论性首先是一种情感的肉身体验。也许难以言说也难于书写,但这种矛盾的、默默期待又咬牙忍耐的身体感受似乎是今天人们共通的情感。就像她所说,这些残酷的乐观主义造就的场景,“一方面意味着深刻的威胁,另一方面又是深刻的确认”。
这是一种有毒的关系。残酷的乐观主义的残酷之处,不仅在于它其实永远无法满足你的渴望,更在于,它如此深刻地与你整个意义世界和本体性安全相连,以至于你根本无法承受失去这种乐观本身。它为你的生活提供了“延续性”和根本的支撑。但当你被这种乐观激发着朝前迈进,等待着你的却是无尽的自我消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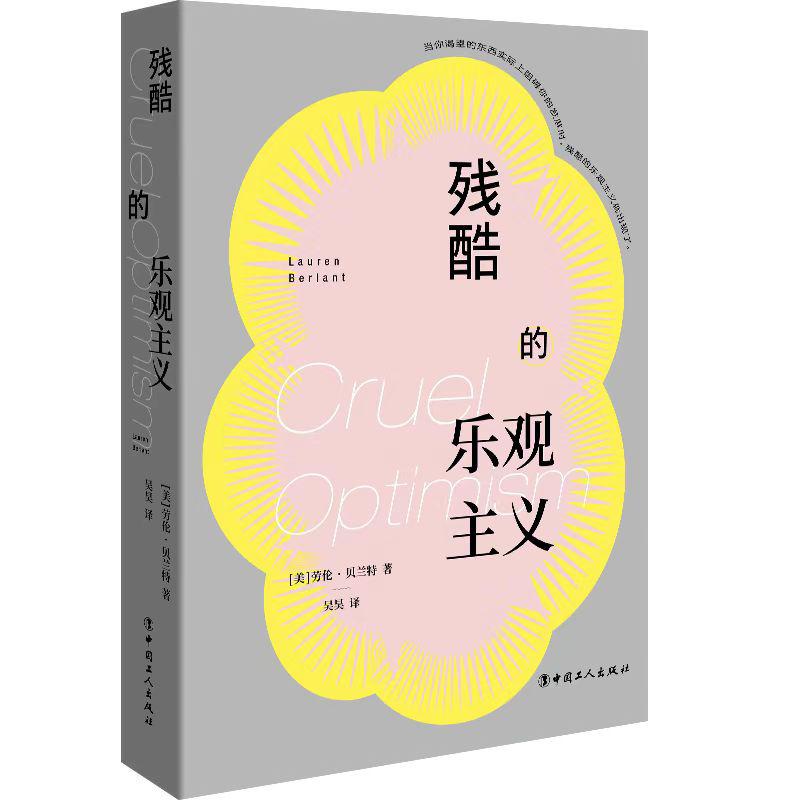
《残酷的乐观主义》
[美] 劳伦·贝兰特 著
吴昊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
贝兰特想要借这个概念和这本书回答的问题便是:“当越来越多的证据都昭示某种熟悉的美好生活的幻想已经如此不稳定、脆弱和代价高昂, 为什么人们仍然对诸如与爱人、家人、政治制度、机构、市场和工作之间持久的依存关系如此眷恋?”
为什么我们会维系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
当我们维系的是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历史性当下
回到本书坐落和回应的历史性时刻是重要的。《残酷的乐观主义》原版于2011年。它所聚焦的是“二战”后美国和其他地方社会民主主义萎缩和新自由主义滋长的历史时刻。它以1990年以来的大众传媒、文学、电影和先锋艺术为“案例”,追溯剖析了这一历史性当下的“情感结构”。
“历史性当下”这个概念导向的问题,是“此刻”如何被生产出来,以及何以具有深刻的政治性。通过本书,她希望建构的是一种分析历史性当下模式,可以超越结构与能动的二元性。她将“情感”当作理解历史性当下的关键。而残酷的乐观主义,正是我们所在的历史性当下的情感性“政治主体性”。
贝兰特看到,在这样的历史性当下,“暴虐无常的超剥削企业原子主义”开始渗透经济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与此同时,公共领域和团结感在权力的重压下分崩离析。边缘和底层要么面对无休无止的暴力,要么被迫在匿名的阴影里苟且求生,没有声音,没有也存在的痕迹。贝兰特所描述的残酷的乐观主义肆虐的历史性时刻,社会的裂痕沿着经济和政治分化的界限剧烈扩大,而政治和正义成为一种表演,一场闹剧,一种新的残酷体裁。
20世纪下半叶开始,那些自由资本主义承诺的东西,包括阶层流动、就业保障、机会均等、贤能体制、公民身份、政治和社会平等,以及生机勃勃、滋养耐久的亲密关系,作为支撑性的幻想都在结构性地失去其牵引力。随着冷战结束,所有最理想的乌托邦幻想被另一些看起来似乎更“合理”、“方便”、“可得”的幻想取而代之。但这些幻想旋即变作更加梦幻的海市蜃楼。这些幻想承诺的习惯、规范和制度,曾短暂地滋养了依恋感、信赖感、归属感以及乐观的期盼,却很快像已被蛀蚀的房屋一般,威胁着将生活在其中的人全部掩埋。

由达内兄弟导演的现实主义影片《罗塞塔》展现了一个女孩在生活重压下做出的反抗与救赎
比如,第五章中,贝兰特讨论了比利时导演达内兄弟的电影《罗塞塔》。罗塞塔是一个被高度全球化和自由化的经济抛出的年轻人。对她来说,“世界上所有可能的欲望被压缩为一个朋友和一份工作, 一种获得最低限度的社会承认的状态”。
贝兰特描述到,罗塞塔在得到工作后片刻的安全感中,她对自己成为一个“好工人”的前景感到乐观。觉得自己也许终于可以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过一种“正常”的生活。这种对“正常”的依恋,成为罗塞塔的“残酷的乐观主义”。贝兰特尖锐的指出,这种幻想中的美好生活,只是感觉起来是可能的,是美好的——“持续的低工资生活前景和无聊的劳动, 对罗塞塔而言近乎一种乌托邦”。
在社会福利极度萎缩,正规和非正规的经济进一步私有化和零工化的结构下,底层对“正常”的依恋正残酷摧毁着她们的精神和肉体。这种“正常感”,作为一种规范性的、让人安心的承诺,是如此重要——我们看到罗塞塔为了保住华夫饼店那份根本没有任何保障,工资极低且不稳定的工作,背弃了她唯一的朋友。但追求“正常”导致的对互惠关系的伤害,仿佛又让“正常”失去了它最初承诺会带来的感受。
贝兰特看到,“依恋与经济系统同样脆弱, 都对工人后备军呼之即来, 挥之即去”。正是在此种历史性当下产生了这样的情感性主体——她们被“美好生活”托起,却又遭其背叛。
最后,崩溃茫然的罗塞塔辞去了工作,回到那辆租来的破旧拖车——那个她与以酒精自我麻痹的母亲相依为命的家。
危机的日常性
理论和经验的层面上,贝兰特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超越以往讨论历史性当下的“创伤”体裁。创伤理论关注创伤性的“例外”事件对主体性的塑造。于此相对,她提出“危机的日常性”,认为当下的危机并不具有“例外”的性质,而是以一种让人并不舒适,也难以言明的方式被编织进日常生活本身的纹理之中。
她认为:“日常生活是多重历史的交汇点, 人们在这里处理在其想象的美好生活面临威胁时所产生的困惑和断裂性。灾难性的力量也在这里形成, 并在人们生活的历史中成为事件。”
危机的日常性是一种“慢性死亡”,而“创伤”修辞遮蔽的正是慢性死亡的状态。是一种“结构层面引发的个体的耗损——既不是一种例外状态, 也不是例外的反面。而是令人不安的生活场景与日常生活相互交织的状态。就像发现蚂蚁在一块不经意抬起的岩石下慌张逃窜。”。
本书中到处都是这样的例子。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贝兰特对丽莎·约翰逊的短片《10号公路以南》的讨论。她谈到,影片用缄默主义的镜头,无声地记录下灾难性的卡特里娜飓风过后,被国家和新闻的煽情凝视遗忘的密西西比州沿岸人们的生活——这里长期被肮脏的阶级和种族历史蹂躏。我们看到,人们在飓风席卷后的时间发呆、劳动、休息、捡起被灾难摧毁的物品,清洗、修补,努力让其恢复功用,或成为什么别的。

卡特里娜飓风灾损
贝兰特指出这个时代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危机就是生活本身,它“并不是呼啸而过的,而是绵延漫长的”。贝兰特提醒我们,必须反思“苦难的日常性”“常态的暴虐性”和所谓“忍耐的技术”,提出“对此刻的残酷性”的尖锐质问,“去看看在远离一个日渐衰微的美好生活的幻想的过程中, 那些踌躇停顿、期期艾艾且隐隐作痛的东西是什么”。
残酷的“僵局”
贯穿本书,贝兰特向我们证明,残酷的乐观主义之下,人们面对的,是幸福的无限“推迟”和生活本身的“暂停”,是一个没有出口,没有未来的“僵局”。
就像第一章讨论的黑人兄弟库特和洛夫提斯的故事。当贫穷的兄弟“清理”了另一个赤贫却意外得财的邻居,贝莉小姐,他们被获得巨量财富抛入了一个“僵局”。他们痛苦地意识到,这些财富并不能让他们免受贝莉小姐的命运,即“忍受黑人特有的失去生活中仅有的那一点点东西的恐惧”。他们僵住了,生活并没有因此开启,因为“每一次购买,都会是一次不值得的交易,都是对生活本身的消耗”。在异化的消费主义体制之下,对象带来的愉悦本身已经被占有的感觉吞噬,人们拥有的只是取之不竭的“非关系”。
在贝兰特的书中,这些残酷的僵局无处不在。无论是《一诺千金》中无言同行的雇主儿子伊戈尔与移工妻子阿西塔,《暂停》中若无其事家人朋友隐瞒自己失业的文森特,《两个女孩,一胖一瘦》中用食物、思考和逃离绝望的桃乐茜和贾斯廷,还是《人力资源》中在管理阶层“未来”和工人阶级家庭“历史”中撕裂的弗兰克,都昭示“僵局”已然成为历史性当下的主要体裁。
正如贝兰特残酷地指出:“在危机日常性的体制之下, 生活好像被删节了, 更像是绝望地狗刨, 而不是壮丽地游向地平线……生命献给了对美好生活的规范性/乌托邦所在的追求, 但却实际上陷入了我们可能称为求生的时刻、挣扎的时刻、溺水的时刻、紧紧抓住边缘的时刻、扑腾踩水的时刻——那无法停下的时刻。”
贝兰特的《残酷的乐观主义》一书,是忧虑的、悲观的、残忍的,但也许也是乐观的。而这种乐观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拆解世界,并同时保持对创造世界的持续承诺……直面与世界的锚定脱钩的血肉模糊的过程”。
虽然此刻已是残酷的僵局,团结和改变意味着卓绝的斗争,但也许,人性仍然为我们提供了想象不残酷的乐观的可能性。正如贝兰特所说,“生活真正发生的地方是当我们拥有一个朋友、一个伴侣, 或当我们满怀热切地注视着的人, 最终对我们的挣扎苦难报以温柔同情的时刻。”
为了真正的美好生活。
作者:吴昊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朱自奋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