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多数人都无暇阅读卷帙浩繁的史书,但人们依然需要了解一些历史知识。在这个时间急促而破碎的时代,读者们依然需要文字轻松又不失知识逻辑的著作。《中华帝国的轮廓:从秦汉时期到戊戌维新》就是一本视角独到、注释详尽、观点新颖的简明中华史读本。
![[立体封]中华帝国的轮廓.png](http://wenhui.whb.cn/u/cms/www/202208/151334526k79.png)
《中华帝国的轮廓:从秦汉时期到戊戌维新》
吕 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总之,亲近自然,保持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一直是中国人普遍的认识和心性,他们对自然之事保持极大的尊重和依恋,可以在经典的中国传统艺术山水画中获得深深的理解:人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以至人物在自然中所处的位置是微不足道的,几乎像一棵树或一个石子那样平凡并与自然保持和谐。正如《庄子·秋水》中的文字:“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所以,中国山水画的产生和内涵与它的作者阅历、知识背景以及世界观有关。公元353年,中国的诗人们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举行了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聚会。聚会的基本理由来自习惯,即遵循每年春秋二季在自然水边举行祭祀以消除“妖邪”的惯例。这本来不属于一种轻松的心境活动,但是,自汉代之后,在大自然里的祭祀已经演变为游玩,祭祀祛除妖邪的理由仅仅是文人们季节性的遨游的托词,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喝酒吟诗,领略自然的景色,并且体验自然的清新。诗人们告诉我们:
今我斯游,神怡心静。
……
嘉会欣时游,豁尔畅心神。(王肃之:《兰亭诗》)
散怀山水,萧然忘羁。(王徽之:《兰亭诗》)
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
这样的心境与任何时代的人渴望到自然环境中去游玩的内心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西晋末年,老庄玄学的肆意蔓延衍生出了玄言诗的泛滥,求仙与悟道成为人们进入自然的重要理由,以至对自然的赞美具有冥想或思想远游的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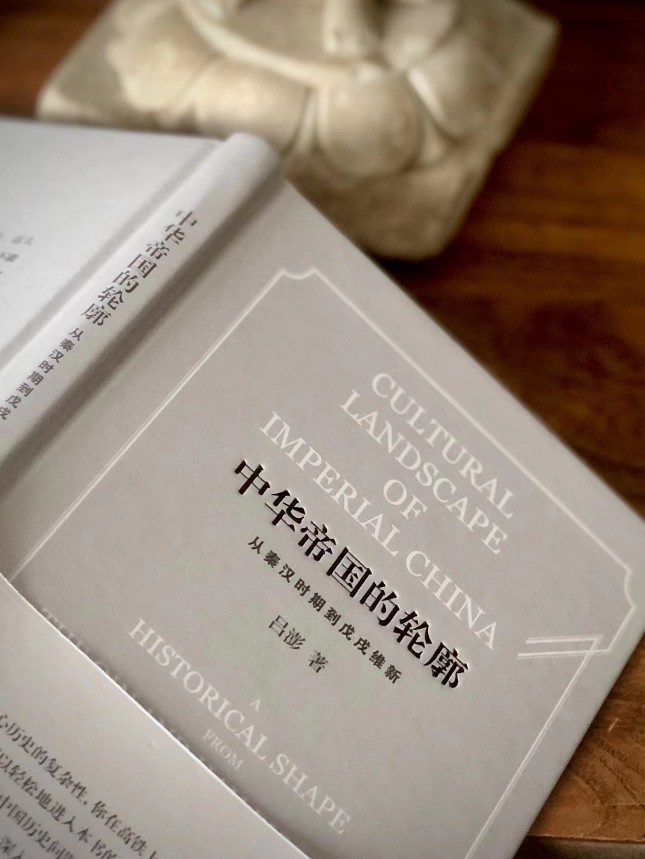
直至今天,我们几乎没有得到多少关于唐代(618—907)山水画真迹的证据,尽管诗人王维(701—761)的《辋川图》和《江干雪霁图卷》经常被提及(尽管通过郭忠恕[?—977]或者燕文贵[967—1044]的临品对王维的山水画的研究可能是不可靠的)。最有可能将唐代的山水观念中的绘画因素提取出来研究的是相对宁静岁月的田园诗,而这正是王维的重要性。这位诗人在26岁就生发出了归隐田园的动机看来不是因为不得志,而是一种传统的感染。事实上,王维27岁在淇上任官,次年就弃官隐居淇上,29岁闲居长安,34岁隐居嵩山,41岁又弃官隐居终南山,天宝元年至天宝十五载(742—756)在做官的同时经营辋川别业,属于半隐生活。安史之乱后勉强为官,但居山水田园之间。他的诗也显出了面对自然的平和,例如: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山居秋暝》)
所以,那些《辋川图》的临品所反映的农村生活可以想象是让人感到平静的风景。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对王维的画进行评价时使用了“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这样的语句。这种接近文学描述性的评论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如何对应让人困惑,以后荆浩的评价是“笔墨宛丽,气韵高清”,这里我们看到了文人画的早期内在因素。由于苏轼(1037—1101)的原因,王维的绘画被认为明显地提示出诗画同一的概念,“画中有诗”与“诗中有画”成为画论的习惯性用语,以至遮蔽了图像与文字在人的内心里产生作用的心理差异。

当然,画家一开始尊崇眼睛所看到的对象,这是绘事的一般经验。例如作为一位嗜酒好道的“隐士”,范宽 ( 生卒年不详 ) 被描述为“卜居于终南太华岩隈林麓之间,而览其云烟惨淡,风月阴霁,难状之景,默与神遇,一寄于笔端之间,则千岩万壑,恍然如行山阴道中,虽盛暑中,凛凛然使人急欲挟纩也”(《宣和画谱》卷一)。《宣和画谱》的作者是如何知道范宽“览其云烟惨淡,风月阴霁,难状之景”的心情以至肯定他“默与神遇”的?在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完全成型之前,范宽的作品表现出五代宋初时期画家对自然的绝对真实的无与伦比的关注。就像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在他的书《山川悠远》中所说的那样:“范宽的意图很清楚,他要让观者感到自己不是在看画,而是真实地站在峭壁之下凝神注视着大自然,直到尘世的喧闹在身边消逝,耳旁响起林间的风声,落瀑的轰鸣和山径上嗒嗒而来的驴蹄声为止。”不过,苏东坡说:“近岁惟范宽稍存古法,然微有俗气。”(《东坡题跋》)这个关于“俗气”的评语其实是对经验与事实的反感所致。
的确,五代至北宋初南北画家在皴法上的差异很大。南方自巨然后很长时间极少有知名画家,北方皴法因其皇室上下追求雄奇的风尚,在经济与权力的支持下占据主导地位,但画家因其方法的局限也在皴法上利用披麻皴表现山水。南宋时期,南北画家经历了皴法上的交融,例如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四人的画作中披麻、斧劈、卷云三大皴法已交互用,直至最后南北派别的差异事实上已为院体趣味所导致的方法替代。笔墨之间的分别在不同时代的画家和批评家那里被过分抽象地表述,可是一旦面对画面,我们就能在画家运用自如的皴染中感受到笔墨的微妙趣味与效果。

思想总是通过文字呈现,而被称为“文人画”的画家一开始就与精英士大夫阶层有关,人们很容易想到苏轼这类事实上是朝廷命官的人物。在两宋时期,那些流落在民间的画家从来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力,看上去与院体风格相去甚远的文人画的合法性与持久的影响力同样也来自合法的儒家意识形态和道家人生态度的支持。文人画的最初倡导者苏轼的政治观点是,既然士大夫阶层是国家力量的主要部分,为什么不可以通过严格的儒家精神和高级的文化来提升他们的素质进而使整个政府机构的水平更加提高呢?然而,以若干经典为象征的儒家思想因知识背景和教养、政治地位与目的、集团利益与权力者目标的不同而可以有多种解释,这样,对道德品质的解释也就出现了显而易见的差异。
关于“士”“大夫”“文人”以及“知识分子”这些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真正含义同样也是具有重要性的,不过,文献给我们留下的记载表明,只要我们知道在两宋时期的那些主张不同于院体风格的绘画思想和笔墨方法的人物事实上是那个时代富于责任感的儒家知识分子,知道他们总是在个人命运的不同阶段保持着圣人孔子的经典教导“士志于道……”(论语·里仁)的立场,就清楚这些文人画的主张者的基本知识与教养背景。儒家经典《大学》说:如要治国就先齐家,欲先齐家就应该“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正心”“诚意”“致知”都是先圣去世后数百上千年讨论理解的课题,直至朱熹的诠释被合法化与正统化。宋代理学家对技术的反感所到的程度在程颐的表述中达到极致。

作为文学家,“文人画”的倡导者苏轼因为自己的天才在文学诗词书法方面都有卓越的名声。人们知道苏轼在散文领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方面与黄庭坚(1045—1105)并称“苏黄”;而论词,他又与辛弃疾(1140—1207)并称“苏辛”;在与绘画有直接不可分割的书法领域,苏轼同黄庭坚、米芾(1051—1107)、蔡襄合称“宋四家”。这正好表明了“文人画”的一个显著特征——“文”的重要性。
苏轼为人们广泛引述的《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诗中的文字让太多的文人和研究者困惑: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东坡诗集注》卷二十七)
表达“诗意”事实上是儒家教育的传统,“诗画本一律”的含义成为我们理解苏东坡观点的重点。究竟是什么让苏轼非常自信地认为诗画“一律”?苏轼在《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诗中说:“神机巧思无所发,化为烟霏沦石中。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东坡诗集注》卷三十)显然,诗歌中“比兴”的方法在苏轼的语词引导下进入绘画领域。

唐宋时期的诗词和绘画,在任何时代的中国人看来都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成果,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运动最为激烈的时期,也没有一个先锋艺术家对此加以否认,这的确类似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成为后世文学艺术没有穷尽的资源:多姿多彩,卓越非凡,精妙绝伦,通常来说,任何赞美之词都不为过。在那些不同程度呈现思想态度的作品中,我们总是能够找到儒家思想和道家的精神背景,不过,尽管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是那些由隐而仕或由仕而隐的文人创作的经典文学范例,但一切取决于文学艺术家在创作作品时所处的语境以及相应的思想状况,人们更多地认为,那些呈现了人的内心深处和普遍性心理的诗词——
像南唐的李煜(937—978)的词,总是对人生的转折和生命的内在特征最深邃隽永的绝唱: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
这类调性与气质,自始至终都贯穿在华夏精神文明的演变过程中——儒家的人生之道与道家的自然之道融为一体,维系至今。
作者:吕 澎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