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它在心头划出鲜血,却可以疗愈人心——《以鹰之名》揭示我们与野生世界的亲密关系
《以鹰之名》是非虚构知名奖项塞缪尔·约翰逊奖获奖作品,科斯塔文学奖年度作品。
2007年,父亲骤然离世的那段日子,海伦·麦克唐纳回忆:“当时我再也不想当人,选择走入小时候本能迷上的苍鹰世界,因为做一个人,我就会感受心里深处那不见底的悲伤和情绪。我想停止那一切,飞离那一切,我想变成其他生物。”
她开始训练世上最难驯服的禽鸟:苍鹰,自由野性的象征。日日活在鹰的世界,离开人群投入荒野天际。在这个过程中,她与儿时熟读的作品《苍鹰》的作者T.H.怀特重逢,追寻了与自己相同的怀特离群索居、训练苍鹰的过程。
一个骤失父亲的女儿,一位写出传世亚瑟王传奇的潦倒作家, 以鹰的名义,他们相隔百年却遥相呼应——有些伤口,永远不会愈合;以驯鹰的名义,他们放飞手中的鹰,期望那条象征习惯、饥饿、伙伴,被驯鹰人称为“爱”的线,永不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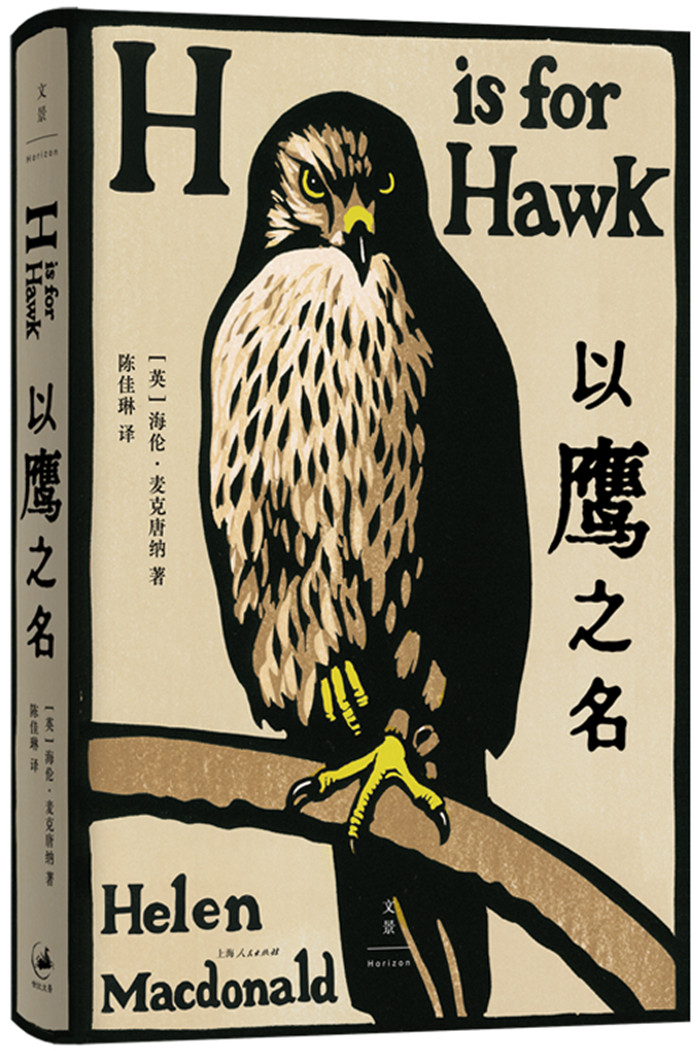
《以鹰之名》
[英]海伦·麦克唐纳 著
陈佳琳 译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版
>>内文选读:
第一章 耐心
从剑桥往东北方开车大约四十五分钟,有一处我最近特别喜欢的秘境。干涸砂砾地取代了原本的潮湿沼泽,一眼望去全是扭曲的松木、烧得只剩钢板骨架的破车、弹痕累累的路标,还有一座美国空军基地。编了号码的松树林地还留着几间破败小屋,散发着幽灵出没的气息。杂草蔓生的土冢曾经存放携带式核弹头,由十二英尺高的围墙层层防护。那一带还有几间刺青工坊,美国空军的专属高尔夫球场。春天时充斥各式杂音:来来往往的运输机、豌豆田回荡着的枪响、林百灵的啼叫与喷气发动机的噪声。那里是布雷克兰区,我看叫“破烂区”还差不多。七年前某个初春清晨,我一时兴起去到那里。当日早上约莫五点时,我还躺在床上,瞪着路灯投于天花板上的方形黑影,听着屋外人行道上人们热烈的聊天,他们的派对刚散场。我浑身不对劲:又累又烦,脑子完全被抽空,取而代之的是微波得焦黑、失去光泽的皱铝箔团。不行,我一定要出门,我心想,一面甩开棉被,出门去!我套上牛仔裤、长靴与毛衣,用煮过头的咖啡漱口。我开着那辆冻僵的老大众上了十四号公路,到了半路才回神要去哪里,目的是什么:是那片森林,雾蒙蒙的挡风玻璃前看去的地平线,就是那片荒废的林子,我正朝着那里前进。我要去看苍鹰。
我本来就知道很难,能看到苍鹰就不简单。你在花园看到过鹰抓过小鸟吗?我没亲眼见过,但我知道它们来过。我目睹过证据,有时候会在门廊石阶上发现细微线索:细致如小虫的鸣禽的脚爪,紧紧蜷曲;更骇人的还有掉落的鸟喙——也许是家麻雀的上喙或下喙,半透明锥状铜色物体,隐隐的上喙羽甚至还没掉落。我想你可能见过:某次不经意看向窗外,竟有一只嗜血大鹰在草地上谋杀鸽子,或乌鸫,或喜鹊,但那可能是你毕生见过最壮观的野性场面了,仿佛有人将一头雪豹放进你家厨房,结果你看到它正大口吃着你的猫。在超市或图书馆,曾有人冲向我,说:今天早上我家后院有只老鹰在抓鸟!我还来不及回应,喔,那是雀鹰!对方继续说,“我翻了图鉴,那是苍鹰。”不可能,这些图鉴根本没用。后院草坪上老鹰与鸽子打斗的场面过于惊人,鸟类图鉴的插画也很难与记忆相符。图鉴里的雀鹰是这样的:体色深灰,胸腹黑白条纹相间,黄色双眼,尾翼细长。一旁画着苍鹰,同样是深灰色,胸腹黑白条纹相间,黄色双眼,尾翼细长。你心想,原来如此,然后继续读着描述。雀鹰体长十二到十六英寸;苍鹰则有十九到二十四英寸……没错,刚才看到的那只大很多,就是苍鹰了。它们看起来很像,但苍鹰体型比较大,那就是了!
如果这么想就错了。真实世界里,苍鹰之于雀鹰,犹如花豹之于家猫:体型的确略胜一筹,但更强壮残暴、致命吓人,行踪飘忽不定,比雀鹰难发现太多太多了。它待在僻静深林,而不是邻家花园。它们正是观鸟人寻寻觅觅的黑暗圣杯。你可能在苍鹰栖息的森林待了一整个星期,却始终连个鸟影也没瞥见,顶多有它们存在的蛛丝马迹罢了:先是一阵静默,之后传来林鸟的恐慌哀鸣,接着你感觉到若有似无的晃动黑影。也许你会看见被吃掉一半的鸽子尸体,其凌乱白羽瘫在林地上。如果你幸运一点:在黎明晨雾间漫步时,一个转身能瞥见鸟影迅速飞掠,巨大的鹰爪微弯,眼神专注在远方的猎物。这浮光掠影会深深镌刻在你脑海,让你更加渴望与它邂逅。寻找苍鹰犹如追寻恩典:它会出现,但并不寻常,你也说不准时间地点。不过,初春沉静晴朗的早晨,的确有机会看见它,因为苍鹰会在这时候离开树林栖地,翱翔天际热烈求偶。我最想看见的莫过于这一幕。
我甩上生锈车门,拿着望远镜踏过一片银白如锡的霜降林地。这里与我上次来时已不复相同。我找到一片只剩光秃树根与干燥松针的沙地。空地,这是我最需要的。我几个月没运作的脑子开始恢复起来。我待在图书馆、研究室太久,总是对着电脑屏幕皱眉深思,要不就是批改论文,忙着搜寻参考书目。如今我在这里展开不同的追寻。在这里,我是不一样的生物。你见过鹿从隐蔽处现身吗?它们拾步而行,接着驻足不动,鼻头朝上闻着空气,四处张望,再次嗅闻。或许一阵紧张悸动窜流身侧,它们再次确保一切安全无虞后,会继续踱步前行,最后走出树丛,低头吃草。那天早上,我就像头鹿。当然我没有嗅闻空气,或是感到恐惧—但我跟鹿一样,不得不以紧张而缓慢的方式走过这片荒野,不由自主地观察周遭环境。我完全没有思考,体内就有个声音指挥我迈开脚步,如何、向何处前进。或许是百万年的演化造就,或许是本能作祟,总之寻觅苍鹰的我一旦身处灿烂阳光下,就紧绷不安,我发现自己不自觉地沿着光线边缘走,或闪进松林间的狭小荫凉处。听见鸟雀或乌鸦愤怒啼叫时,我甚至退缩了。它们肯定在说,小心啊!人类来了!要不就是小心啊!苍鹰来了!那天早上,我试着隐藏人类的气息以找到苍鹰。几千年来,连接灵魂与肉体、鬼魅般的古老敏锐直觉接管全场,让我在明亮的阳光下感受惶恐。结果我误闯了一处小山丘,最后不得不绕路而行,柳暗花明之后的另一头原来是个池塘:苍头燕雀、燕雀、一群北长尾山雀全都在池边柳林间活泼跳动,远看真像是一团团有生命的棉花花蕾。
这个池塘前身是炸弹坑。“二战”时德军轰炸机在附近的莱肯希思投下了一串炸弹,形成这样独特的水乡景观:小池塘离大海有段距离却有沙丘包围着,沙生薹草丛错落四周。我摇摇头,太诡异了。但这里的景观本来就奇特,走在森林间,你会有五花八门的奇遇。例如大范围的整片石蕊,星状与花朵般的古老植物群生长在贫瘠大地。可以想象夏天将它们踩在脚下时,还会发出清脆窸窣声,简直就是从极地误闯入温暖世界的生物。另外,骨头碎片、燧石碎片也俯拾皆是。露重霜浓的清晨,你甚至可以捡到新石器时代工匠遗留下来的燧石渣,闪亮的小石头在冰冷的浅水洼对你眨眼。这一区曾是新石器时代的燧石重镇。后来,它成了著名的养兔场,兔肉与兔毛都是重要的经济产物。黄沙漫漫的大地曾被大型栅栏围成一区区的养兔场,因而留下了与当年产业相关的地名,如旺福德栅、莱肯希思栅等。可没想到最后兔子带来灾难,它们与绵羊争食牧草,沙地草原只剩下短浅草根。草况持续恶化,成堆黄沙被风吹来,蔓延至整个地区。1688年,强劲西南风卷起这片黄沙恶地,沙尘暴犹如昏黄巨云铺天盖地,伸手不见五指,遮蔽了阳光。成吨黄沙因大自然的力量而被举起、移动、掉落,将布兰登团团覆盖;桑顿道纳姆被全数吞噬,河流就此干涸。暴风稍歇后,沙丘从布兰登镇绵延数英里至巴顿米尔斯,一望无际。这一带后来有了对旅人不友善的恶名:举步维艰的松软沙丘,令人燠热难耐的夏日,入夜后更有沿路打劫的恶徒……这就是我们的阿拉伯荒漠。约翰·伊夫林说这些“流动不定的飞沙……破坏了乡间美景,令人看不清楚城市每个角落,宛若利比亚大漠的黄沙滚滚,几乎毁掉了士绅们的宅邸庭园。”
我现在就站在伊夫林描述的“流动不定的飞沙”中,大部分的沙丘隐身于松林后方。这些松林是20世纪20年代政府所植,以让我们在未来战事时有木材可用。强掳凶狠的不法之徒早已不见身影,但此地仍隐然危机四伏,甚至有种破败的不祥气息。我喜欢这里,因为我一直认为它是全英格兰最蛮荒的地点,但不像高山峰顶的原始风貌,而是人类与土地合力造就的偏僻荒野,这令它独一无二。这里曾有活跃的人文活动,不只是那些占地辽阔的宏伟宅邸所编织而成的庄园大梦,更有工业、林业、商业的丰富历史情怀。这里是遇上苍鹰的绝佳地点,它们与布雷克兰区特殊奇异的地貌相映成趣,因为它们也曾有着像人类般的一段过去。

这是一段美妙动人的故事。苍鹰曾是遍布不列颠群岛上的物种。“苍鹰的种类与体型多元得让人眼花,”理查德·布洛梅在1618年写道,“脾气、力量与韧性也多所不同,端赖它们成长的区域,但唯有来自俄国、挪威与爱尔兰北方蒂龙郡的苍鹰最优异。”然而,圈地运动使平民百姓再也无法放飞苍鹰,有狩猎本领与天性的苍鹰逐渐为人类淡忘;枪支管制的放宽更使得射击打猎蔚为风尚,鹰猎相形式微。苍鹰反倒成了人们眼中的害鸟,而非狩猎伙伴,这让原本栖地就已流失的苍鹰数量愈益下降。19世纪末期,英国苍鹰已经绝种。我手上有一张英国最后一只苍鹰的标本照片。这张黑白照片来自苏格兰的庄园,落寞的标本还睁着一双玻璃眼珠。它们就这么消失了。
然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驯鹰人开始在私底下复育英国苍鹰。英国驯鹰人俱乐部计算出,养大、训练一只从欧陆进口的苍鹰的成本,其实可以与再运入第二只苍鹰带回英国,并将其野放的费用相差无几。买一“送”一最划算。野放送走这种超级独立的掠食猛禽并不难,只要找到一处野林,打开箱子就行了,于是全英国有志一同的驯鹰人开始了复育计划。这群欧陆苍鹰来自瑞典、德国与芬兰,多半都是北方寒带针叶林的巨型苍鹰。有些是人类刻意野放,有些则只是迷路了。那些存活下来的苍鹰找到彼此,隐秘地繁衍了后代,成果斐然。如今,它们的后代多达四百五十对。尽管它们行踪飘忽,却仍气宇不凡,自在地活在这片土地上。它们存活下来推翻了我们的刻板印象:从未被人类野心私利玷污的才算自然野性;有时候,人类也能成就野性。
现在是八点半。我低头瞥见从土壤窜出头的一小枝十大功劳,赭红嫩叶仿佛上光的皮革。这时我抬起头,看见了我念念不忘的苍鹰。它们现身了。是翱翔于温暖天际的一对苍鹰。阳光如温暖的厚实掌心抚触我的后颈,但当我看着苍鹰踪影时,鼻子也吸进了冰冷无比的空气,夹杂着蕨类植物与松脂的芬芳。苍鹰鸡尾酒。自在飞翔于天空的苍鹰呈现出一种繁复的灰,不算是岩石灰,也不能说是鸽灰,那是一种如乌云般的灰黑,尽管它们离我很远,还是能看得出洁白如粉扑的白色尾羽向后开展,尾巴丰厚结实,翱翔时曲线独特优雅的次级飞羽,让它们与雀鹰有天壤之别。这时候,一群乌鸦飞来扰动它们,但它们不在乎,谁管你们!有只乌鸦向上直朝雄鹰飞去,但它只是轻松抬起一边翅膀,让乌鸦经过。乌鸦不是傻子,不愿屈居苍鹰下方。这对苍鹰还不算完全的求偶炫耀,因为我没看到书中提过的“俯冲特技”。它们尊重彼此间的距离,运用空间,借力使力,创造出若即若离的优雅姿态。拍拍几次翅膀后,雄鹰飞到雌鹰上方,凭风朝北滑翔,接着俯冲而下,利落平滑如下笔般倏地出现在雌鹰下方,雌鹰摆动一边翅膀,随雄鹰比翼飞翔。在一棵松树树梢一阵盘旋后,它们消失了。前一分钟,我的苍鹰才在天空向我阐述物理课本上的飞行原理,随即消失不见,我不记得自己曾低头或别开视线。或许我眨了眼,就是如此。它们趁着我大脑运作的细微空当,就这么隐身于密林间了。

我坐了下来,疲惫但满足。苍鹰离开了,天空恢复安静。时间分秒过去,周遭的光线波长缩短了,日子挨过了时间。一只如木头玩具的小雀鹰从我膝前飞掠而过,轻巧如风筝般地越过一片黑莓丛,消逝在林间。我望着它离去,迷失在自己的回忆中。它竟能如此鲜明又难以抗拒。空气弥漫松脂与木蚁酸的刺鼻味。仍是小女孩的我,手指绕着东德进口望远镜的系绳。我觉得很无聊。我才九岁。爸爸站在我身边。我们在找雀鹰。那是个七月午后,它们的巢在附近。我们期待着难得一见的画面:鸟儿滑翔扫过松树林顶时,如潜舰余波般的摇曳树影;鹰眼锐利的黄色光芒;深绿松针间的黑白条纹鸟腹,或是萨里天空中的极速黑点。阳光在松树间投下不规则的阴影,在这橙红和黑色的光影与林木之间的幽暗处紧盯寻觅,一开始似乎很有趣。但当你九岁时,等待简直要人命。我穿了橡胶靴的脚踢着篱笆。全身扭动,烦躁无比。长叹一声,用手指摇晃篱笆。爸爸看见我这模样,似乎有点恼怒,却也觉得好笑,然后他对我解释了耐心。他要我谨记于心:当你很想很想看到一样东西,有时就得维持不动,一直待在同个地点;牢牢记住自己有多想看到的心意,并保持耐心。“我帮报社拍照时,”他说,“有时得坐在车里好几小时,才拍到一张勉强能用的照片,还不能随便下车喝杯茶或上厕所。我只能耐住性子等候。如果你想看到雀鹰,就不能没耐心。”他的神情严肃认真,但并不恼怒。他在告诉我大人世界的真相,但我只是闷闷不乐点点头,瞪着地面。对我来说,这段话根本是说教,才不是什么建议,我完全不懂他说这番话的用意。
你学到了。今天,我心想,我不再九岁,并且不再感到无聊,我很有耐心地等待,鹰果然出现了。我慢慢起身,腿因为坐了太久有些发麻,我发现自己顺手抓了一小把石蕊,这浅灰绿色的地衣在地球任何角落都能生存。这也是耐心的功劳。如果将石蕊留在暗处,冷冻也好,干燥也好,它都不会凋零,只会静静蛰伏,等待对自己有利的时机。狠角色。我在手心掂掂它,几乎没有重量。我一时兴起,将这份从大自然偷来的娇小纪念品塞进夹克内袋,带着回家,毕竟它也陪我目睹了苍鹰。我将它放在电话旁的架上。三周后,当妈妈来电话时,我就紧盯着这株石蕊,她说爸爸去世了。
作者:[英]海伦·麦克唐纳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素材提供:世纪文景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