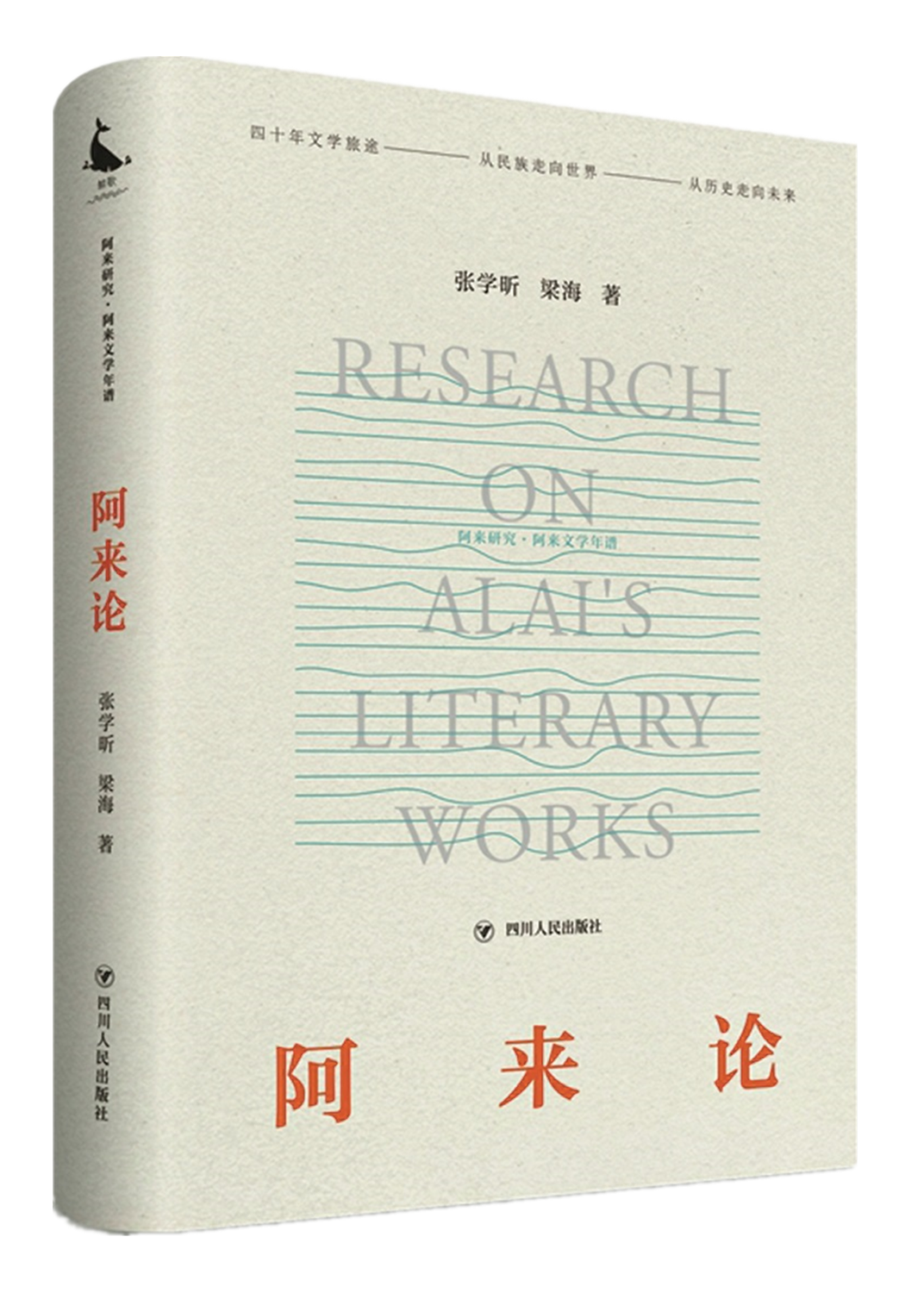
《阿来论》
张学昕 梁 海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当下批评界,有相当一部分批评者操持着西方的理论,熟练地对作家及文本进行着技术的剖析,但我们却很难感受到批评者与批评对象心灵的碰撞,感受不到阐释的冲动与激情,而真正触及文本的评论,必是触及作家的灵魂,是一次心灵对心灵的体悟,精神向精神的作揖,才情与才情的拥抱。近日,张学昕、梁海两位评论家合著的《阿来论》出版,正是以其独具的整体批评姿态和审美品质,为当代文学评论界提供了一份出色的批评实践。两位评论家以十余年的“跟踪式”考察、“心灵抵达式”研究,对作家阿来40年的创作生涯做了一次完整回顾。他们致敬阿来,解读阿来,寻找“大地的阶梯”并以此记阿来研究之“流年”,其中的《阿来文学年谱》还提供了阿来写作、生活大事记,由此也成为阿来文化符号解读的一个“标志符”。
张学昕在评论界深耕多年,“始终崇尚批评者与文本乃至作家之间的精神契合”“实现精神同构”,“文学理想的暗合”更是他选择批评对象的重要前提。他对阿来的关注,不仅仅是因为阿来“当代文学标志性人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评论文字中感受到他被阿来点燃的兴奋点和同频共振的心灵节律,批评同样也是一颗心与另一颗心的碰撞。
论著第一辑共两篇:《阿来论》《抵达经典的一种可能——阿来创作论》。两位批评家分别从自己的视角切入,对阿来的整体创作做了宏观的把握。两篇文章均由对阿来的独特“发现”及由此形成的强烈问题意识引领,作为探寻其隐秘内心世界的入口;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分析阐释贯穿全文,在抵达阿来灵魂隐秘的同时,也抵达了阿来创作奥义的深处。首篇《阿来论》即是用“心”发现了阿来创作的一个被忽略的关键词——“行旅”,以此来探寻阿来的写作发生学,洞幽他灵魂、精神世界的深处的“巨大隐秘”——“期待文字之外,存在一个没有因时代过度递进和变迁的人的安详、坦然和平静的状态”。由此出发,作者将阿来的写作界定为“行走在大地的阶梯”上的写作。对《尘埃落定》《空山》《云中记》等小说的深入、唯美解读,让我们体悟到“文学的阶梯与阶梯之间,不仅架构着历史、现实,还延展着自然和人性”。张学昕以自己的学术敏感、宏阔视野、尤其对阿来内心幽微的洞察,拨开阿来神话的迷雾,从高处纵览阿来近40年创作的“进阶”之美、之魅。他犹如一个好向导,对阅读者发出“请跟我来”的文学邀约,带领他们一步步攀登,最终站在“大地阶梯”的最高处回望,每一级阶梯的独有风景及各级阶梯渐进的无限风光都尽收眼底。我想,这就是对阿来的最好还原,也是批评的一种胜境。真正好的批评不是自我的“独语”,而是引领读者共同进入作家心灵世界的隐秘通道,在不断渐进中与作家共同抵达对人、自然、存在、生命的关怀与叩问。
梁海的《抵达经典的一种可能——阿来创作论》则从阿来对柔弱花草的醉心入手,发现并探寻“自然界轻灵花语”与阿来厚重的文学世界的隐秘勾连,将其视为阿来不竭创作灵感的来源。

▲作家阿来,摄于2021年
阿来正是要借助大自然中神秘与未知的力量,重新激发人们曾经失去的想象和敬畏,使人们所渴望的舒展和纯粹的生活状态能在自然的本真与原初中得以唤醒……这种灵性的世界观和审美取向,已然化为藏民族传承与他的血缘基因,让他在吸纳和排除外部的美学扰动之后,获取了属于自己的最独特的叙事起点。
梁海从“写作发生”的角度切入,以“灵性”叙事起点为自己的研究起点,发现并细致阐释由“灵性”延展生发出“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的独有审美价值:在错位、移植和并置中摇曳出的别样美感”的语言、跨文体的别样叙事、神话和史诗的精神品格,让阿来拥有了在当代汉语写作中无可复制的“原创性”。进而,她对阿来藏地书写的审美“陌生性”进行“抵达经典可能性”辨析,目光穿透阿来汉语写作“陌生性”的奇异美感外壳,向纵深发掘出普适性的价值和人文关怀的内核,从而做出“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思考,建构民族记忆之上的人类生存寓言”的审美判断。梁海由对阿来的细部感觉入手,探究其写作发生,层层递进,一路欣赏花开花落,最终带领阅读者攀援于阿来文学“大地的阶梯”最高处,俯卧、贴近、触摸他博大的人类情怀,倾听他心灵的律动;仰望,静观、品悟他原创书写天空的云卷云舒、溢彩流光。
两位批评家对阿来的整体评论都由写作发生学为阐释、分析、判断的逻辑起点,以一颗心灵去撞击另一颗心灵,不断向阿来的内心深处掘进,穿越“历史”“民族”“地域”“诗性”“空灵”“救赎”的表象地带,最终抵达“阿来之所以为阿来”的本质与内核,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对阿来进行“文学经典化”的阐释初衷、也确立了当下“经典”的衡量判断标准。

▲左起:张学昕、阿来、梁海。摄于2021年《阿来论》首发式
谁愿意在残花中瞭望破败晚秋的降临呢?对于自然而言,大地的枯谢和绿色的堙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生机的毁损,成熟像伤疤般长出了锈迹。人类在近一个多世纪时间里的干涉和放纵,消弭和切割了多少自然的生物链条。我们既不愿意看到开败的“残花”,更不愿意看见地貌上的任何一种生物随风飘散般消逝,香消玉殒。风吹来的种子,又被风裹挟而去,是格外凄清和伤感的事情。这样,人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每一个种子,都把整体作为生命的未来及其可能性,包藏在自己的体内,它将尚处于胚芽状态的神性的逻辑植入大地,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小心翼翼地敬畏和服侍我们脚下的土壤呢?
这是《阿来的植物学》中的一段话,带有极强的散文诗性质,是张学昕探寻阿来对植物的热爱、痴迷时,对人与自然美轮美奂的相互呼应的感怀,他将自己对植物生命及生长于斯的大地的敬畏,对人类“消弭和切割自然的生物链条”的痛心,以诗意唯美的形式,传递出来,在“把自己也烧进去中”完成了“文本另一次写作过程”。此类带有浓浓“唯美叙述风”的“另一次写作”在论著中随处可见,批评家鲜明的个性风格得到充分彰显。“我注阿来”“阿来注我”的交织让批评文本张力十足,在相互的心灵抵达中凝聚、裂变为更强大的阐释力量。这样的自我阐发式批评让我不禁联想到,“让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在行间”,是阿来的书写情怀,但又何尝不是批评家的阐释追求?我想,这或许是文学生产链条的最佳“生态”——批评家以此完成了对作家的心灵呼应,也引领阅读者共情共振,在文学灵魂的隧道中,张开双臂,飞升、净化、遇见更美好的自己,文学也便抵达了它的终极意义。
被理论绑缚只能让批评陷于没有灵魂的“生命空壳”境地,而“云中漫步”才是《阿来论》追求的批评境界与姿态。这份诗意灵动而又不乏厚重的阐释也契合了阿来“神性”的精神气质和行走于“大地阶梯”的写作气度。从这个意义看,《阿来论》无疑是阿来研究、也是作家论的一个范例。
本文作者徐晓杰:文学博士,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作者:徐晓杰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