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阅读世界文学》
[美]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著
陈广琛 秦烨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世界文学灿若星辰,也浩如烟海。我们到底应该读什么、怎样读才能进入文学的多重世界?达姆罗什总结了他和宇文所安等教授在哈佛的授课经验,为此提供了具体的方法和一系列阅读模式。
达姆罗什还通过鲜活生动的例子,带领读者体会历代文学瑰宝的丰富与魅力,这些作者和文本包括:《吉尔伽美什》、迦梨陀娑、索福克勒斯、杜甫、紫式部、《一千零一夜》、莫里哀、休谟、康拉德、鲁迅、博尔赫斯、张爱玲、沃尔科特、索因卡等等。
>>书摘
最黑暗的非洲,正在陷入黑暗的伦敦
三个世纪之后,另一个水手的航行催生出整个欧洲帝国时代的所有虚构叙事中最深刻的作品之一——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之心》(1899)。与《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和《奥鲁诺克》一样,康拉德的中篇小说取材自一段旅程,其目的地刚果成为故事的主要场景;这个地区当时是比利时国王列奥波德管辖下的商业机构。康拉德1857年生于乌克兰,他的父母是波兰人。他先后在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远洋商船上工作,最终在1890年代中期决心成为一名用英语写作的作家,而英语是他的第二门外语。跟之前的卡蒙斯和同时代的鲁德亚德·吉卜林一样,康拉德的作品大多取材自他的远游经历;他把故事设定在印度尼西亚、印度洋、南美洲、非洲和欧洲。在结束航海事业之后,他定居于英国;但对于康拉德来说,这个第二祖国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异国。虽然他最终成为一个英国公民,却一直都是一个主要以世界性视野写作的作家。

▲康拉德
康拉德与英语、英格兰的关系,类似于一个亲密的异乡人。他的英国友人对他能够如此深刻而又微妙地使用自己的语言感到困惑(也有一丝嫉妒)。吉卜林评论道:“当他手握着笔时,他是我们之中最棒的。”但他也补充道:“阅读他的作品时,我总感到自己是在读一部外国作品的优秀翻译版本。”(博雅斯基《吉卜林对话录》)H. G. 韦尔斯评论康拉德说的英语“很奇怪”,但是也承认“他编织出一种异常丰富的描述性英语散文,一种新的只属于他自己的英语,很明显地完全没有陈词滥调”(韦尔斯《自传实验》)。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23年的一篇随笔中所说:
显然他是一个奇怪的幽灵,在19世纪末年空降到这个岛上——一个艺术家、一个贵族、一个波兰人……因为过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是不能把他看作一个英国作家。他太正式了,太客气了,对这门并不属于他的语言,使用得太谨小慎微了。(伍尔夫《康拉德先生:一段对话》)
而到这时候,康拉德早已把英语变成属于他自己的语言空间了。
在《黑暗之心》中,康拉德编织出一张细密而空灵虚幻的语言之网,来传达他那粗粝的经历。那是一段沿着河流行进的旅程,一段令人深感不安的心灵旅行。在其中,帝国主义的理想逐渐沦入疯狂的境地。在1890年,他得到一份工作,为一家比利时公司在刚果河上驾驶一艘蒸汽船。这家公司借助奴隶的劳动剥削刚果的自然资源。这段航程为他的中篇小说提供了最初的灵感,结果,康拉德那正在拓展的作家理想也由此被赋予了崭新的、强烈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在回程的旅途中,他带上了一个垂死的公司职员——乔治·克莱恩;此人后来成为小说中那个令人恐惧的自大狂库尔兹先生的原型,他是公司里一流的象牙收集者。在小说中,作为叙事者的水手马洛被公司派遣,逆流而上去与库尔兹先生会面;后者作为科学与进步的使者进入刚果。然而,马洛惊讶地发现,垂死的库尔兹正处于恐怖而野蛮的场景中,欧洲的理想在此已经崩溃。
小说对帝国主义毫不留情的解构,正是建基于康拉德亲身的经历,而我们对它的体验,又受到现实中列奥波德国王野蛮的殖民行为的影响。但是,读者对马洛旅程的理解呈现出激烈的两极分化。我们果真能在其中读到非洲吗?还是只不过瞥见马洛想象出来的、自我灵魂在暗夜中的存在主义幻象?我们目睹的是欧洲帝国主义的本质性腐朽,还是更加模棱两可的帝国主义的失败?又或者,我们是不是看到了一种荒蛮的原始状态,它是如此没有节制、不可救药,以至于康拉德在批评帝国主义种族偏见的同时也在强化它?这最后一种看法,被尼日利亚小说家奇努阿·阿切贝有力地提出来;他写于1958年的小说《瓦解》可以被看作从另一个角度讲述的帝国殖民故事。他在题为《非洲之像:康拉德〈黑暗之心〉中的种族偏见》的散文中展开对康拉德的批判。他尖锐地批评康拉德,让其笔下的非洲人物完全不具备流畅通顺的语言能力,又或者任何独立自主的行为。他指控康拉德所表现的不过是——
纯粹作为背景板的非洲,在其中,非洲人作为人的元素被完全取消了。非洲成了一个形而上的战场,其中毫无任何可辨认的人性可言;欧洲人在其中游荡,后果自负。把非洲降格为一个布景,用来衬托一个卑微的欧洲大脑的堕落,这当然表现了一种荒谬和变态的傲慢。但这还不是关键。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古老的态度曾经并且现在还在鼓励全世界对非洲和非洲人的非人化。真正的问题在于,一部颂扬这种对一部分人类进行非人化描述的小说,居然可以被称作伟大的艺术品。我的回答是:不,它不可以。(阿切贝《非洲之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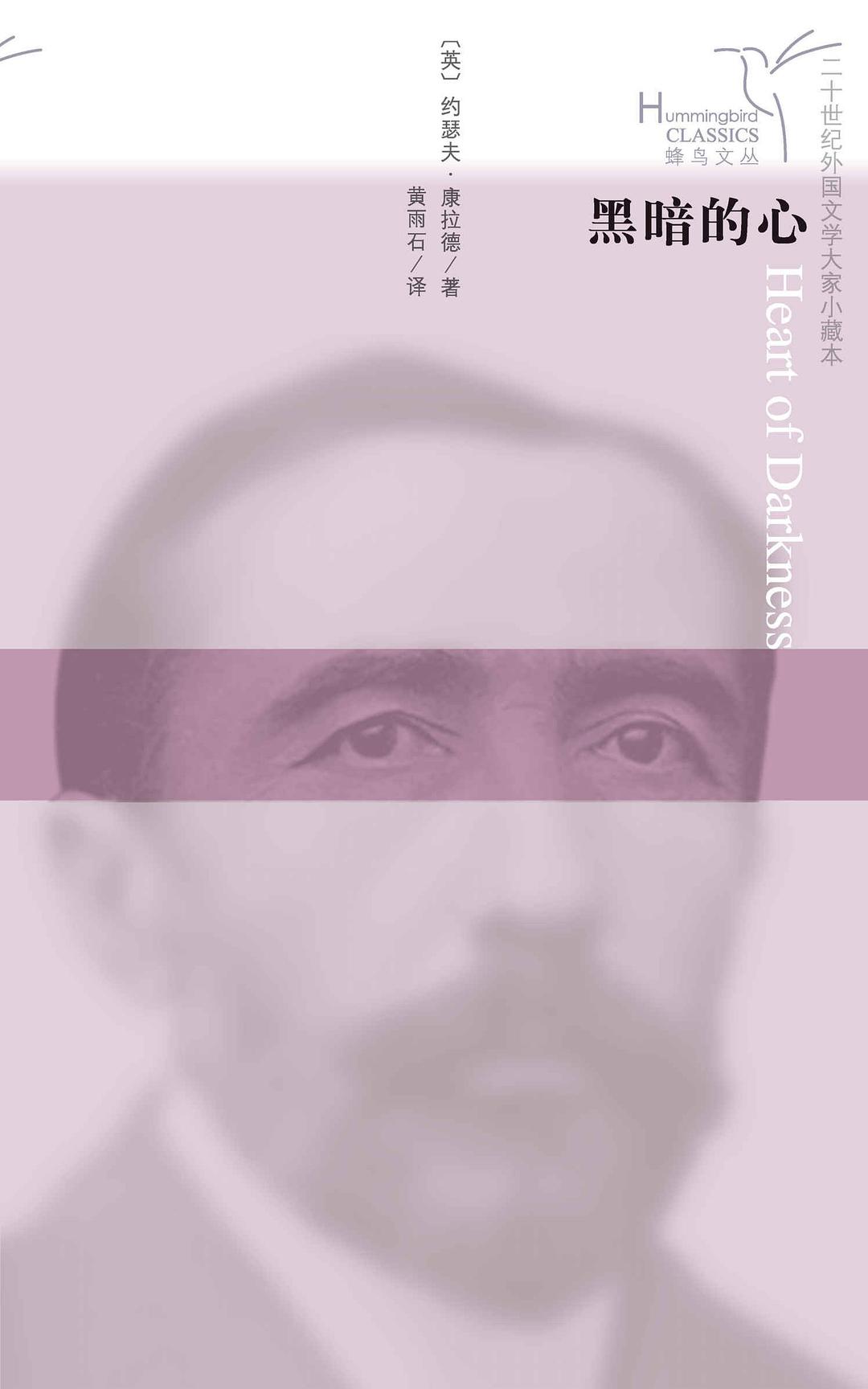
当阿切贝在1977年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黑暗之心》正被广泛地理解为关于库尔兹和马洛心理斗争的故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评论家注意到它的政治性,但仅限于对欧洲殖民行径的批判;没有几个英国或美国读者会留意康拉德对活生生的非洲人的表现。这本小说把非洲人表现为一块对欧洲人的活动构成威胁的布景板。阿切贝论点的重要贡献之一,是纠正读者对这一层面的模棱两可的态度。
同时,阿切贝的批判也反映了一个写实主义小说家对康拉德现代主义模糊手法的不耐烦。康拉德通过某种类似于文学印象派的风格,迫使我们通过马洛的眼睛来体验非洲;但是马洛远非一个像卡蒙斯的达伽玛或者吉卜林的金那样的客观观察者。康拉德多次打破马洛作为叙事者的权威,有力地减弱了所有简单化的种族主义描写,而这正是马洛和库尔兹经常做的事情。故事并不是开始于非洲,而是在一艘名为奈利的游艇上,它停泊在泰晤士河边,在伦敦城外。一个形象模糊的叙述者转述了马洛的故事,但是语调中明显带有讽刺和不信任的意味。随着夜幕降临,马洛的形象变得越来越不清晰,但是他却错误地告诉听众:“当然了,你们现在肯定比我当时看得更清楚。”(康拉德《黑暗之心》)他嘲笑库尔兹和其他公司职员,把象牙变成一种被崇拜的偶像。满腹狐疑的叙事者说,在这个过程中,马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穿着欧式服装、没有莲座的佛陀,在给我们布道”。康拉德对他的故事主角做了吊诡的处理:马洛觉得自己已经厌倦了尘世,但似乎又有种幻觉,以为自己失去了所有的幻觉。
阿芙拉·贝恩强调自己是一个不受男权主导的殖民体制误导的女性;通过这种方式,她加强了自己叙事的权威性。相反,康拉德从内部削弱了殖民体制的男权特质。在小说中,从始至终康拉德都在隐晦地讽刺马洛身上残留的那点帝国主义男子气概。一开始,马洛就不得不依靠一个有广泛社会关系的舅妈来获得这份刚果的工作;他为此感到尴尬:“我,查理·马洛,要女人来帮忙找工作。天啊!”最终,马洛在库尔兹死后回到英国,并对库尔兹的未婚妻表示哀悼。当她恳求马洛告诉她自己爱人的临终遗言时,马洛不再像一个自以为无所不知的自大狂:“我感到一股寒气直冲胸膛。‘别’,我低声说。”现在他不再有权威了,而是听起来像一个强奸的受害者。在压力下,他不再像平时那样坚持说真话;他没有透露库尔兹真正的临终遗言——“可怕啊!可怕啊!”而是谎称他说出了她的名字。听到自己想听的话之后,库尔兹的未婚妻(作者始终没有告诉我们她的名字)发出了胜利的呼喊,然后让马洛离开。
马洛尝试把帝国主义看作被它背后的“理想”拯救了,又或者比较朴素地、被具体的人的工作拯救了。但是小说的叙事逐渐把这两种逻辑都消解了。马洛不断遇到越来越癫狂的人推销探险和掠夺活动,比如一群自称“黄金国探险组”的人——他们在找寻伏尔泰所说的钻石遍地的乌托邦,却居然不知道自己登陆了错误的大陆。无论马洛到哪里,他都遇到各种冰冷的反讽,从拖拉的铁路工程,到在没有铆钉的情况下试图修理损坏的蒸汽船,再到库尔兹营地周围的桩柱上那些精心安置的骷髅头。康拉德把当时欧洲对非洲的各种种族偏见发挥得淋漓尽致,但跟后来的阿切贝不同,他的目的不是要批驳它们,而是要借此暴露出所谓的文明欧洲与作为他者的非洲之间极为模糊的分界线。
如果说贝恩把奥鲁诺克拔高为恺撒再世,那么康拉德则通过把罗马时期的英国置换为早期的非洲,以此消解帝国殖民的合理性——在故事的一开始,面对着落日中的伦敦,马洛说:“这也曾经是地球上一个阴暗的地方。”他描述了一个想象中的罗马兵团从泰晤士河逆流而上的阴森经历:
载着军需品,或者货物,或者任何东西,逆流而上。沙滩、沼泽地、森林、野蛮人——没有什么适合文明人吃的东西,除了泰晤士河的河水外,没有别的可喝……寒冷、浓雾、暴风雨、疾病、流放,还有死亡——死亡弥漫在空气中、在水里、在丛林之间。在这里,他们肯定就像苍蝇一样死去。
早期的英格兰,幻化为“至暗非洲”的镜像。而当马洛叙述他的故事时,夜幕正在降临。马洛从陌生的大陆归来,发现大英帝国的正中央,文明和野蛮正互相纠缠、难分难解。
>>作者简介
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
哈佛大学厄内斯特·伯恩鲍姆比较文学讲席教授,比较文学系主任。曾任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著有《埋藏之书:吉尔伽美什史诗的消失与重现》《什么是世界文学?》《如何阅读世界文学》《比较文学:全球时代的文学研究》《八十本书环游地球》等;主编的世界文学教材和原典选读有《朗文世界文学选集》(六卷)《朗文英国文学选集》《普林斯顿比较文学文库》《劳特里奇比较文学论文集》等。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是一位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学者。
作者:大卫·达姆罗什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