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年在欧美文坛叱咤风云的明星作家海明威身后给世人留下了诸多谜团,而他的死因便是其中之一。据警方的说法,1961年夏日的一个清晨,他在家中用猎枪向头颅射击,饮弹身亡,但他的第四任妻子玛丽·韦尔什则断言这是一次意外事故,在她的看来,海明威不会自杀,这与他惯常所持的理念相悖。他曾将自杀视为人世间“唯一毫无意义的事情。”许多人对她的说辞坚信不疑。但海明威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健康状况日趋恶化,由于电震疗法丧失了记忆力。先前体魄健壮的他实在难以忍受无法创作、无法狩猎的废人状态,不想再苟活于世,因而毅然以自己的双手结束生命也是情理中事。这和他信奉的可以被毁灭不能被打败的硬汉精神一脉相承,况且他的父亲也是自杀离世,仿佛他身上携带的父辈隐秘的基因到了合适的时机,便顽强地破土而出。
平心而论,海明威并不是天生的硬汉。在和平繁荣的新大陆度过了青少年快乐散漫的时光,1918年他未满19岁,便和众多美国青年一起,志愿参加了红十字救护队,奔赴欧战前线,想在枪林弹雨中寻觅生与死的极限体验。在意大利前线,他受了重伤,做了12次手术,取出了200多枚弹片。与肉体上的创伤相比,精神上的伤痛烙刻在他灵魂深处。回国后好长一段时间里,他万念俱灰,先前浪漫色彩十足的玫瑰色云霓荡然无存,直至他担任记者常驻巴黎时,精神上的抑郁颓靡仍时时显山露水。怪不得长年旅居法国的美国作家葛特鲁德·斯坦因将海明威这代年轻人称为“迷惘的一代”,在她眼里,他们是一无所信的醉汉,彷徨于无地。她不经意间说出的这句话后来成了海明威这一代作家的醒目标签。
海明威早年的两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忠实地映射出他这一时期迷惘的心态。《太阳照常升起》中的主人公巴恩斯年方20多,正值风华正茂的时刻,但他的生命其实已经结束了,行尸走肉般徜徉在巴黎街头,不时以酒精麻痹敏感的神经。他不但心灵抑郁,而且也无法尽情地及时行乐,因为战时脊椎受伤使他失去了性能力。和他相恋的英国人阿施利夫人无奈在多个男人间周旋,游戏人生。过后他们俩和数位朋友去西班牙观赏极富刺激性的斗牛比赛。喧嚷的观众,血腥的气味,帅气英武的斗牛士——这一切让巴恩斯暂时忘却了自身的残损,迷醉在原始生命力恣意挥洒的盛宴中。让他心有不甘的是,竟眼睁睁地目睹了阿施利夫人与年仅19岁的斗牛士罗梅罗虽然无果但却热烈迷醉的恋情。全书收尾时阿施利夫人悄悄对他说他们俩要能在一起多好,巴恩斯的回答是“这样想想不也很好吗!”读者不难从话中听出强忍的悲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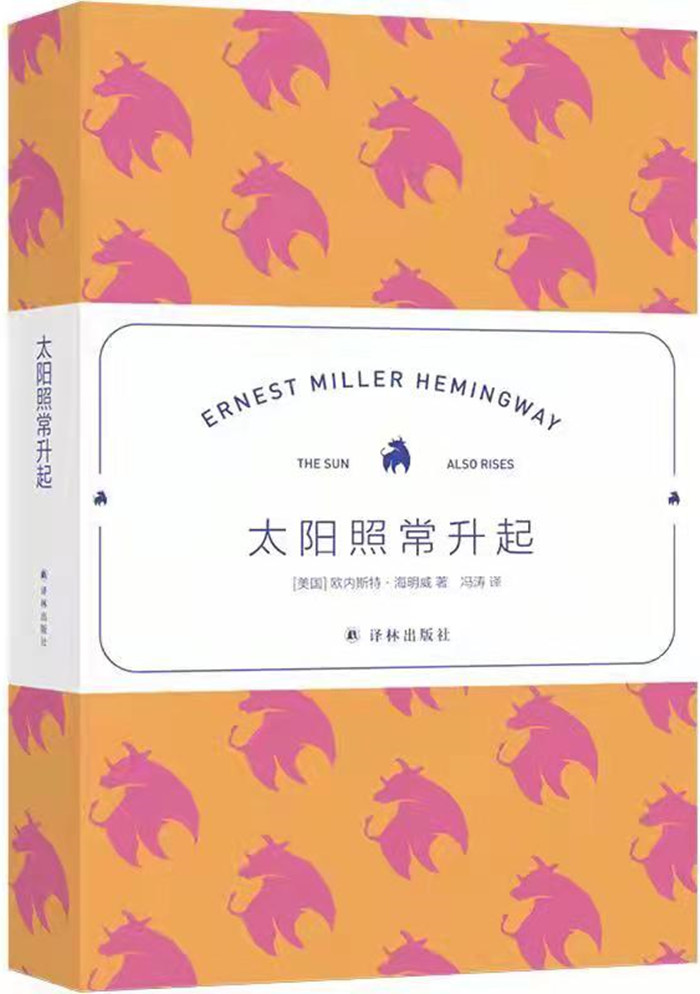
稍后问世的《永别了,武器》更多地展现出海明威本人一战时在意大利前线的经历。和巴恩斯相比,亨利尽管也负了伤,但幸运的是他还能爱,也有人爱他。他与英籍护士凯瑟琳的恋情成了战争阴云中的一抹亮色。战争的种种残酷、荒谬使他极度憎恶,一度几乎成为枪下冤鬼。他侥幸逃脱后带着凯瑟琳来到了中立国瑞士,过上了神仙般的隐居生活。但好景不长,老天和他开了个冷酷的玩笑,凯瑟琳分娩时难产而死,将亨利孤零零地抛在这昏暗无光的人世间。虽然他以斯多噶式的隐忍坚毅面对爱人离世,但最终无法走出迷惘的阴影。
到了十余年后问世的《丧钟为谁而鸣》,海明威画风为之大变。占据人们视野的不再是巴恩斯、亨利这样的迷惘者,而是勇敢自信的罗伯特·乔丹。他原本在大学中教授西班牙语,过着安静的学院生活。当西班牙内战烽烟四起,他在信仰的感召下奔赴前线,誓为大众自由解放的事业而斗争。他排除万难,完成了炸桥的任务,本人受伤后为了不连累战友,毅然孤身留下与敌军对峙。可以料想,牺牲成了他的必然归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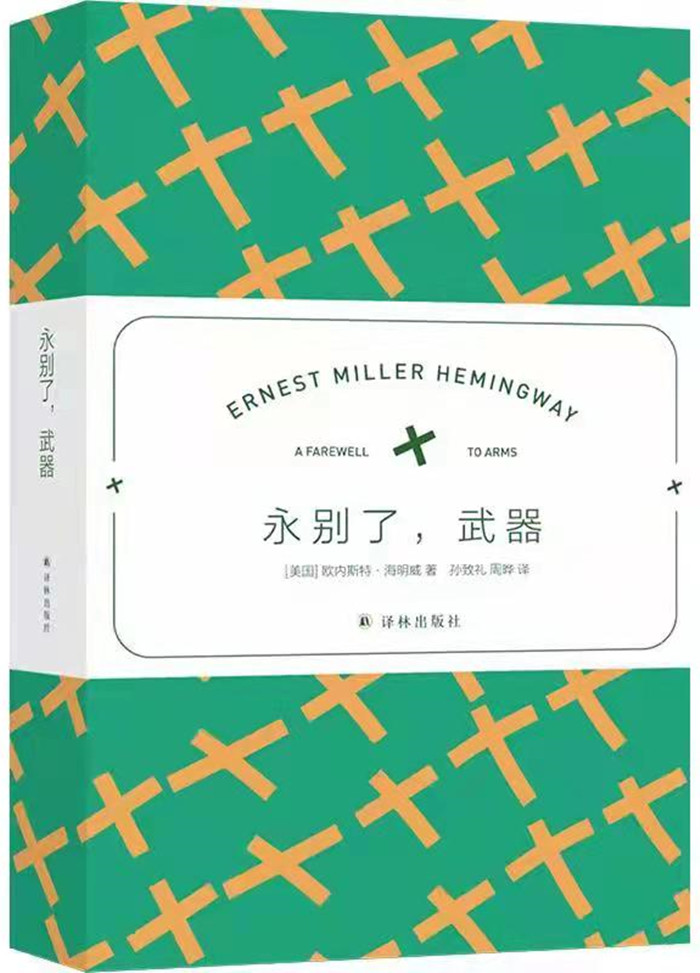
乔丹可谓海明威塑造的新人形象。它一扫先前蒙罩在诸多人物头上的阴霾,呈现出一股罕有的清新爽健之气。尽管作者详尽细腻地展现了内战的种种惨状,西班牙特有的南国的温润的氤氲让整部作品抹上了一层地中海阳光绚烂的色调。乔丹足智多谋,但并不缺乏柔情。他和曾受蹂躏的少女玛丽亚的恋情无疑是全书中写得最为动人的篇章,它淋漓尽致地展示出生命的美好壮丽,反衬出战争的残酷无情。乔丹是海明威心仪的硬汉形象系列中的一员,虽然他有着丰富的内心生活,但他并不是沉溺于冥想的哈姆莱特,他是一个行动者,甘愿在战火中印证自身的价值。他一身正气,有时不免让人感到太过完美,但他伟岸刚毅的形象时时感召着人们。
到了晚期的《老人与海》中,海明威将具体的社会环境悉数抹去,以近乎抽象画的方式在不长的篇幅中聚焦夫圣地亚哥悲壮之至的捕鱼经历。他先是84天没打到鱼,后好不容易钓到一条大马林鱼后,归途中多次遭到鲨鱼袭击,返港后只剩下鱼头鱼尾和脊骨。圣地亚哥最为鲜明地体现了海明威硬汉哲学的内核,在老人的这番话中奏出了苍凉悲壮的最强音:“然而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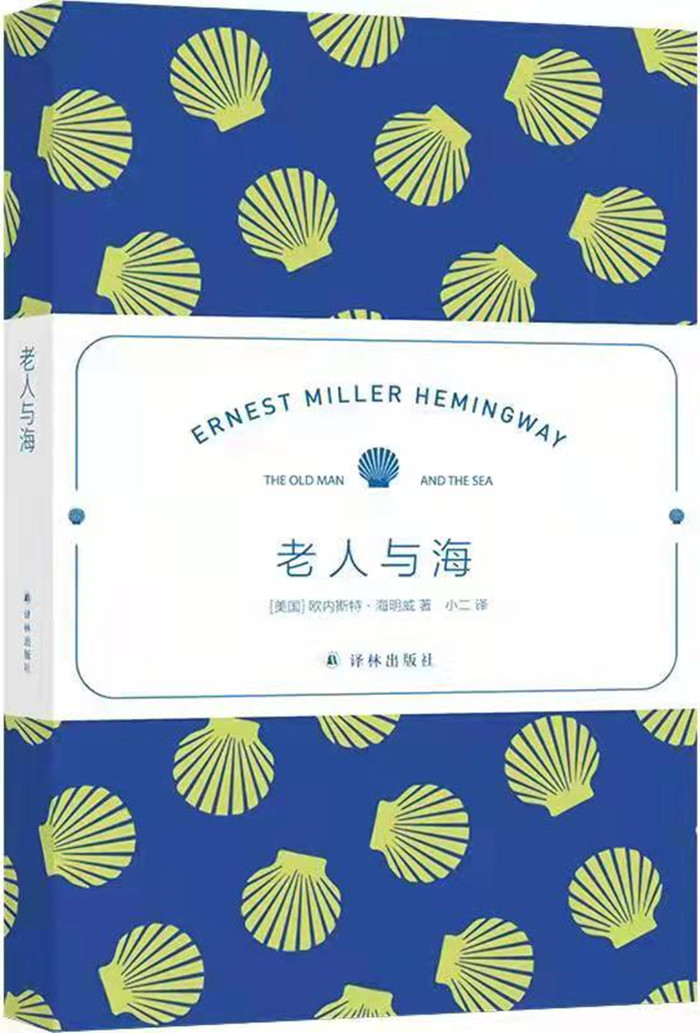
熟悉美国文学的读者不难发现,《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和麦尔维尔《白鲸》中的主人公埃哈伯船长颇多相似之处。正如作家格非指出,麦尔维尔对死命追捕白鲸的埃哈伯船长的态度是双重的,他既赞叹其无所畏惧的勇气,又察觉中到其间蕴含的疯狂与病态。正是对人性内在双重性的认识,麦尔维尔触及到了人性深处的黑暗面。相比之下,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则要单纯得多。海明威本人也是一个行动者,他不是在沉思冥想,而是在斗牛、狩猎等冒险中探测人性的极限与秘密。从本性上说,他或许并不是一个大无畏的勇者,硬汉形象成了他精心打造的面具,他藉此来应对人生的挑战,抵御虚无,确立自身的意义。作为灵长类动物,出于求生的本能,人们时不时会在未知的艰险前怯懦退缩,时不时会一败涂地,正如帕斯卡尔所说,“我们所有的快乐都不过是虚幻,我们的苦难是无穷无尽的,而且最后那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我们的死亡,它会确切无误地在知短的若干年内就把我们置诸于不是永远消灾就是永远不幸的那种可怕的必然之中。”在此情形中,如何确立人生的价值支点,就成了不容回避的挑战。海明威锻造出了硬汉哲学作为盾牌,既保护自己,又给稍纵即逝的人生涂上了瑰丽的霓虹。也正因为是面具,所以它如一桢黑白照片,对比鲜明,但剔除了大千世界繁富的色彩,有时难免显得单调,无法将人生多层次的细微皱褶纤毫无爽地展现出来。他那富于极简主义特色的冰山式文字风格更是加强了这一倾向。刚辞世的文学批评家斯坦纳在《逃离言词》一文中曾坦爽直言,海明威的“这种风格将福楼拜‘每个词恰如其分’的理论退化到基础语言的水平”,“这种风格背后是最狭隘的文化资源观”。在他眼里,海明威“把语言紧缩到一种有力的抒情速写”,这种语言“怎么能传达能言善道之人的丰富内心生活?”虽然言辞不无苛刻,但却揭示出海明威文学才华的边界,也标示出硬汉形象的极限。
作者:王宏图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