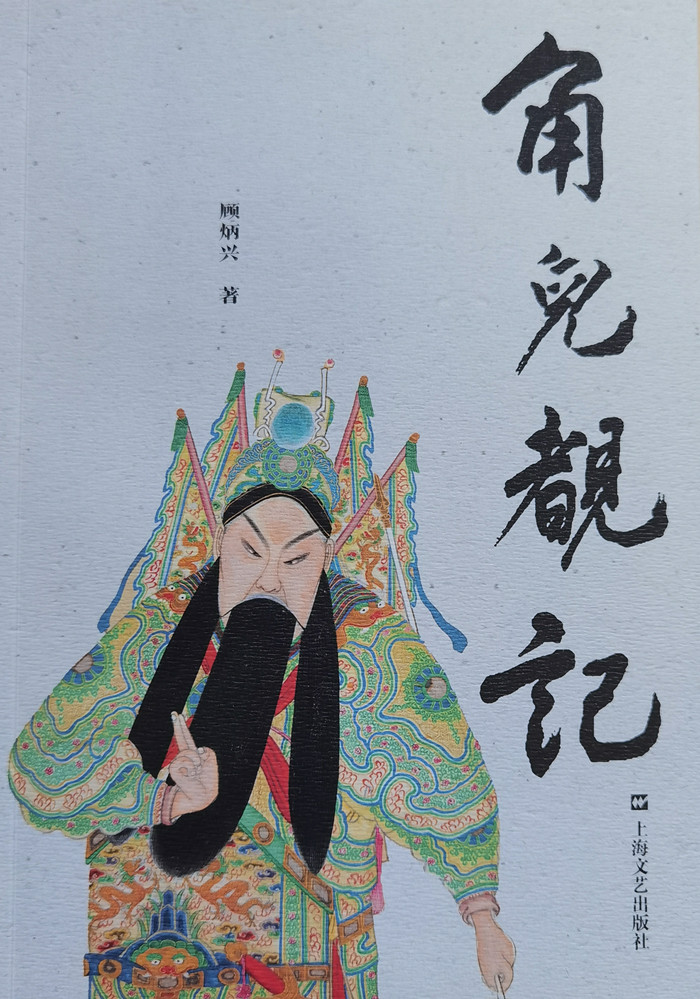
《角儿睹记》
顾炳兴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顾炳兴老先生将数十年来所撰戏曲文章加以精选、编辑、结集,嘱我作序。我自欣然应命,盖因我与顾老既有一段因缘存焉,更有一番感慨寄之。
十六年前,我受命出任一家戏剧杂志社的主编。杂志影响甚大,稿件应接不暇,尤以各类戏曲文章最多。作为一名十多年工龄的职业读者,我对这些文章的阅读体验是有变化的——初感皆佳,开卷不惟有益而且得理;但读多了,难免倦怠起来。总体而言,阅读口味变得越来越“刁”。这不是指戏曲的话题不多,也不是嫌弃文章的质量不高。恰恰相反,吾国戏剧博大精深,实在谈不胜谈、写不胜写;刊发文章达标及准,无不有根有据、夹叙夹议。然而旁征博引,所得难免类似;尽管殚精竭虑,所见大多雷同。其中的大多数,文字洋洋洒洒,用词佶佶屈屈,辨析滔滔滚滚,引证条条框框,然而读着读着,总感纸背缺了某些东西,却也难以看清、无从道明。
几年之后,读到顾老来稿,感觉颇不相同——没有论文定式,没有深奥词句,没有学术做派,有的是真切的观赏体验、寻常的行文样态、简单的资料佐证、即兴的点评感慨。后来顾老来访,交谈之下,得知他自童年起便随父出入上海各大戏院,饱览各类戏剧演出,尤以京剧最多。那时的京剧,是大众艺术,时兴、火爆、通俗、平民化,一如顾老的文字和文风。幼时的濡染,很容易成为一生的习惯。于是从少年到青年,从中年到老年,顾老看戏票戏、扮戏唱戏,岂止成了业余爱好,而且成了生活方式,与京剧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他是一名京剧盛世的亲历者,是一名戏曲艺术的热衷者,又是一名勤思善文、传广播远的写作者。至此,我的前疑得到开释,学院派、学术流、师生们,尤其是大量不到五十岁的年轻学者们,必然不会亲历,多半不会热衷,只是专注写作,将戏曲作了研究的对象、教学的内容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媒介。没了亲历,少了热衷,只剩下了写作,于是文中多的是西式的名词和晦涩的长句,少的是中式的戏谚和通顺的短文;多的是理性的逻辑和大段的引证,少的是切身的感想和感性的灵光。他们的大块文章与当今的许多戏曲一样,缺少活泼泼的情感,概为冷冰冰的“非遗”。
当然,这绝不是他们的错。一代自有一代的文艺,京剧的黄金时代算是足够辉煌和长久的了。想来京剧命为“国粹”、戏曲定作“非遗”都是百多年、几十年前的事,现在的年轻人只能在老一辈的话中和笔底,约略地感觉它们当时的光芒和炙热。想来我也和他们一样,未曾被戏曲的盛况所震撼,未曾被名角的风采所折服,故无法将亲历的感性、热衷的知性与写作的理性,一并形成“三位一体”。想来我也和他们一样,从事的是过去的一套,诸如戏曲、曲艺、书法或国画;喜爱的则是当下的一套,诸如电影大片、电视神剧、玄幻小说或电脑艺术。但包括我在内,又有几个人希望自己能像顾老对于京剧那样,亲历着、热衷着并写作着?
我对戏曲、对京剧,只欣赏而不惋惜、只感慨而不抱怨、只阅读而不批评。眼光放远一看,唐诗、宋词、元曲,现在没人亲历过,也是鲜有热衷者,人们不一样在欣赏、仿效、讲演、研究和写作着吗?固然,站在历史的高处,可得出更宏观、更科学的判断;不过处于当时的现实,却拥有最真切的感觉、最当得的权利,最是应该珍惜并自觉记录的,正如顾老所言:“我当时所见的,不乏杰出演员,许多轰动表演,至今无法忘怀。因此,我总觉得有一种责任,驱动我把当年的盛景记录下来,不致使其如烟而湮灭。”
听了此言,我不禁再发感慨。一门艺术要达它的鼎盛,创造端固然最为重要,审美端同样极其关键,即须有大量集亲历者、热衷者与写作者为一体的受众。眼光放远一看,唐诗、宋词、元曲及明清小说莫不如此,昆曲、京戏以及各类地方戏也曾如此。由此可见当下戏曲之微、京剧之弱,与“三位一体”如顾老者的由多渐少,后继乏人直至最后无人,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京剧是中国戏曲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块里程碑,从表演技艺到审美趣味,从演出市场到社会文化,皆胜此谓。京剧从诞生、成熟到繁荣、鼎盛,其百八十年来的成就绝不仅是这一个剧种的事,而是近现代中国戏曲及几乎全部剧种的事。首先,京剧从徽剧、汉调、秦腔、昆曲、京调等多种戏曲和曲艺综合而来,在剧目、行当、化妆、音乐唱腔上均既有创新之功,更生出蓝之色,是公认的集大成者。其次,京剧对上述剧种、曲种以“角儿”为中心的审美模式,先予以了巩固,后发挥到极致,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流派唱腔、鲜明的演艺风格。在“同光十三绝”“前三鼎甲”“后三鼎甲”“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的创造下,京剧这一“以角儿为中心”的“花部”代表,扬弃并替代了“以本儿为中心”的“雅部”的审美范式,一举改变了两百年重案头剧本、轻舞台表演的文人戏历史,开启了两百年重唱做技艺、轻文本写作的民间戏格局。正因如此,顾老将此书定名为《角儿睹记》,既出于自己主观的体验,合乎这段客观的历史,也符合学理的定论。于是读者从中读到他所认识的金少山杨宝森,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周信芳,读到他“四见李少春”,观赏“唐韵笙和童芷苓”,读到他熟悉并了解的海派名家粉菊花、白玉艳……一以贯之,都是如此。也因如此,顾老对戏曲演员前世今生的命运、古往今来的前途,也有不少阐述评论,其中也不乏细致的分析、独到的见地。
京剧南下不久,南派京剧尤其是海派京剧诞生,重塑了演剧理念、丰富了创演模式、吸收了外来文化、拓展了市场规模,使京剧成了近代城市市民文化娱乐品类。从此,皮黄一脉分为京海两派,京派使京剧从宫廷走向民间,成为中国戏曲的主流;海派使京剧从古典迈进近代,成为汇古今、通中西的综合艺术。若在当时放眼全国,我可以百分百地确定“三位一体”的京剧受众为数最多,覆盖最广。顾老是上海人,既见京派艺人众多,又受海派影响最大,曾从自己的观剧经验出发,对京海两派作出了生动简洁的分析,一看这篇文字,便知不是出自学者,而是资深戏迷之手,易懂而又会心,亲切又感人。
如前所述,京剧集各路“花部”于一身,一方面是许多京剧名角兼跨多个剧种、兼胜多门行当,其表演理念及风格影响了各路地方戏;一方面是各地戏曲艺人主动吸收京剧的扮相、程式、唱腔,为己所用。对此顾老也有广泛涉猎,比如淮剧、锡剧、甬剧、越剧、沪剧、滑稽戏等。他曾谦逊地说,自己对地方戏问津甚少,印象不深,记忆肤浅,比如越剧只看过袁雪芬、范瑞娟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徐玉兰、王文娟的《春香传》;淮剧只看过筱文艳、何叫天的《秦香莲》;甬剧只看过徐凤仙、贺显民的《半把剪刀》;滑稽戏只看过“程刘俞”的《活菩萨》、“杨张笑沈”的《七十二家房客》、文彬彬范哈哈的《三毛学生意》、“姚周”及“双字辈”的《认钱勿认人》《满园春色》……轻描淡写之中,名剧名角灿若星斗,他们皆为“以角儿为中心”的代表、各剧种的宗师级人物。另外,顾老也曾观赏许多话剧,并认为一部上乘的话剧,需要两个条件,即“好的剧本和出色的演员相组合”才能成功。显然这种审美观念是从戏曲而来的,直指几十年来话剧重剧本、重导演而轻基功、轻表演的弊病。
二十四年前,顾老突患风疾。尽管身体行动不得,出言口齿不清,他依然在病榻上轻吟着京剧的唱段。儿孙孝顺,不仅每日悉心照料,更是陪伴顾老共吟,助其兴致,养其精力,不久奇迹发生,顾老居然彻底痊愈。可见对他而言,京剧不仅是灵魂精神的支柱,而且是身体细胞的活性。这支柱、这活性,不仅助他恢复了生活的质量,而且令他产生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举家学京剧。于是祖孙七人,七大流派,组建了唱念做打俱全的“顾氏票房”,上海登天蟾,北京上央视,声动票房界,名传梨园行。顾老更以他的渊博和热情,结交了不少当今的梨园名家,也常为他们作颇中肯綮的评价文字。如今儿孙已大,戏艺愈显成熟;顾老虽老,精神依旧健旺,此乃京剧之赐予、戏曲之福音,诚如顾老所言:“夕阳西斜近黄昏,老朽垂暮更精神。”
作者:胡晓军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