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
译者从来就是隐形的存在。一个好的译者,固然有被读者记取的可能,却并不会将“名垂译史”当作自己唯一的追求。他们以沉默之姿,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维系着语言—思想这一多样的,坚韧的,不可或缺的存在。
我们在华东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推出“丽娃河畔的翻译家们”的栏目,绘制一幅群像,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从华东师范大学走出的这些低调、简朴、从未失却初心而又不乏个性的翻译家。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在记取中更好地前行。

郭大力和夫人

孙大雨

戈宝权
我对周煦良的兴趣,好像是从他译的毛姆开始的。《刀锋》里频繁出现的“晃膀子”倒是并未引起我的不适,因为我多少有些向往那个时代的现代汉语译者,没有太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很自然地就用非常生活的语言,让发端时期的文学翻译将同样在发端时期的现代汉语生动地保留了下来。真的令我回味的,是他在译本序言中很淡然地说:“小说不是历史,不需要反映一个时代的全貌,但它反映的那一部分,特别是其中的人物,必须给人以真实感,不能只是影子。”——看到这句话,我突然有点理解他对毛姆的选择了。这种调性,是毛姆的,也是周煦良的。只是看周煦良的人生轨迹,用卞之琳在他去世之后的回忆文章的话来说:“基本是书生,却有活动能耐,一贯以行动支持社会、国家进步、正义大业”,比毛姆的行动能力怕是要强很多。但反过来说,从周煦良现在已经淡去的声名,可见得他在自我价值的问题上,与毛姆的通透有的一拼。
的确,在华东师大那么多年,我很少听人谈论周煦良。对我而言相隔甚远的他最初只是一个名字,被镌刻在新校区的大师榜上。但是进入了他的文字,我倒是慢慢地觉出他的亲切来。他不像同在上海的傅雷,在文学翻译的历史上是那样耀眼的存在。他甚至在文学的趣味之外,还会去译《神秘的宇宙》这样的天体物理学的著作。这位“民主党派的高层人物”(同样是卞之琳语)在做完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的第一届系主任之后不久,就进入政协任职。想来,能够有幸听到过他的课的人应该是不多了吧,至少在身边可接触到的范围内是不多了的。
可传承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一旦一个名字在某种意义上闯入记忆,就会不经意间一次又一次遇见。就连前阵子猛读李健吾时也遇见了:韩石山的《李健吾传》提到抗战胜利之后活跃的上海文协,成立大会后紧接着就餐娱乐,活泼泼的一群人用方言热闹闹地读诗,说“周煦良用四川话和北京话尝试着背诵自己的诗篇”。我又顿时觉得很有兴味。周煦良是诗人,家学渊源的原故,对旧体诗很有心得,但在对新文化的坚定信仰中又拒绝写旧体诗,只坚持用译诗的方式找寻新诗的可能性。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文学信仰,而中国的新诗,或者说新文艺,也是大量的周煦良们努力的结果。如此说来,翻译应该也是周煦良诸多行动之一。
是啊,谁没有过自己的好时光呢?有理想的,充满活力的时候。哪怕世事不一定遂了人愿。这才想起周煦良终究是那一代的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的专家:卞之琳、李健吾,还有傅雷的那一代。但是为什么翻译史又好像忘记了他的存在呢?乃至即便是博学而志趣广泛的前辈陆建德,有次也专门问我周煦良是不是“在华东师范大学任过教”。于是我开始挖掘“家谱”,却意外地在“家谱”上又发现了很多名字,仅仅举我最熟悉的法语文学,就有《红与黑》的第一个全译本的译者、女翻译家罗玉君,还有专译莫泊桑的李青崖。

周煦良
不用等到“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的成立,这册“家谱”就翻开了第一页。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已然涌现出了一代要通过翻译找寻救国之道的前辈,这总与大夏或者光华坚守“光大华夏”和“日月光华”的信仰却并不一味排斥他者文化的理念相关。否则,又怎么解释当时在大夏读经济系的戈宝权最后却以翻译立世,将高尔基“在乌云和大海之间”,“像黑色的闪电”一般“高傲地飞翔”的海燕送入一代人的诵读记忆;又怎么解释罗玉君从大夏毕业之后,成为第一批留法的女博士,回国来毫不犹豫地将根落在华东师范大学,默默只是尽一个译者,一个外国文学研究者的最朴素的义务呢?就连周煦良,也是放弃了光华大学化学专业,转到爱丁堡去读的文学硕士,横跨了文理。这一代人当中最小的,是今天仍然健在的任溶溶,译了一辈子童话,写了一辈子童话,任世事变化,兀自童心不变。
甚至不仅仅是文学。《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之一郭大力出自大夏大学,也是从化学转攻哲学与经济学;为毛主席和斯诺做过翻译的吴亮平,《反杜林论》首个全译本的译者当年也是从大夏投奔革命;任教于华东师大的著名数学家程其襄在用一本自己主编的《数学分析》奠定了中国高师系统的数学分析理论之前,却也没有忘记将《马克思数学手稿》或是《几何基础》这样的德国数学基础著作翻译过来。
但是散落在漫长而广阔的中国翻译历史里,很难让人发现这些分别看上去并不很起眼的事实之间的关联。便是我这样真正意义上与他们有学缘关系的后辈,也很难将自己与他们联系起来。二三十年前做《红与黑》的翻译研究,罗玉君的名字和文字在我眼前出现了无数次,但简单简历中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除了带给我一点点疑惑——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老师说起过?——就也在研究中过去了。在这一点上,我远远没有陈丹燕有良心。在一篇文章里,她动情地写道:“我坐在大教室的第二排,看得到王智量老师在说到普希金的长诗,和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在大雪中,跟着流放的丈夫前往西伯利亚时,眼睛里闪烁的泪光。”
如果不是良心的事情,我为自己找的理由是:比较起翻译的历史,翻译的地理总是更为模糊,更难确定边界。翻译家是文化的旅者,翻译这回事情更是跨越边界的活动。在翻译的地理上,我们一向采纳的是更加宏阔的,语言的边界。因而我总是最先想到把自己“厚颜无耻”地添在傅雷—李健吾这条用法语文学串起来的传承之线上,却很少会想到我和并未谋面的戈宝权、周煦良、罗玉君,或是再晚一些的叶治(主万)、孙大雨、虞苏美等老师之间的关系,尽管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是他们翻译的普希金、毛姆、司汤达以及纳博科夫、莎士比亚给了我最初的外国文学教育。他们的译本,也和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或者李健吾译的《包法利夫人》一样,比任何一本外国文学史都要来的生动和真切,被抹去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进入同一个汉语构成的文学共和国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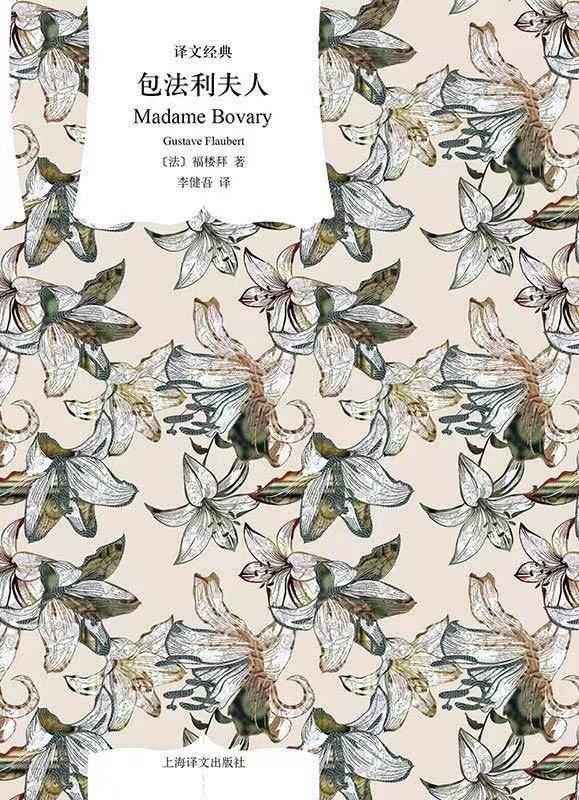
所以,同样未曾谋面,我和傅雷或李健吾之间的连接真的要比和他们之间的连接更加紧密吗?我突然之间有些拿不准了。当模模糊糊地想着,“晃膀子”也曾经是自己年轻时候的理想——甚至也像拉里那样,告别了熟悉的,看上去更应该符合自己身份的生活——当读到“除了保留在最最黑暗的过去中的一小片温暖,在记忆的岩穴和幽谷中,她什么也不存在了”这样的字句,总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狠狠地啄了一下,觉得用自己一辈子的文字去换来别人的这一段文字也是心甘情愿,我还是说服了自己,我的的确确,从气质和命运而言,是注定要在丽娃河这一翻译地理的囿定下,去继承这段翻译的历史的。这种奇妙的命定,也可以解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华东师范大学既接纳了热情执着的王智量,也接纳了恃才傲物、“人见人不爱”的孙大雨,接纳了并无教学与研究经验的叶治——在翻译的王国里,他更以“主万”的笔名立世。然后,再过二十余年,他们也接纳了用五年的时间在外面“晃膀子”的我。
以融入时代的方式在各个领域寻找还未曾显现的可能性,我想,这应该就是丽娃河畔的翻译家赋予自己的使命吧。噢,不,“使命”这个词也许在他们看起来也稍微大了一点,他们的所有野心或许就只是成为“一小片温暖”,个人的,或是集体的;文学的,或是科学的。即便这样的“一小片”成了不足以道的微光,但这又何妨?因为文字是真实的,而不是影子。
作者:袁筱一(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教授)
编辑:周敏娴
责任编辑:宣晶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