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写完池莉散文新著《从容穿过喧嚣》的读后感,又集中读到孙甘露的《时光硬币的两面》、梁鸿鹰的《岁月的颗粒》和赵丽兰的《月间事》这三本新近出版的散文新著。于我个人而言这虽只是一种巧合,但在一个时段内得以如此集中地阅读散文的确也不多见。或正因为如此,这次集中阅读给我留下的某些局部印象反倒十分强烈。
上述三位作家文学创作的主打方向都不是散文,散文写作似乎只是他们在自己主打之余的一种调剂;尽管如此,倒是一点也没妨碍他们在散文创作时所流露出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个性,其散文作品既明显不同于专业散文作家的创作,又不时“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若干自己主打专项的某种特色。比如池莉与孙甘露平时主打的都是小说,但各自小说创作的画风则差异甚大,这些差异在他们的散文创作上也同样表现出来;梁鸿鹰长期主打文学理论批评,这部散文新作的总体特色虽近乎个人亲情与成长历程的“自叙传”,但这种“自叙”又不时“止乎于礼(理)”;赵丽兰我基本不了解,搜索了一下,她在进入创作散文之前似乎更多地是从事诗创作,且又生活在云南澄江这个地域特色十分独特的地方,因此她的散文创作出现了一种不太同于一般散文创作的“灵异”感。如果本人上述这种局部的阅读印象大抵不谬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这几位作家的跨文体写作,那只跨出去的足迹又多少总会带着另一只主打脚的印记,这对他们所跨入文体的创作显然又是一种丰富与拓展。关于池莉的散文创作本人已有专文评述,这里不妨再看看孙甘露、梁鸿鹰、赵丽兰三位在进入散文创作时这界究竟“跨”得如何?
1
《时光硬币的两面》收入了孙甘露不同时期创作的散文代表作。作者自己坦言:“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是为报纸和杂志写的,因为受篇幅的限制,都比较短小,更多是当时的一些日常生活记录,或者是阅读、观影札记,还有因个人经历上的触动而写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如果标上日期的话,我觉得可以复原整个年轻时代的岁月和生活,以及一些思考”。的确如此,或许是为了迁就三辑小标题所囊括的内容归类,作者有意识地隐去了写作的时间,但全书卒读下来,我脑子里闪现出的还真就是作者近三十余年的生活与思想碎片,虽琐屑,却闪烁着微光与智性,时而亦显露出昔日先锋之锋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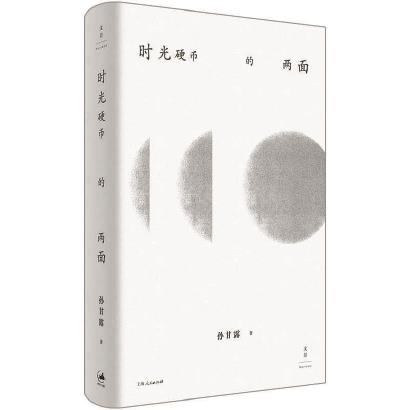
1986年伴随着《访问梦境》的面世,随后又有《我是少年酒坛子》和《信使之函》等的跟进,一举奠定了孙甘露作为当时所谓“先锋文学”骨干之一的定位。而那时所谓“先锋”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其创作明显有别于传统文学叙事的一些基本规则而充满了各自的“实验性”。具体到甘露而言,作品中那些随意而破碎的想象依照作家自身的情感和体验、以及对时间永恒性与存在瞬间性的哲学思考等元素,大多以一种看似无序的叙述而展开,这一切对习惯了传统阅读的读者而言无疑都形成了一种高度陌生化的效果。这样一些“实验”的渊源或初衷在这本《时光硬币的两面》中同样不经意地得以自然呈现与流露。甘露对这本散文集的命名本身就很有意味,所谓“硬币”当然是一个整体,而“两面”则是这个整体中某些相对独立甚至相左的元素。尽管时间在流动,但“硬币”这个整体又总是将“两面”之间精神的牵连或流动联结成一体。
具体到《时光硬币的两面》中,上述那种“渊源或初衷”“牵连或流动”主要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集中体现在作品第二辑“我所失去的时代”中,那些言语虽简洁却是直陈己见,作家在对上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回眸中就蕴含着诸如“作家所说的关于小说的话大多是不可信的,当然不比批评家更不可信。如果真的关心小说,还是去读具体的作品,在那里面,作家丢人现眼的地方有的是”之类对文学、艺术和创作的思考;二是无论在哪一辑中,乔伊斯、杜拉斯、兰波、齐泽克、尤奈斯库、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索尔·贝娄、博尔赫斯、罗兰·巴特、普鲁克斯、奈保尔、卡尔维诺等作家以及《生活在别处》《死者》《第二性》《椅子》《百年孤独》《追忆逝去的时光》《交叉小径的花园》《驳圣伯夫》《赫索格》《S/Z》《米沃什辞典》《看不见的城市》等作品是甘露笔下出现的常客。如果说前者是作者那个时代从事“先锋文学”实践的一些理性思考,那么后者则可从中窥视出当年“先锋文学”的某些渊源,未必那么直接,但瓜葛犹存应该是无疑的。
综观《时光硬币的两面》,既有碎片式的日常生活,又有片断的智性思考,还不乏上海实景,这样一种由点到面、由抽象到具象的轨迹与作者的小说写作大抵也能找寻到重叠的斑痕。在时光流转之中,一个文学的时代、一个现实的社会被甘露精到的简洁文字流下了一幅幅剪影。
2
收在《岁月的颗粒》中的部分篇什我以前在《上海文学》和《十月》等文学期刊上曾零星地拜读过,当时即感觉这些作品近乎记录作者跨入工作岗位前生活与成长的一种“自述”,此番得以集中阅读,这种感觉就更为强烈与清晰。尽管作者在不同的单篇中也尝试着变换叙述者的人称,但无论是第二人称的“你”或是第三人称的“他”,都依然无从抹去“自述传”这一特征的基本痕迹。

鸿鹰将自己的首部散文集命名为《岁月的颗粒》是恰如其分和名副其实的。18则散文尽管长短各异、叙述主体不同、客体也有变,但无疑皆为“颗粒”,而将这18个“颗粒”拼接起来则串成了一段岁月,虽童蒙、虽青葱,但那也是“岁月”。于是在塞外的那个小镇上,家庭往事、幼时经历、青春记忆、小镇风情、塞外尘埃……统统在作者的记忆中被激活,栩栩如生地得到一一呈现。
这部散文集中给我留下比较强烈印记的当是作者那些对自己过往情感追忆与思念的文字,包括亲情、爱情、同窗情和乡情等等。对哺育过自己的奶妈、慈爱的姥姥、质朴的舅舅,特别是有关常年卧病并在自己12岁时就不幸离世的妈妈以及父母间……这些与作者关系紧密的至爱亲情,鸿鹰倾注的笔墨十分饱满;此外,对自己情窦初开时的青葱爱情以及懵懂时的男女之悦也并不回避。这类文字在我看来恰是这部散文中最有特色也最为出彩者。依常理,面对至爱血亲的或生离死别或生死相依,面对“两小无猜”的那种纯真与眷念,作者用情浓一点都很正常,也谈不上所谓“过头”。但鸿鹰的处理却别有一番特色:过往的那些哀乐生死,在舒缓的回忆中透出的那份敏感虽纤细,但温度却并不及想象的那般浓烈,淡淡中别有一番特色与味道。比如,失去妈妈后面对父亲,自己与他的关系却从来都不那么亲密,年少时还一直想摆脱,直到父亲离世自己也做了父亲后,才发现自己竟然越来越像父亲,这到底是因其血缘与基因的强大还是冥冥中一种情感的牵系?比如,在80年代大学校园中的那段爱情,从无到有、辗转曲折、若即若离,在断断续续的情感碰撞中呈现出情与“礼(理)”的碰撞。所有这一切,从表面上看皆可归于“发乎情而止乎礼”,而骨子里这“礼”当更是来之于“理”,这样一种融敏感、纤细、节制于一体的艺术处理,其背后的总控莫不来自鸿鹰自身的理性把握。
当然,在《岁月的颗粒》中,呈现出的并非只限于“发乎情而止乎礼”这单一的理性特色,另外,还有诸如“我”“我们的主人公”“你”“他”这样叙述人称的变化、视角的不同以及时间的错位,有自然、空气、风雨、光影、味道、声音等自然元素的交错,有对话、书信、闪回、情感和思绪的叠加,这些看似碎片般“颗粒”的叠加使得主人公那段曾经的“岁月”浑然一体地鲜活灵动起来。
3
最后再来说说赵丽兰和她的《月间事》。这应该是一位文坛还比较陌生的作家,我也是在不经意间翻阅她的散文集《月间事》时,一下子就为其作品中不时呈现出的那种灵异、冷艳、亦真亦幻、似人似仙……总之是一种我一时说不太明白的特别风格所吸引,也曾试图借助万能的“度娘”来搜一下她的基本情况,结果依然是知之甚少。
或许对我们间接理解作者散文创作特色略有参考价值的辅助信息就是赵丽兰来自云南省的澄江县(现似已改县为市)的阳宗村,这是一块位于抚仙湖与阳宗海之间的土地,一方汉、傣、景颇、阿昌、傈僳和德昂等多民族的栖息地,一个有着儺戏传统的村庄;而对理解《月间事》更直接的信息则是赵丽兰为自己这本散文集“写在后面的话”中的几句夫子自道:“我对散文,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亦有一种与之对抗的叛逆性。”而这种“叛逆”则集中表现在作者“尝试着将虚构与非虚构进行融合转换”,“因而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在‘真实’和‘谎言’之间,有了一个美好的存在。这样,既表达了真实的自我,同时,又因了错位的构置,成了另外一个东西。那个新的东西,无法具体,但又确实让人感到淋漓尽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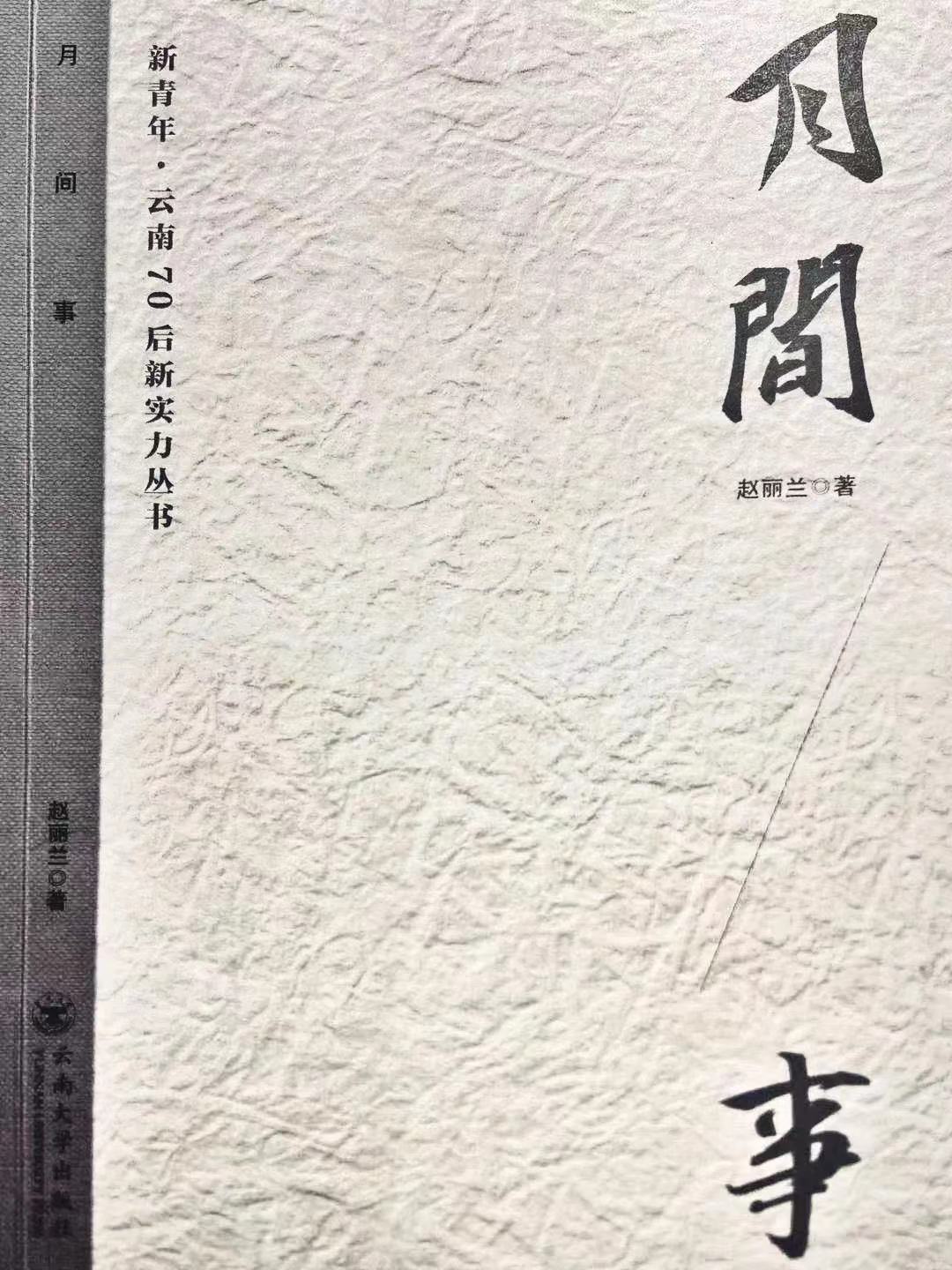
正是因为作者生长于这片神奇的土地以及她对散文创作的上述理解,因而在她笔下的散文创作就出现了以往我们阅读这类文体时所罕见的陌生化效果。以“月光”这个意象为例,我国众多过往的文人骚客笔下多用其托相思寄乡愁;赵丽兰对月光独有情钟,不仅用“月”作为书名的关键词,而且诸多篇什都围绕着“月”来布局谋篇,但她笔下的月光显然更加立体,月不再只是作为某种情思的寄托,而是将其拓展为一种视角、一种眼光,注视和见证生命中的种种呈现,那些由“我”的老祖、姑奶、奶奶、母亲讲述的故事,大多发生在月光下;至于“我”的故事则更是离不开月光。《有人在月光下洗身子》《安放在月光里的床》《知羞草》等篇什就是表现了月光见证“我”灵魂和肉身成长的那些个时刻,那些诸如初潮、出嫁、生育等女性所独有的隐秘变化在赵丽兰的笔下都发生在月光之下。
一本《月间事》,有中国传统典籍《尔雅》《山海经》《清稗类钞》、民间戏曲《霸王别姬》《野猪林》的印记,有小说式的叙事,有诗一般的语言……这些在习见散文那里十分稀见的元素构成了一个特别的赵丽兰。当然,仅凭这一册《月间集》就来对赵丽兰下定论,或许有点草率,但这的确是我们值得关注与兴奋的一位新人和一部新作。
作者:潘凯雄(知名文艺评论家)
编辑:范昕
责任编辑:李婷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