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文的正题之所以要打上引号,是因为它就是本文评说对象第一章的标题;之所以要如此“拿来”,是因为它与本文欲评说的角度再贴切不过。冒犯了,晶明兄。
这是一部专题研究鲁迅先生散文诗《野草》的学术随笔,之所以用“随笔”相称,是因为它的确不同于许多出自学院派之手的学术专著,但又是比一般所谓“专著”更专的专题研究。
阎晶明其实也是地地道道地出自学院,其硕士研究生的攻读方向就是“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关于鲁迅研究,此前便有《鲁迅还在》《鲁迅与陈西滢》和《须仰视才见》等著述出版并编有《鲁迅演讲集》和《鲁迅箴言新编》,是地道的“鲁研”专家;同时,阎晶明又是当代文学方向的著名评论家,有《十年流变:新时期文学侧面观》《批评的策略》和《独白与对话》等著述面世。再同时,阎晶明还是从专业走向管理的专业型干部,从曾经的山西作协秘书长到现在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作以上罗列,当然不是为了显摆什么,阎晶明也不需要这样的显摆,而只是为这本《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为什么不那么“学院派”但又学术性十足埋个伏笔。
回到《箭正离弦》这部研究《野草》的专著上来。在阎晶明眼中,“《野草》是理解的畏途,长期以来,我并不敢去触碰这一话题”。既然长期不敢,现在何以就“敢”了?还是看阎晶明的夫子自道:《野草》“这包含《题辞》在内的24篇长短不一的作品集,引出不知超过它多少倍的难以计数的阐释。这些阐释的努力,透着真诚,传递着各自独特的感受。但我又觉得,从总体上,对《野草》的阐释有时觉得有过度之嫌,有时又觉得还有很多空白。也许最大的矛盾在于,《野草》是跃动的、不确定的,但研究者总在试图确定它、固化它,《野草》的呈现方式也如‘野草’,具有‘疯长’的特点,但研究者想要找出它们共同的规律和特点,使其秩序化,使之成为散文诗这一新文体的范式甚至‘标准’”……正是因为目睹《野草》研究的这种现状,阎晶明才“希望《野草》研究能从‘诗与哲学’的强调中回到本事上来,关注和研究鲁迅创作《野草》的现实背景,特别是分析和研究《野草》诸篇中留存的本事痕迹即现实主义成分”。这样,当“有助于调整《野草》就是‘诗与哲学’的固化认识,避免研究上的重复和空转,以及阐释上的过度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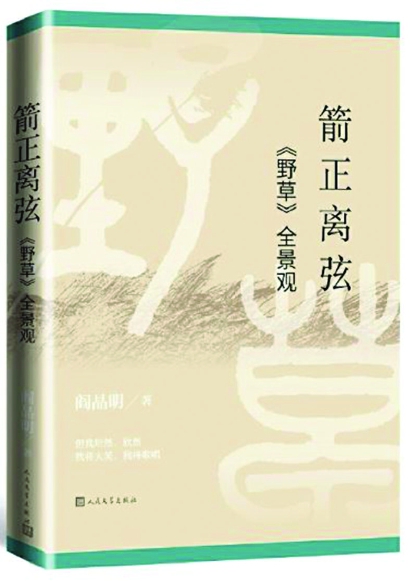
在我看来,阎晶明的这种认识与判断,既很准确也需要勇气。从整个鲁迅研究看,它显然已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鲁学”,正如同《红楼梦》研究被称为“红学”、《金瓶梅》研究被称为“金学”一样。一旦被称之为“学”了既说明研究对象之重也意味着从事研究者之众。从理论上讲,这自然不是什么坏事,毕竟不是什么研究都能够被誉之为“学”的。然而,现实毕竟又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一旦称“学”就极易出现“过度阐释”与“随意拔高”“任意延展”的偏向,特别是将一些未必属于研究本体的所谓“研究”也纳入所谓“学”之中,在所谓“红学”“金学”和“鲁学”中,这些个现象并不鲜见,大家只不过出于各种利益与关系的考虑,并不愿说破而已。而从《野草》研究的现状看,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倾向,鲁迅先生这部体量并不大的散文诗因其文体的创新及先生曾有“我一生的哲学都在《野草》里”这样的自白,因而时常被认为是鲁迅先生“最私密化”的作品,是“一座诡异的房子”,而所谓“诗与哲学”的过度阐释亦由此而来。
正是基于这样的大背景,阎晶明的《野草》研究才格外强调“本事”二字,也可以说,“本事”二字就是《箭正离弦》的“书眼”之所在。
“本事”者,就是真切的事实或事实的真实性。《汉书·艺文志》中即有“(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之言。在《箭正离弦》中,阎晶明从三个维度解析了《野草》的“本事”,即第一章“抖落思想的尘埃”,从北京的风景与环境、故乡绍兴的童年记忆、现实世相与人物“原型”、日常生活中有记载的实物以及中外文史典籍的引用或提及等“本事”元素来考察《野草》的成因;第二章,阎晶明并不回避“诗与哲学”这样的话题,但他只是以此切入进一步深入探讨鲁迅先生对“本事”的改造、升华和艺术创造;第三章则是从《野草》的发表、出版流变的过程进一步考察其“本事”在传播过程中的逐渐“丰饶”。三个维度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在这个过程中,《野草》的“本事”渐渐浮出了水面。
经过上述这样一番梳理,《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的突出贡献及价值我以为绝不止于停留在对《野草》“本事”的梳理与还原,更突出地表现为如下两点:
一是对学术研究中基本方法论的重申与实践,即从“本事”出发、立足“本事”、回到“本事”。依常理,就学术研究而言,这本不是一个问题,但我们学术研究的不少现实表现为它偏偏就成了一个不小的问题,离开研究对象本身,或者只是以研究对象为媒,自说自话地炫耀自己的所谓理论与研究新发现,至于这种所谓“新发现”与研究对象是否有关反倒不那么重要了。这样一种离开“本事”的学术研究无论貌似多么深刻、多么新鲜,其实都是毫无真正的学术价值可言,相反倒是很容易将研究导入歧途。
二是对回到“本事”后求实学风的张扬与践行。《箭正离弦》虽然没有如一般学院派专著那样建筑起宏大体系,但其中求实、求真、求证的严谨则是许多貌似体系化的学术专著所无从比拟的。单看全书最后的两个“附录”当可见出阎晶明为写作这部仅23万字的专著所付出的心血。“附录一”是“鲁迅关于《野草》的自述辑录”,包括鲁迅先生从1924年到1933年整整十年间的日记与文章中有关《野草》的自述;“附录二”则是“主要参考书目”,包括国内外有关《野草》的相关版本及研究论著38种,还有那些众多未列出细目的相关论文及文史资料。这些都是学术研究的死功夫,来不了半点投机耍滑。倘没有这样的死功夫,阎晶明笔下的“本事”其“信”也会大打折扣。
在本文的结束之际,有必要呼应一下前面埋下的那个伏笔。在我看来,阎晶明的这部《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虽无一般学院派的体系建构,但又的确做出了扎扎实实的学术贡献,这得益于他一是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并深谙学术研究之真谛;二是有着从地方到北京、从专业研究到走向以管理为主的从业经历;三是研究领域横跨现、当二代。将这样一些外在因素与本书所取得的成就扯在一起看似有些牵强,其实不然。这样的学术历程对阎晶明的治学之道不可能没有任何影响,这样的个人经历客观上也使得他自觉不自觉地少了点学术研究中的那些潜规则或无形羁绊。于是,就有了这支学术之箭,它不是引而不发而是正在离弦。
作者:潘凯雄(知名文艺评论家)
编辑:郭超豪
责任编辑:卫中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