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醉(1914—1996),原国民党陆军中将,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28岁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著称。1949年12月被卢汉扣押,参加云南起义,时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1960年被人民民政府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1980年,由战犯身份改为起义将领,后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在他写的《沈醉回忆录》中,收录了很多揭露军统内幕的文章,也间接地记录了许多没有留下名字的革命先烈事迹,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军统特务们绑架的方法越搞越阴险毒辣
抗战前军统在上海租界内比暗杀搞得更多的是绑票,当时美其名曰“秘密逮捕”,实际上是实行政治绑架。除了以共产党员为主要对象之外,对许多民主人士与反蒋集团分子都是采用这种办法绑到南京或秘密予以杀害。当时担任这种罪恶工作的,最初还是以赵理君率领的行动组来执行。1935年以后,我兼任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公职后,大部分绑架工作便由我担任了。特务们开始是采用上海绑匪的一套硬绑的方法,由几个特务以手枪威胁着将人强拉上汽车。这种办法时常遭到意外麻烦,最难处理的便是被硬拉到汽车旁边后,被绑的人总是昂着头尽力挣扎不肯上车,虽然一边一个特务挟持着并且用手枪抵着腰部,仍不易推进车门。戴笠常骂我们蠢猪笨蛋,不会多想办法。我便和我当时率领的组员苏振通、朱又新、王开明、陈邦国等十来个人经常研究,改进绑票的方法。我们有公开的职务身份,有在英法两租界携带手枪的证件,整天可以将手枪带在身边进出租界,万一失手,便可改绑票成公开逮捕。
当我们最初研究出一套强拉上车的办法后,戴笠非常称赞。其实这种办法很简单,当把绑到的人(肉票)拉到汽车旁边时,先有一人在车内将车门打开,挟持的特务,一人用手枪抵住“肉票”的腰背,一人以拳猛击他的小腹,这时被击的人自然会将腰一弯,正好是一个上车姿势。紧接着另一特务用手压住他的上身不使再昂头,车里的特务再一拉,这样就能够很快将“肉票”推入汽车。这往往是紧要关头千钧一发的时刻,分秒都得争取,因此我们得空便加强练习。后来,我们这一套手法锻炼得很熟练准确,即令被绑对象狂呼大叫,我们也只要几分钟就能将他绑上汽车。附近的巡捕发觉后,往往连警笛都没有来得及吹响,我们便已一溜烟开车跑了。
戴笠看到我们肯钻研,鼓励我们进一步研究“软”的办法,要能在热闹大马路上稠人广众之中去进行绑票,不应当局限于偏僻地区。在金钱和精神两方面不断鼓励之下,特务们又渐渐找出了许多新的窍门。我们经常采用而行之有效的方法又增加了好几种。例如,我们事先侦察好要绑架的对象经常经过的路线,便将汽车开去停在附近,当对象走到离汽车不远的地方,由一个特务从背后用两手蒙住他的眼睛,并以大拇指用力掐在两耳根下命门部位,使之无法挣脱,另一特务则紧握对象两手,两个特务同时狂笑说:“这一下你猜不到是谁了!”过路的人以为是在开玩笑,被绑的人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已被连拉带推绑进汽车,纵然发觉想叫喊也来不及了。
有时甚至不用汽车,临时雇人力车也能把人绑了回来。那是先准备一条一头装有铁砂等物的橡皮管,由一个特务从对象背后猛击头部一下,便立刻飞逃。当这个对象被击昏倒地后,另一特务便装作这人的亲友,一面扶住一面大叫抓凶手,一面假充好人叫人力车(或在附近租汽车),伪装送往医院急救,等抱上汽车或人力车后再在途中改变地点伪称先送回家,这样就很顺利地把人绑回来了。有次用这个方法绑一个画家,正遇到他的学生,特务们便马上要他去通知他家里的人到广慈医院去。这个学生当然愿意,于是便被轻易地支开了。
由于特务整天在打坏主意搞这类罪恶勾当,方法也越来越多。有次我带了两个人去侦察桂系派在上海活动的特务头子陈六安,准备绑架他,正巧遇到他从家中走出来,提着一个大皮包向一家出租汽车行走过去。我们立刻采用紧急办法进行绑架。我们当时都穿着便服。我叫两个助手等在路上,我自己很快跑到车行叫车,车行以为我是陈家的佣人;同时我又帮助司机将车打扫一下,陈又以为我是车行助手。陈走过来雇车时,我忙将车门打开请他上车,自己坐到司机旁边。车刚开出,我叫司机停一下,两个助手一边一个窜了上来,在三支手枪威逼下,便将他绑到了侦察大队。司机一看是军事机关,在多给他几块钱后,他也吓得不敢说出去。当然在利用别人汽车进行绑架时,也有失败的时候。如在英租界三马路扬子饭店绑刘芦隐先生,因他的夫人发觉了大叫起来,刘先生也很机警地从后面一个筋斗栽到前面,占住司机座位不让特务开走。这时巡捕赶来,我们便只好由绑票改成公开逮捕了。
到了1937年初,特务们绑架的方法也越搞越阴险毒辣了。我们训练了两个女特务来协助进行。这一办法便可不受地区限制,什么热闹马路上都可进行。这是利用旧社会那种乱搞男女关系的风气作为罪恶行动的掩护,特别对一些穿着很考究,排场阔气,用其他方法不容易达到目的的人最有效。这种方法,除了不能在绑架对象的住所使用外,其他的地方都能实行。女特务伪装成绑架对象的姘妇,一见面便把对象扭住又哭又吵要拉他回去,当对象受到此一突然纠缠时,最初决不会马上叫喊是绑票,多先作解释,认为她看错了人。她便更大哭大吵起来,一面骂着没有良心,丢了她不管又去找别人等一类的话,同时用力扭住他上车,另一个女特务也从旁相劝叫他同回去一趟。这时看热闹的人当中又闪出一两个男特务来,一开口便说:“怎么?你们又吵起来!你们在街上吵太不雅观,还是大家回去好好商量一下吧!”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先把这一问题肯定成为秘密的男女关系争吵问题,使看热闹的人不会识破是一幕绑票案。在几分钟内,这群特务便连拉带拖将肉票推上汽车,被绑的人弄得有口难辩。只要一上了车,什么都解决了。特务们用这一办法先后在英法租界最热闹的地区绑过三个人,都没有遇到困难,到抗战开始才没有再做。
当时除了在租界上经常进行绑票外,在反动政府统治地区也常进行这类活动,不过一般都限于对工厂中进步工人与大学校的进步学生。因为到工厂里公开逮捕人往往遭到工人的阻拦,有时甚至发生殴斗,结果人抓不到,反而走漏风声,一些关系马上转移了,以后不能再进行连续逮捕。所以总是用秘密的绑架方式进行逮捕后,马上执行刑讯。这种密捕(即绑架),多半先暗中与厂方领导人或黄色工会负责人取得联系,由他们提供照片和关系,了解对象常出入什么地方,有时甚至是在夜班时,厂方或工会故意借故指派被绑者外出,暗中协助特务,只要对象离开工厂或工人群集的地方便可下手。至于绑架(即密捕)大学中的进步学生,则不去和校方联系。因为学生失踪后,学生家长往往吵着向学校要人。特务们也不公开到学校逮捕,因为学生一哄而来,不易将人带走。一般采用的方法,往往是由学校中的职业学生先提供线索,或故意约其外出,让特务们得到便利。
军统特务“脱梢”后又遭遇“打狗团”成员
对于居住在华界的个别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等,一般不采用绑票方式,而于深夜去搜捕。这样,不但可以将人抓走,还可抄查证据文件。几年间,这种公开逮捕到的政治犯比用秘密绑架的还要多得多,其中最大的略举几件如下:
约在1935年间,一个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叛变,出卖了几个同志后,他还想进一步去破坏上级领导机关,整天到处去活动。结果他被地下党组织进行了纪律制裁,在法租界徐家汇孝友里附近空地上被击中两枪,因未中要害而未死。当时戴笠正在上海,知道这一情况后,即指示上海区和侦察大队,要利用这一叛徒的生命来进一步达到破坏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目的。戴笠不准送他到华界医院就医,硬叫他住在法租界西区偏僻处一家小医院里。同时叫一家小报发一个消息,说徐家汇空地上发生一次情杀案,被害者身中两枪经××医院进行抢救后已无生命危险,不日即可出院等。按照戴的估计:一方面,这个人未被杀死,会更加仇恨共产党,必然要设法报复;另一方面,地下党组织一定会派人继续制裁他。如果再去,便可发现线索扩大破坏。他调派十多个特务暗中监视,准备跟踪,还派一个混入医院充当内应。戴笠决定的办法是不当场逮捕,等再来把这个叛徒打死以后再分别跟踪。因为租界的巡捕经常在马路上“抄靶子”(对人身进行搜查),共产党员不会身带枪支在外面乱跑,必然会分途回去,只要跟住一个便不难发现这个秘密机关。
我当时也被指定带了几个特务去附近监视,过了三四天还没有一点动静。我们几人分别化装成为拉人力车的,做小生意的或骑自行车故作损坏修理的,都掩护得很好。这个住在医院里的叛徒,不知道军统准备牺牲他的生命来达到破坏党组织的阴谋,还一再写出书面请求,请求带伤出院寻找关系,一方面趁机立功,另一方面可以报仇。戴笠坚决不准,要他整天睡在床上静养。
大约在第五天或第六天下午,果然有两个人提着水果食品等进医院看这个叛徒。当时附近有两三个把风的特务在守望,见此情况,顿时紧张起来,立刻分别做好各种准备。这两个人刚进去不久,便听到两声枪响,一会儿便跑了出来分途飞奔。这时,守候在医院外面的特务们,乘自行车的、拉人力车的、步行的,都一齐出发跟踪追去。十多个特务中,有两个人因为走慢了跟不上,便乘电车回去,半路上正好遇上了其中一个,这样才没有被“脱梢”。其余的特务兜了几个圈子之后,都找不到要跟踪的人,我只好带着他们准备回去受处分。戴笠接到守在医院的特务的报告,知道那个叛徒已受到第二次惩处,被击中头部当场死去,便赶到侦察大队听取跟踪结果。他一看我带着几个人垂头丧气回去,知道没有跟上,气得跳脚大骂,并限期一定要侦察到这些人的地方,否则要严厉处分。他骂过一次还不够,过了不久又把我和几个特务再骂一次。
正当戴笠怒气冲冲地准备离开时,突然接到那两个跟上的特务来电话,说开枪的人有一个已被我们跟到了法租界福煦路一家银楼,这人从后门上去许久没有出来。戴立刻命令会同法租界巡捕马上去搜捕。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杨凤岐、组长许鹏飞和我,立即率领几乎整个大队的特务出发,会同法捕房华探长直扑这家银楼,果然在二楼抄出手枪六支、子弹几十粒和几百元现款,并逮捕到三男一女,其中的一个男的便是去医院开枪的人。当时法租界警务当局以案件发生在法租界,要先行审讯,戴笠认为只要抓到了共产党,破坏了机关和抄出了枪支,让法巡捕房审讯一下也可以,但是发现新的线索要马上告诉侦察大队。听说这几个被捕的人只承认是专门制裁共产党内叛徒的一个组织,叫“打狗团”,即专打叛徒,并不搞暗杀国民党统治集团上层分子的活动。以后这几个忠贞不屈的党员,再没有供出其他情况,最后都被引渡到南京处了死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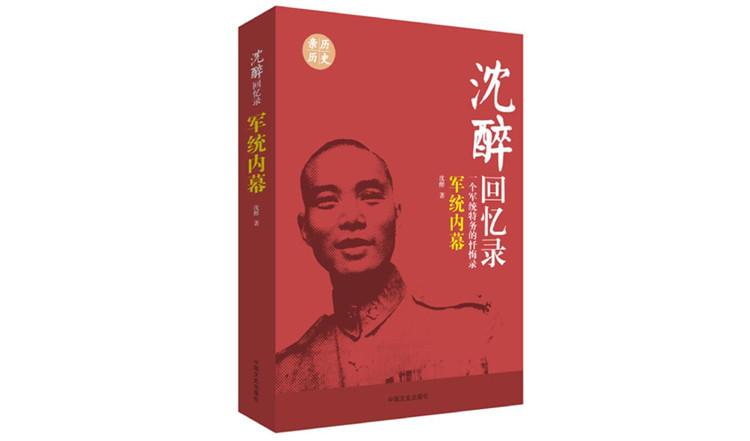
*本文摘自中国文史出版社《沈醉回忆录》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王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