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诺阿名画《游艇上的午餐》
自古以来,人类对于菜肴口味的好恶是近乎执拗的。因而,食物被认为不易在不同文化之间传递。事实却是,菜品和食材正兴致勃勃地在不同的地区之间交流,甚至出现了汉堡、炸鸡等全球化快餐食品。食物和饮食方式跨越文化,流动是如何发生的,障碍是怎样打破的?
对于食物史上这个令人好奇的问题,今年由中信出版集团引进出版的《吃:食物如何改变我们人类和全球历史》一书中,英国知名历史学者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给出了答案。原来,“吃什么”和“怎么吃”的发展史,也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写照;食物与文化的远程交流,几乎浓缩了半部世界史。
——编者

跨文化饮食的障碍在历史上由来已久,深植在个人心理当中
个人经验和逸闻趣事显示,人往往倾向于回归习惯的老味道。即使有世界各地的食物可供选择,人多半还是固守往常的菜单,一再点同款菜品。
食客嗜好熟悉口味的心态影响了整体文化。美国侦探小说家沃尔特·萨特思韦特写了一个很妙的故事,名为《化装舞会》,故事里侦探主角很讨厌吃“内脏杂肉”。有一回他为办案来到巴黎,被人哄着吃了一种法式香肠,他原本觉得挺好吃,后来却发现其实就是灌了猪肚和小肠的猪大肠。后来这种抗拒扩展到任何看似精心制作的或是在他看来含混不清的菜。高级烹饪艺术很不“美国”,厨师巧手打点装扮食物这项伟大的传统倒像是虚伪的矫饰。他渴望吃简单的烤牛排,什么酱料也没有,而蔑视罗西尼牛排上的鹅肝酱和马德拉酱汁这类奢侈品。
据18世纪晚期一位英国复古主义烹饪的推广者的说法,法式烹饪在法国还一切如常,但在英国就成了号称“伪装肉类”的花架子。“法式烹饪在这里是使好肉变坏的艺术……在法国南部……则是使坏肉变得可以下咽的艺术。”1929年,圣菲铁路公司最高级的“加州特快”线路的餐车专营商在设计菜单时发现,英语菜名的“小里脊牛肉,蘑菇”销路比法语菜名的“菲力米浓,菌类”好多了;但其实两份菜是一样的。
法国口味和盎格鲁-美利坚口味之间的历史分歧,其实只是一个普通事实的极端例子而已。这个事实是,食物和语言与宗教一样(或许程度更堪),是文化的试金石。通过食物可以形成认同,因而无可避免地带来分化。同一文化社群的成员经由食物而辨识出同伴,并通过审视菜单而查出外人。虽然饮食常有时尚流行,广告可以鼓动风潮,饮食文化却是保守的。跨文化饮食的障碍在历史上由来已久,深植在个人心理当中。个人的口味很难调整。吮食甜味母乳的婴儿除非后来断奶,转而接受新滋味和新口感,否则一辈子都会嗜甜如命。儿童坚决不肯尝试新口味。经济不宽裕的家庭尽量不做饮食试验,以免造成浪费。为人妻者恼怒地听着歌曲里的丈夫高喊:“给我一盘我老妈常做的香肠和土豆泥!”
当一种烹饪风格被贴上国家的标签后,便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僵化:必须保持它的纯净,不受外来的影响。传统菜品必然包含有关地区盛产的几种主要食物和调味料,这些材料早已渗入大众集体口味。在可以取得同样食材的不同地区,就连特定的料理方法也能变成地方性文化特征或认同象征。在地中海沿岸大部分地区,鹰嘴豆是不可或缺的产品。在地中海的一端,每逢鹰嘴豆正鲜嫩,放在舌上轻轻一顶便可压碎时,人们就会加佐料、调味料、动物油脂和血炖煮,然后趁热食用这种淡色圆球形的豆子。但在地中海的另一端或更远的海岸,人们却爱把这豆子煨烂成糊,冷了以后拌上油和一般包含柠檬在内的佐料。同一样材料在海的西岸是农民锅里少不了的食材,到了东岸则被混合起来捣烂,成为精致小菜。然而出了地中海地区,却没有人用过上述两种方法来烹调这种豆子。

赫达《有牡蛎、柠檬和银杯的静物》
烹饪的影响源头,并未超越帝国主义的范畴,这使得饮食习惯等文化产生转移
有一些力量可以渗透文化障碍,促成食物的国际化,其中之一是战争。在食物史上,“殖民流通”是比汉堡和炸鸡更早发生的现象。
烹饪的影响源头(或许应该说是文化交流的源头)都并未超越帝国主义的范畴。帝国的势力有时可以强大到对其外围地区强加母国的饮食口味,帝国也通常鼓励人口迁徙和殖民。这也使得饮食习惯和其他层面的文化产生转移。帝国饮食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帝国各个枢纽的高级饮食,它将帝国各地的食材、风格和菜肴通通汇聚于中央菜单。第二类为殖民地饮食,包括精英阶级殖民者自“母国”带来的食物等。第三类是反殖民饮食,原本的帝国臣民或受害者让帝国的人民认识了他们的食物。
在第一类中,土耳其菜是绝佳的例子。使得土耳其烹饪闻名千里、成为世界一大菜系的菜品,是首创于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的宫廷贵族世家,特别是托普卡珀宫殿里苏丹的厨房。16世纪时,厨房平时每天需供应5000人饮食,假日则需供应10000人。主厨手下有50位助理厨师,糕饼主厨有30位助手,尝膳长有100名部下。随着帝国规模渐大,菜品日益精致,烹饪影响逐渐扩张以及专业分工日益精细,上述的数字也逐渐增加。到了18世纪中叶,6样不同的甜食分别交由6个专门厨房制作,每个厨房有1位主厨和100名助手。从事厨务的总人数增加为1370名;每天有100车的薪柴送进宫里的厨房;每天到货的椰枣、李子和李子干来自埃及,蜂蜜来自罗马尼亚——专供苏丹食用的则来自克里特岛的干地亚,油来自科龙和梅东,包在牛皮里的黄油来自黑海。17世纪初,宫里每天吃掉200头幼羊和100头小绵羊或小山羊、330对野鸡,还准备了4头小牛供贫血的宦官食用。事实上,托普卡珀宫的烹饪兼具帝国和都市风味,可谓融合菜,因为它结合帝国各地的材料,烹制成新菜品。
当今的“得墨”菜(注:美式墨西哥菜)显示出殖民地的族群混合,而美国西南部菜系的心脏地带,全是美国在19世纪大扩张时代自墨西哥巧取豪夺的土地。帝国主义的黑暗力量总会转向——美国西南部的食物就重新墨西哥化了,标准的墨西哥食材逐渐成为西南乡土菜系的主要材料。辣椒是此菜系的一大标志,玉米和黑豆是其牢固的象征;酸橙赋予其风味,薄薄一层的乳酪则使其特色鲜明。辣肉酱的标准材料有肉末和水煮的整粒黑豆,煮时加了很多辣椒和孜然,其中的孜然大概是受到西班牙菜的影响,而肉末更是其招牌。辣肉酱也是得克萨斯州的州菜,在那里,最正宗的做法是不使用任何豆类的。在制作辣肉酱的过程中经常用到的辣椒粉,就像咖喱一样,不是一种单独的香料,而是混合香料。这道菜堪称最具代表性,有关它的起源则是众说纷纭,可信度不一。辣肉酱不论源起何方,显然都使用早在美国吞并西南部以前即已在当地通行的食材,自此以后,这些食材逐渐征服了征服者的胃。塔可钟连锁餐厅在全美核心地区打开大众市场,贩卖墨西哥快餐。在一部很受欢迎的科幻电影中,塔可钟还被塑造成终将接管地球。得墨菜已超越其历史边疆,这或许是因为其中掺杂了殖民母国的滋味。
菲律宾的边疆菜系则和谐地结合了原住民和殖民母国的材料。西班牙从1572年起殖民菲律宾群岛,殖民过程缓慢而痛苦。在殖民时代,华人移民确是菲律宾群岛重要的经济力量,中国风味对菲律宾菜的影响并不亚于西班牙。另外,尽管外来移民带来变化,菲律宾菜的马来根基却始终未动摇。通常会用香蕉叶调味的松软白米饭,几乎构成每一道菲律宾菜的基础,但一旁还会附上面包,沿袭了西班牙传统。有些菲律宾面包加了椰子调味,一顿菲律宾餐食往往会包含有做法不同的椰子,椰油更是普遍的烹调用油。西班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第一是厨房用语,比如虾称为gambas,芳香四溢的炖肉叫adobos。第二,有些很受喜爱的菜品是略微改良过的西班牙菜,比如海鲜饭、名为lechón的西班牙式烤乳猪,以及用小山羊肉做的番茄炖羊肉。最后一点,菲律宾菜必以甜点作为一餐的最后一道菜,而这些甜点通通源自西班牙,包括名为flan的焦糖布丁,这也是西班牙仅有的一款名闻全球的甜点,材料有蛋黄、糖和杏仁蛋糕。
帝国势力逐渐衰退时,返乡者带着多半是热带风味的胃口回到欧洲。由于厨师和餐饮业者致力迎合这些归国者的口味,并促使没有殖民经验的顾客群体也爱上这些菜,反殖民饮食就此兴起。在后殖民时代,英国、法国和荷兰分别成为把印度菜、越南菜、北非菜还有印度尼西亚菜传至全球的跳板。
荷兰菜的名声糟得叫人难过,荷兰人尤其这么以为。另一方面,荷兰人基于对荷兰菜的自谦心理,对其他文化的食物往往欣然接受。据说印度尼西亚的米饭餐已被视为荷兰的国菜,它的对手是土豆泥杂拌:一道用根茎蔬菜的碎块所制的菜泥为主材料、外观欠佳的菜肴,用来纪念1574年莱顿遭围攻时,那些营养欠缺仍坚持保家卫国的志士,人们如今吃这道菜,只剩下情感上的意义。要烹饪美味的米饭餐并不容易,因为一次得做很多道菜,每道包含很多种材料。除了作为核心的一碗饭,同时还得准备十几样不同的菜品,放在黄铜容器里或酒精灯上保温。炒辣椒酱绝不可缺,这是用辣椒、多种香料、洋葱和蒜合炒而成的酱料,可用来浇在肉或鱼上,配鱿鱼尤其好吃。另外还有好几种配方不同的辣椒酱,有的加了酸橙皮,有的加了虾酱。

让·贝劳德《香榭丽舍大街的蛋糕店》
通过贸易而渗透各地的盐、香料和糖,渐渐登上了全球的餐桌
要使有天壤之别的烹饪风格彼此渗透,除了帝国主义和殖民行动以外,就只有一项活动:贸易。各种食材通过贸易而循环全球。
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食品的远程贸易局限于奢侈品。除非进口货色更廉价,否则大多数社会都自行生产其主要粮食。不过有时候,就连基本的必需食物也得自远方运来,无法轻易纳入帝国体系当中。盐即是这样的食品。要维持生命,一定得吃盐,人体在新陈代谢时会渴求比实际需要更多的盐分。盐还可用来保存食物,盐分可以杀死细菌、抑制腐化,因此成为应季保存腌渍食品时的必需原料。在没有盐矿或盐池的地方,必须借由蒸发海水来提炼盐,或从款冬、海蓬子等植物中萃取它们自泥土里吸收的盐分。不过有些社群无法在本地获得足够的盐,所有人口不断成长的地区在其人口超过某一限度后,就必须立刻从外地进口盐。因此盐是世上最古老的大宗贸易商品之一。
在北欧,对盐的需求更比黄金迫切,特别是16世纪时人口开始增加,食品产业努力想赶上人口增长的速度。波兰、法国和波罗的海部分区域有丰富的盐矿,荷兰的盐传统上即来自这些地区,但这些地方的盐越来越昂贵,遇上战争时期供应情况也不可靠。最令人觊觎的供应源位于葡萄牙和加勒比海地区,掌握在西班牙君主手里,据说此二地的盐最适合用来腌渍鲱鱼,价钱又便宜。对西班牙盐的依赖使荷兰人在1609年与西班牙媾和。而当荷兰与西班牙的和平状态终于破裂,对盐的需求也成为荷兰人在1621年成立荷属西印度公司的主因。
比起大宗、高价且攸关民生的食盐贸易,香料这种奢侈品的贸易应该不大重要才对。但事实上,胡椒几乎算得上民生必需品,因为全球精英阶级的菜单里少不了它。在16世纪和17世纪,胡椒贸易占了世界香料贸易的七成。香料贸易另外几样主商品为肉桂、肉豆蔻衣和肉豆蔻,它们的贸易量比较少,但是为贸易商创造了极高的利润。我们不能说盐改变了烹饪文化,毕竟盐的作用是加强味道,而非颠覆传统菜品的完整性;然而,在通过贸易而取得香料的地区,香料却促成新食物文化的诞生。
由于香料生产十分专业,而且有地域限制,香料市场益发显得神秘,产品价值也随之上涨。在古代,阿拉伯本土或许可以取得桂皮,但在中世纪时,真正的肉桂生产几乎全为锡兰垄断。至于胡椒,商人须到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肉豆蔻、豆蔻和丁香则仅出产于印度洋的几个地方和现今的印度尼西亚,尤其是特尔纳特和蒂多雷这两个“香料岛”。上述这些地方的产品大多出口至中国,中国市场最大,经济最富有。据马可·波罗估算,在他那个时代,每天有1000磅胡椒运进杭州。
有种说法是,欧洲之所以要香料,是为了拿来遮盖臭鱼腐肉的味道。而事实却可能是,当时的新鲜食品和保存食品大概都比今日的健康,因为种植时并未施以化学肥料。无论如何,香料在烹饪中担任的角色取决于口味和文化。用上很多香料的菜价格高昂,因此有区分社会阶级的作用。对吃得起的人来说,这一点使得加香料的菜成为无法避免的奢侈品。
传统上由东方独占的香料市场出现新局面,改变从糖开始。糖是大西洋生产的唯一可与东方香料媲美的高价佐料,大西洋的生产中心联合组成某种与东方竞争的香料阵线——西方的产糖岛屿对抗东方的香料岛屿。蔗糖取代蜂蜜,成为西方世界的甜味佐料。当时的情况可能是先有供给,接着才出现需求,因为在15世纪最后25年,当大西洋的产糖业因加那利群岛新蔗园的开发而突飞猛进时,糖渍食品仍是奢侈品。举个例子,当时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分赠给皇室儿童的圣诞礼物,有很大一部分是糖果。不过,就像18世纪的茶和咖啡以及19世纪的巧克力,大众很快地响应供应量的增加,调整了口味。1560年,亨利二世的医师报告:“人们用糖而不用蜂蜜……眼下几乎没有食物不用糖的。糖被用在面包中,被加进葡萄酒里。水掺了糖以后不但好喝,而且有益健康。肉被撒了糖,鱼和蛋上面也有。我们用盐比不上用糖那么多。”
(摘编自《吃:食物如何改变我们人类和全球历史》,[英]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 著,韩良忆 译,中信出版集团)
延伸阅读 >>>>>>
关于饮食文化,还有这些图书予人新知
《饭局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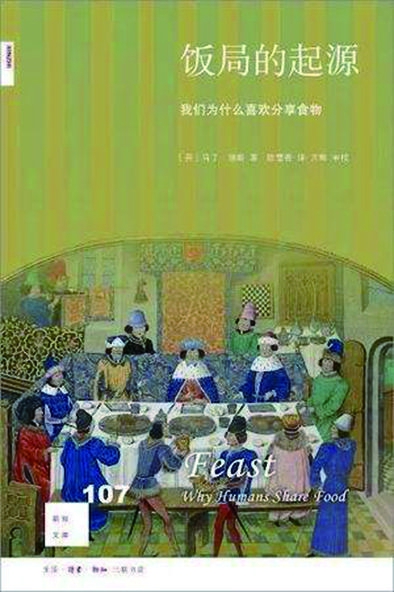
[英]马丁·琼斯 著
陈雪香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饭局起源于人类近亲黑猩猩对于食物的分享。这本书的作者剑桥大学考古系教授马丁·琼斯以讲故事的方式,为人们梳理了千万年以来,“人类”分享食物的历史。从人类近亲黑猩猩分享一只髯猴的活动,旧石器时代晚期狩猎者的大型狩猎活动,到农业起源之后人们在定居活动中的饭局,希腊罗马时代的经典宴会,再到现代大学教授们的晚宴。内容涉及古生物学、考古学、文献历史学、艺术史等,全方位解答了“为什么我们人类这么喜欢组织参加饭局、分享食物”。
《饮食人类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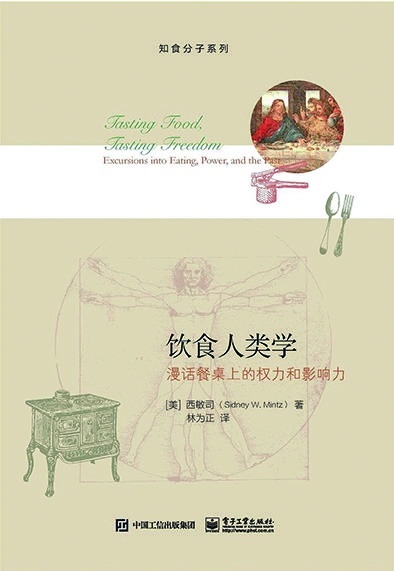
[美]西敏司 著
林为正 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年轻战士说,他们是“为了保卫喝可口可乐的权利而战”。这本书的作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类学教授西敏司也认为,纵观历史长河,在众多改变人类饮食习惯的方法当中,数战争最具效力。他在书中告诉人们,饮食不仅是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大事,也是人类文化史中的重要一环。饮食不仅仅与政治、经济、战争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对人类思想形态的形成造成了重大影响。在这本书风趣的论述中,人们将重新认识人类饮食的发展历程。
《餐桌上的世界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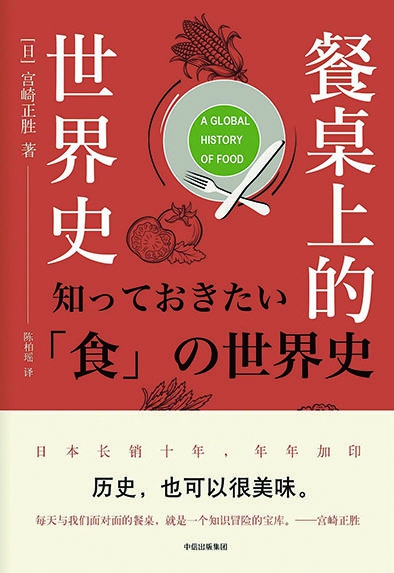
[日]宫崎正胜 著
陈柏瑶 译
中信出版集团
从最初寻找人类可用的食材,到全球食材的大交换,再到食物的过剩与危机,这些纷繁复杂的变动背后,既是人与自然生存博弈的体现,也是人类认识自我的漫长过程。这本书的作者日本知名学者宫崎正胜从世界史的大框架出发,通过平常可见的各种食材和料理,以全球性的宏大视角为人们讲述人类文明、文化的交流与变化的过程。
编辑:范昕
责任编辑:宣晶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