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8年西班牙爆发的一次大流感迅速蔓延,造成全世界近五亿人感染。其中,奥地利艺术大师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就是被这次流感夺去生命的。图为克里姆特的名作《生命之树》
连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令人揪心。
这并非人类第一次面对肆虐的病毒了——瘟疫简直是人类发展进程中挥之不去的梦魇。从古至今,人类其实从未停止抗争瘟疫的脚步,从未放弃为病人寻求治疗、慰藉、缓解、恢复的方式。抵抗瘟疫的历史,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堪称悲壮,却也极大地促成了医学的进步,并且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正值全民“战疫”的非常时期,让我们从阅读中一窥人类试图征服瘟疫的那些故事,从时光深处汲取前行的力量。
——编者
历经长达3000多年的围剿,世界终于彻底告别了天花
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与传染病不断作斗争的历史。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疟疾……多少肆虐的病毒细菌,让世界闻风丧胆、损失惨重。而时至今日,人类彻底消灭的,只有天花。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在经历了对天花长达3500年的苦难和困惑之后,我们终于开始对它有了一些了解,并终于能阻止它对人类的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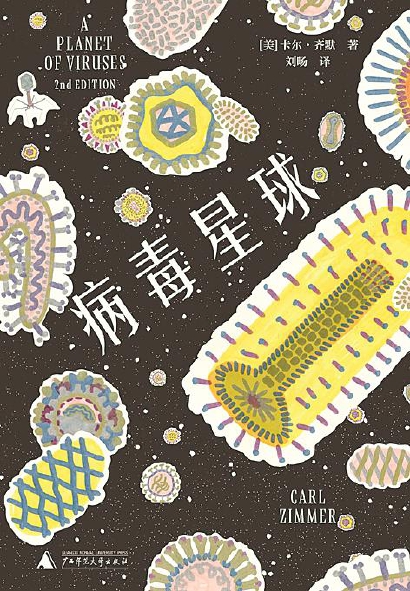
现代医学还真的曾经从自然界中完全消灭了一种人类病毒,它就是导致天花的病毒。
这真是人类一大壮举。在过去的3000年里,天花可能比地球上任何其他疾病杀死的人都多。古代医生就知道天花,因为它症状清晰,与众不同。病毒通过进攻呼吸道感染受害者。大约一周后,感染引起寒颤、发烧和难忍的疼痛。发烧几天后就消退,但病毒远未罢手。病人先是口腔中出现红斑,然后扩散到脸上,最后蔓延到全身。斑点里充满了脓液,给人带来难以忍受的刺痛。大约1/3的天花患者会丧命。哪怕幸存下来,脓疱也会覆上厚痂,在病人身上留下永不消褪的深疤。
大约3500年前,天花在人类社会第一次留下可追溯的痕迹:人们发现了三具古埃及木乃伊,身上布满了脓疱留下的伤疤。包括中国、印度和古希腊在内的其他许多古代文明中心,也都领教了这种病毒的威力。公元前430年,一场天花疫情席卷雅典,杀死了1/4的雅典军人和城市中大量普通人。中世纪,十字军从中东归来,也把天花带回了欧洲。每次病毒抵达一个新的地区,当地人对病毒几乎毫无招架能力,病毒的影响也是毁灭性的。1241年,天花首次登陆冰岛,迅速杀死了两万人,要知道当时整座岛屿也只有七万居民。城市化的进程给病毒传播提供了捷径,天花在亚欧非大陆如鱼得水。1400—1800年,仅在欧洲,每百年就有大约五亿人死于天花,受害者不乏俄罗斯沙皇彼得二世、英国女王玛丽二世及奥地利的约瑟夫一世等君王。
世界上第一种有效预防天花传播的方法可能出现在公元900年的中国。医生会从天花患者的伤疤上蹭一下,然后摩擦到健康人皮肤上的切口里(有时他们也把伤疤做成可以吸入的粉末,来给健康人接种)。这种过程称为“人痘”接种,通常只会在接种者的手臂上形成一个小脓疱。脓疱脱落后,接种者就对天花免疫了。
至少这是个办法。通常情况下,接种人痘会引发脓疱,接种有2%的死亡率。然而,2%的风险也比感染天花之后30%的死亡率强多了。人痘接种预防天花的方法沿着贸易交流的丝绸之路向西传播,17世纪初传入了君士坦丁堡。免疫成功的消息又从君士坦丁堡传到欧洲,欧洲医生也开始练习人痘接种。
当时,自然没有人知道人痘接种为什么有效,因为还没人知道什么是病毒,也没人知道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如何对抗病毒的。天花的治疗手段在不断的试验和试错中完善。18世纪末,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终于发明了一种更安全的天花疫苗。这个伟大的发明源于他听说的一系列民间故事。有几次詹纳医生都听说,农场的挤牛奶女工从来不会得天花,他想,牛会感染牛痘,而牛痘的表现和天花很像,会不会是牛痘给挤牛奶的人提供了保护呢?他从一个叫莎拉·内尔姆斯的挤牛奶女工手上取出脓液,接种到一个男孩的胳膊里。这个男孩长出了几个小脓疱,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症状。六个星期后,詹纳又用人痘对男孩进行了测试——换句话说,他让男孩暴露在真正的人类天花面前。结果完全没有新的脓疱长出来。
在一本印刷于1798年的小册子里,詹纳发表了这种崭新且更为安全的天花预防方法。詹纳把他发明的方法称为“种痘”,这个名字来源于拉丁语的“牛痘”。此后三年内,英国有逾10万人进行了牛痘接种,种牛痘的技术进而又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挤奶女工的传说,终于化作一场医学革命。
整个19世纪,医生们一直专注于寻找更好的天花疫苗。一些人把小牛当成“疫苗工厂”,让它们反复感染牛痘。一些人尝试用甘油等液体保存病人的伤疤。直到科学家发现天花实际上是病毒引起的,疫苗才终于可以工业化生产,运送到更广大的范围造福更多的人。
随着疫苗的普及,天花不断丢失它们的城池。20世纪初,一个又一个国家报告了他们最后一例天花。1959年,天花病毒已经从欧洲、苏联和北美洲全面溃退,只在一些医疗力量相对薄弱的热带国家发挥余威。但既然天花已经被逼到只剩最后一口气,公共卫生领域的科学家开始谋划一个大胆的目标:从地球上彻底消灭天花。
疫情不断爆发出来,又一次次被击退,直到1977年,埃塞俄比亚记录了世界上最后一例天花。整个世界彻底告别了天花。
(摘编自《病毒星球》,[美]卡尔·齐默 著,刘旸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稳定与安全地攻克黄热病,科学家们探索了近百年
疫苗的研制与改进,既书下人类的史诗,也堪称科学与工业的传奇。人类借此一步步攻克的病毒,就包括黄热病——一种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值得一提的是,研制疫苗的道路充满挑战与警示。黄热病疫苗近百年间即经历了多次迭代,科学家们不断探索与实验,只为寻求更为稳定与安全且能用于大规模接种的那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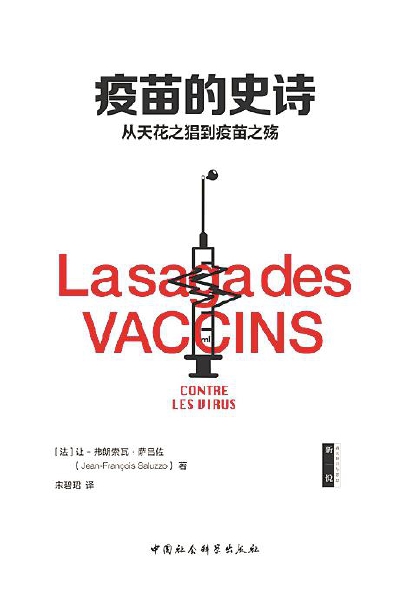
在20世纪20年代,一场灭除埃及伊蚊的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这种蚊子是黄热病的传播媒介,在除蚊运动之下,黄热病在美国东部的大城市、南美洲和加勒比群岛几乎绝迹,但该病仍然在非洲大行其道。为了研究并终结黄热病对人的侵害,全球有志于此的研究人员们开始通力协作,与黄热病进行殊死搏斗。
许多研究人员在尝试攻克黄热病时以身犯险,1931年美国的一份报告就证实了这一点:在1931年之前的五年中,各实验室共发生32起感染,其中五起最为致命,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波士顿哈佛大学的研究员们受损尤为严重。为了使人们对黄热病的研究得以继续,研制黄热病疫苗迫在眉睫。
1927年,哈佛大学的安德鲁斯·塞拉德博士带着十几只亚洲恒河猕猴和一些古巴岛埃及伊蚊来到 法国巴斯德研究所。此前有研究证实,亚洲猴子更易感染黄热病。
塞拉德来到巴斯德研究所,在得到当地卫生部门的支持后,他对黄热病的研究就此开始。研究员们对一位感染黄热病毒的患者进行血样提取并注射给一只恒河猕猴。
此外,他们还让16只埃及伊蚊叮咬患者背部并在28天后放出蚊子去叮咬另一只恒河猕猴。这两只猴子均出现感染黄热病症状,并在五到八天内相继离世。塞拉德将染病猴子的肝脏进行切片和冷藏,并将之分发到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他自己也将其带回哈佛,与助手马克斯·泰雷尔进行合作研究,而后者对黄热病疫苗之后的研制有着重大贡献。
1930年,离开塞拉德的泰雷尔来到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威尔伯·索耶教授麾下工作。经过不断探索,他们研制了一种黄热病病毒—血清的混合物,没有染过黄热病的志愿者接受注射后获得了免疫性。虽然从未被计划投入大规模应用,但这种疫苗还是令索耶教授成为黄热病疫苗的第一个发明者。
泰雷尔其实并不认同索耶将病毒—血清混合物作为候选疫苗的想法,同时对塞拉德与让·莱格莱研制的一种基于鼠脑制备的黄热病候选疫苗——该疫苗衍生出的减毒活疫苗被命名为“法国嗜神经毒疫苗(FNV)”也颇有疑虑。于是,泰雷尔在1934年投入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研发他认为现代且必须安全的疫苗。
泰雷尔和他的团队开始了减毒活疫苗的研制,他计划采用一种特性完全改变了的黄热病毒。他们的第一步,是成功使病毒适应鼠胚胎碎片的培养,而这是在历经17次失败尝试后才宣告成功的,之后他们又尝试使病毒适应鸡胚胎碎片的环境。泰雷尔用去除了头部的鸡胚胎碎片进行多次传代,每一次都对猴子进行测试。在第89-114次传代之间,人们惊喜地发现:病毒对猴子不再具有致病性。
经过不断地探索与实验,转眼到1936年,泰雷尔已拥有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候选疫苗,并随之展开了大规模测试。候选疫苗的生产从1937年1月开始,仅这一年,巴西就有超过39000人接种。到1938年9月已有60万人接种该疫苗。然而在之后的岁月里,各地开始出现一些疫苗事故,一些人在接种疫苗一两个星期后罹患脑炎。人们随机进行调查,发现是疫苗经过的传代过程出了问题。于是毒种批策略诞生,即用传代次数固定的病毒制备疫苗。到了1984年,随着一种新的化学稳定剂成功研发出来,黄热病疫苗的制备又迈到一个新阶段。不含禽白血病病毒的稳定性黄热病疫苗问世,并用于大规模接种。
直到21世纪初,人们还在探索更为稳定与安全的黄热病疫苗,此时的黄热病疫苗17-D已声名卓著,被视为最有效的疫苗,只要1针即可产生长达十年的保护作用。但这也不能说明该疫苗的完美无缺。2001年人们还是接到了七次疫苗接种事故的报告,共造成六例死亡。不过这些事故都是极端个别案例,黄热病疫苗并未因此受到质疑。
研制疫苗的道路充满挑战与警示,令人类不敢因噎废食。2009年以来,制备灭活黄热病疫苗的事情又被提上了日程,这个故事从塞拉德、泰雷尔开启,而现在又到了它重新起航的时刻。
(摘编自《疫苗的史诗》,[法]让-弗朗索瓦·萨吕佐 著,宋碧珺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宣布流行病的末日来临
疾病报告系统是流行病监测领域的重大进步,可以说整个人类都在其中获益匪浅。但是,等到疾病出现了再做出报告是不是有些滞后了呢?有没有可能赶在致病微生物在人类中流行以前就发现它、制止它?
若把微生物对人类的致病作用看作“恐怖袭击”的话,那么每天发生在动物和人之间成千上万次的接触就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提示信息了,哪种信息应该被筛选出来,呈送到“国家安全局”的案头呢?
在流行病监测的领域里,这种信息就是新型微生物从动物跳跃到了人身上。
在这个跳跃过程中,有一些人比其他人具有更高的被感染概率,这些人应该被称作哨兵人群,猎人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布控系统,监测与野生动物频繁接触的人们,以此来堵截微生物中的“恐怖信息”是完全必要而可行的。在庞大的微生物监测系统中,此种全球布控当然不是唯一的工具。
事实上,所有有助于掌握人类和动物种群传染性疾病的趋势和运动过程情报的研究手段都是可取的。
野生动物学家当然应该包括在内,他们可以观察到动物中出现的不同寻常的大面积死亡,在动物中出现流行性疾病的时候可以尽早搞清楚原因。很多时候,动物的死亡事件可能是人类疫情的“预告片”。
信息化技术也可以成为有效的工具,目前根据谷歌搜索数据构建的谷歌流感趋势系统可以很好地提供有关季节性流感的早期数据。工程师们还在继续努力着,或许在未来,利用搜索引擎来发现某社区兴起的流行病将成为一个常用的检索项目。
利用现有的病毒微阵列专用芯片对可疑感染者的组织或血液标本进行检验,可以快速便捷地检测出新型流行病的微生物凶手,但是芯片的检验范围尚受限于我们已知的病毒种类。科学家们正在探索更为广阔的检测领域,例如通过基因测序来发现来自宿主的组织样本中的所有DNA或RNA信息,以此找出致病原的踪迹。
……
当然,前面描述的一切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成为全球可及的监测手段,但是环球病毒预警行动组织已经建立起来了,并且已经遍布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已然成型的病毒风暴中,它和其他的许多类似的组织将共同为了保护人类而战。
我们处在一个充斥着新型流行病风险的世界。幸运的是,我们也处在一个用技术手段建造环球免疫系统的时代。我们宏伟却又十分简单的理念是:我们应该、也能够将流行病预测和预防做得更好。但真正大胆的念头是:有朝一日,我们能将流行病预测和预防工作做得漂亮到可以宣布“这是最后的一种流行病”——到那时,我们发现和遏制流行病的能力,已经强到连“流行病”这个词都不需要了。
(摘编自《病毒来袭》,[美]内森·沃尔夫 著,沈捷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安东尼·卡巴的油画《白昼战胜黑夜》
相关链接>>>>>>
在这样的时刻,让文学之光照亮我们的前路
你冲破黑暗的束缚,
你微小,但你并不渺小,
因为宇宙间一切光芒,
都是你的亲人。
——泰戈尔
像狱中等待渴望已久的自由,
我等待三月的晨雾,葱郁的山冈,
等待白云带来光亮和温暖,
等待田野里先来的百灵鸟的歌唱。
——伊凡·蒲宁
为了要活得幸福,我们应当相信幸福的可能。
——列夫·托尔斯泰
挺住,意味着一切。
——里尔克
让树木三思吧,然后使出力量,
把这如水的花,这如花的水
从昨天刚刚融化的雪面上,
全抹掉,全饮干,一扫而尽。
——罗伯特·弗罗斯特
英雄的心尽管被时间消磨,被命运削弱,我们的意志和坚强依然如故。坚持着去奋斗,探索追求,绝不屈服!
——乔伊斯
种子不寄“希望”于光,就生不了根,然而希望并不那么容易,希望需要自觉、开放和许多失败。
希望不是乐观者的毛病,而是强有力的现实主义,是一颗脆弱种子的现实主义:种子只有接受地底下的黑暗才能长成树林。
——亚历山德罗·达维尼亚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海明威
这是从地上出来的霜,这是春天。
这个春天先于万木披绿、百花盛开的春天,
正如神话先于有规则的诗歌。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更能清除冬天的烟霾和一切郁积,
它使我确信地球还在襁褓之中,
到处伸出婴孩的手指。
从最秃的眉脊上生出了新的鬈毛。
——梭罗
美好生活没有先兆。
它经受住绝望的氛围,
然后出现,步行而来,不被认识,不带来什么,
而你就在那儿。
——马克·斯特兰德
编辑:范昕
责任编辑:卫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