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翰·伯杰是英国艺术评论家、小说家、画家和诗人。1926年出生于伦敦,他以小说、短篇小说集以及非虚构作品闻名于世,他的多部艺术批评著作形式创新,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政治洞察力。2017年初,90岁的伯杰在巴黎郊区的家中去世。
在他去世三周年到来之际,伯杰最重要的小说《到婚礼去》中文版出版。伯杰的传记作者汤姆·奥夫顿说:“他所有小说中,《到婚礼去》最令我动容,这很难仅用批评术语来解释。这是一本关于艾滋病的小说,写于1994年。印象中与和桑塔格的约定有关。伯杰与桑塔格曾频繁通信,影响了彼此关于摄影的写作。她于1989年发表了《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这在当时是尤为紧迫的主题。伯杰写作这本书时,家里有一位成员被诊断为HIV阳性,最终由他来照顾,所以他获得了不同的视角。”
《到婚礼去》是这样的一部小说——它关于巨大的心碎,升腾的希望,而在一切之上,是爱战胜了死亡。
作家麦凯恩评价:“这是我们时代最伟大和诚实的爱情故事之一。它做了所有伟大文学能做且应做的——我们在那些并非自己的身体、故事、历史、地理中活了过来。我们通过想象,被给予了一份新的生活。如果我哪天必须打包藏书,这本书永远不会被放进箱子里,我会把它塞进外套带在身上,无论我在哪里。”
作家翁达杰形容:“这是一首抒情诗,伟大、悲伤、温柔;一部小说,共同体和同情心以某种方式汇成漩涡,克服了命运与死亡。无论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我知道我都会把这本书带在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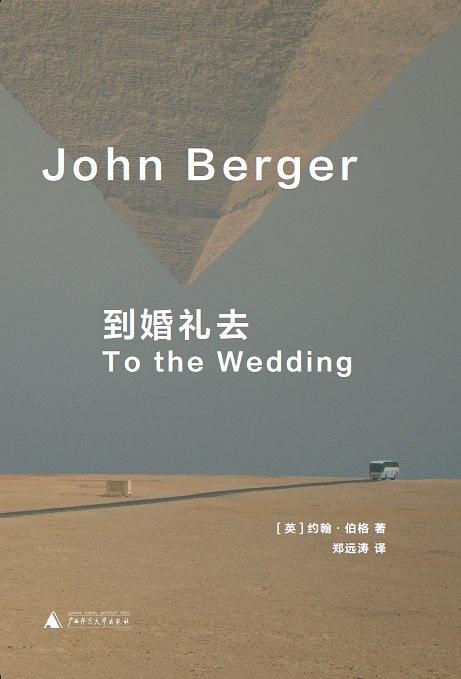
在他的文字里,生命以一切可能伸展开来
纳迪姆·阿斯兰
我读到这本澄明动人的书是一九九五年它刚出版时,从此以后,我每年都会重读一次,渐渐和书中人成了亲密朋友,甚至可能是一家人。它字里行间都见证着我所珍爱的一切,它也证明,约翰·伯杰居于世界上最超群有力的作家之列。
古人相信——书中希腊盲人叙述者这样告诉我们——创世的第一个举动是分开大地和天空,这是艰难的,因为天地互有欲望,不愿分离。在意大利滨海的村子戈里诺周边,陆地化成水,以求尽可能接近天空,像镜子一般反映它。
戈里诺是书名中的婚礼拟定要举行的地方。新郎是个叫吉诺的年青人,在集市摆摊卖衣服为生。婚礼前夕,他爸爸打算杀死儿子的未婚妻。他感到这是一桩必要的罪行,连自己事后遭审讯的情形也想象到了。
他筹划要杀的新娘叫妮农。故事进程中,我们跟随妮农在布拉迪斯拉发的妈妈、在阿尔卑斯山法国地区的爸爸,跟随两人各自起程,到婚礼去。妮农的未来公公的嗓音,只是穿插于父母旅程的众多嗓音和故事里的其中之一,这些嗓音、这些故事属于当下,也属于久远的过去。
一幕接一幕,我们看见伯杰展露他作为文体家的出色才华。这里有日常人类活动的精确复现。(一个兴许是微醺的男子某夜出门,在道路和山坡上用硕大的字母涂写爱人的名字。他带着一罐油漆、一把刷子、一个改锥——最后一件东西霎时间叫人惊讶,不过我们随即会想到,他需要用改锥来撬开油漆罐的盖子。)这里有对于自然界的敏锐意识:又陌生又熟悉的笔墨。(伯杰说,一只土拨鼠从冬眠醒来,骨头疼痛;我们从未想到这一点,但当然该是这样的。)伯杰构思的对话漂亮之极。妮农的爸爸在某个时刻停下摩托车,跟路上遇到的一个牧羊人交谈,他们聊天的十来句话里有一种妙不可言的诙谐调子。
行驶过又一段路程后,尚·菲列罗走进一座博物馆,里面陈列着一挂美丽的古希腊项链,他想盗走项链,送给女儿作结婚礼物。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片刻,如是者,书中还有很多。以我们对他迄此为止的了解,决想不到他会动偷窃之念。但我们马上能想起妮农,他的女儿、待嫁的新娘,是HIV感染者。她从匆匆邂逅的露水情人身上感染病毒,根据治疗师的看法,她只剩下三年多左右的正常人生。我们记得,在大悲大恸、一切失去意义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行为可能也会脱轨——还不只是针对自己。
小说家兼评论家杰夫·戴尔(Geoff Dyer)有一次谈到伯杰,形容他“提醒着我们那大多数当代作品会教我们遗忘的:那就是,大作家最终以人文素质卓异于众。”这种人文素质——我说的是,始终明辨生命的悲哀与残酷,明辨那些可将神志最清明的人引向无可挽回之错的恐怖与混乱,也明辨带给我们快乐的大事小情——它在这本书上,在伯杰写过的每一页里都清清楚楚。从流动工人的困苦到农民生活的艰辛,作家一直在讲述各种各样的被剥夺境况,《到婚礼去》和艾滋病题材也极其自然地进入他的作品集当中。伯杰说,早在1940年代,他就发现自己“盼望和这世界上那些产出权力的人越无关越好。这盼望变成了一种终生的规避。”这一点,使他在今日作家群中独一无二。
妮农的HIV阳性状况是她的未来公公想杀死她的原因所在:这是另一个震撼,但吉诺难断痴情,不顾妮农的病,坚持要跟她结婚,而在一时的疯狂中,他爸爸希望能让儿子免于多年心碎之苦。
然而吉诺抓住了这样的建言:
和她结婚吧。你的结婚对象是一个女人,不是一种病毒。
如此作品,如此智慧与领悟有一个词可以形容。那是恩典(Grace)。
妮农的爸爸驾驶摩托车之际,她的妈妈也同样满怀痛苦,坐大巴从布拉迪斯拉发前来。她叫泽德娜,是个刚烈、聪慧,或许还有点脆弱的女性;这些年来渐与女儿疏离,也许是她那边发生的悲凉的欧洲历史所致。踏上旅程前,泽德娜去做了头发:我外表越好,就越少给妮农添上负担,这思绪读来有千钧之重。在大巴上,她和邻座男子交谈起来。他们的23页谈话(译本第145—155、159—162、167—174页)属于我一生读过的最真切、最澄明、最直见性命的文字。有时我甚至于相信,这些文字概括了我活在地球上一生为人所需要的一切。一种传承、一卷圣书。一部指引、一首安慰之歌。男子问泽德娜要去哪里,她说了真话,给他看了一帧吉诺的相片:男子说吉诺的样子仿佛一个始终没有学会计算的人。
泽德娜说:如果他能在街市卖衣服,我想他会计算吧!
计算价钱,那是会的,但是不计后果。
所以我说是疯狂,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恰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比你和我都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段文字有惊人的透辟。这些词语过后,生命以一切可能伸展开来,令读者叹为观止。
泽德娜征求男子的建议。
我见到她要对她说什么?我受不了谎言。这辈子我一直在跟谎言斗争——并且付出了代价……
没有必要说谎。需要的是平静。
当绝望与困惑行将吞没我们,我们需要听见的正是这些朴素的话语。需要的是平静。对这个建议,对这本书、对伯杰写过的所有,我们只能报以一句:
谢谢你。
作者:纳迪姆·阿斯兰(巴基斯坦裔英国作家)
译者:郑远涛
编辑:柳青
责任编辑:柳青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