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故而知新”,究竟是“边温故边知新”还是“温故后才出新”?历史编纂学在西汉之前已有千年历史,司马迁如何建构自己的体例……今年上海书展首次辟出国学馆,推出了“七天七堂课”系列国学讲座。樊树志、傅杰、姚大力、陈引驰、辛德勇、张国刚、刘永翔……书展七天,每天有一位文史专家,分别围绕《论语》《老子》《史记》《资治通鉴》等国学经典做阅读导览,为观众解惑。
“七天七堂课”成为本届书展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不仅七堂课的预约30分钟内就被“秒光”,现场七天更是座无虚席。通过学者解读经典聚焦传统文化,为深度阅读“圈粉”。
“守正”中看“出奇”,发现经典作者的眼光和智慧
被称为“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究竟承载着作者司马迁怎样的治史心志?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姚大力教授开讲的《“与司马迁对话”——问君此书有多珍》令人耳目一新。
在西汉之前,历史编纂学已经有千年历史,姚大力介绍,对于当时历史书写的两种传统,司马迁并不认同, 他认为,“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始终。”
“儒者断其义”是指用史笔进行道德审判,“驰说者骋其辞”指诸子百家在纵横奔放的议论过程中,把历史证据当作修辞来用,采用这两种取向和宗旨的史学书写,被关照的人物容易从实际背景中抽离出来,成为“历史故事”,成为一起割断的、孤立的事件,而不再综合考察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司马迁认为,这是“不务综其始终”。

创作《史记》时,司马迁把三千年的历史进行原始察终式的追溯与完整呈现,当遇到不能完全解释的,就有所保留。《史记》的历史叙事,构成一种有意识地要突显其变迁过程、多层面包含着不同文化实体的多元历史,这正与他在《报任少卿书》中所阐明的原则“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相一致,“比如,他不仅仅记录汉文明,还写到了中亚、西亚诸国。”姚大力说,这样的“治史”精神非常伟大。
学者所拟定的选题方向,没有过高的学术门槛,有助于普通读者理解文本。而新鲜的解读角度,则展现出经典丰富的阅读层次,令不少读者萌生出再读经典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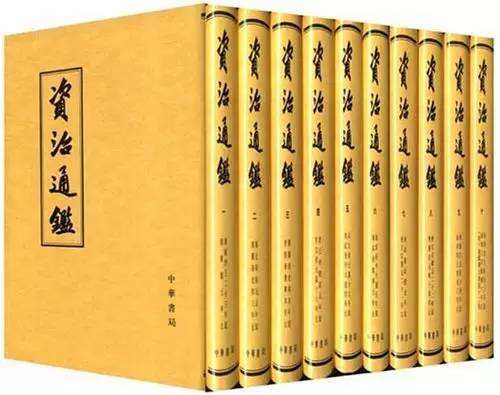
比如,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张国刚在《资治通鉴》的“守正”之中,看到“出奇”的一面,令听众耳目一新印象深刻。他举例,在历史上,曾国藩看出 《资治通鉴》中兵家用法之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驰通过比较的方法,开讲“道家老庄的智慧”。“《老子》西文的译本要比《论语》多得多。”陈引驰的这一说法刷新了很多人的印象,“在中国,儒家和道家对于塑造中国文化都非常重要,《论语》展现的更多的是世俗、社会、道德的一面,而《老子》更注重的是思辨,其思维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应用……”
“温故而知新”,别因温故艰辛失去知新的机会
开卷有益,传统经典不仅蕴藏着巨大的信息量,而且还传递着中华智慧,为当下的决策或自省提供借鉴。
科技越来越发达,各行各业的成果都在不断丰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傅杰说,30年前他在求学时,训诂学、音韵学之类的研究成果,一年也出版不了多少本,但如今几乎每个月、每周都有此类新书出版。想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专业文献几乎看都看不过来。知识的流量那么大,应该如何主动学习才好?
这令他萌生开讲 “从《论语》看孔子的学习观”的想法。傅杰介绍,孔子所说的“学习”是从读原典开始,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君子,其中包括大量扎实的文本阅读。

这在移动互联网提供大量信息的当下尤为重要。按照孔子的观点,将知识内化需要通过反复学习,没有捷径可走。《论语》中,孔子率先强调要温故而知新。有人认为,温故、知新是两个并列的词,也有一种说法称两者是表递进的关系。
“在今天的语境下,或许人们更倾向前一种理解。”傅杰说道,有人会说我们的大脑为何要成为前人的“跑马场”?也会有人迅速地拿知识变成财富、名望。“但这恰恰是一种逃避,因为温故本身是非常艰辛的过程。”
七天的国学课程中,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解析流传千古的《燕然山铭》,诗词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刘永翔教授带来题为“诗与好诗”的讲座。明史专家、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以“张居正改革漫谈”为“七堂课”压轴。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七天七堂课”每场讲座还配备手语翻译,通过网络实时直播,让书展场内场外更多人走进国学,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作者:童薇菁
制作编辑:童薇菁
责任编辑:李婷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