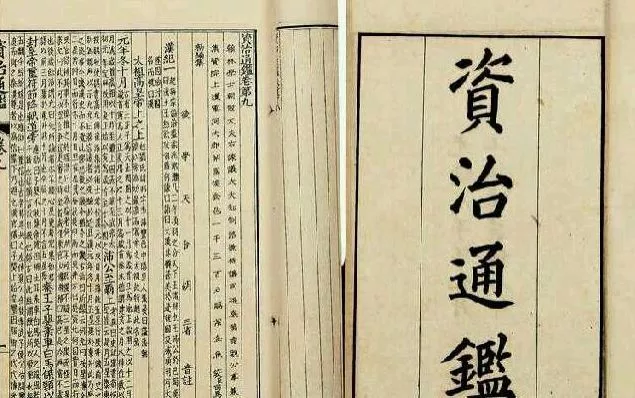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宋神宗支持下主持编撰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鉴戒史学集大成之作。此书的编撰宗旨就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在司马光看来,历史可效法、可借鉴,对于帝王和各级官员的治国理政来说,历史就是一面镜子。
《资治通鉴》在史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从史料搜集、史事考证、遣词造句、体例和叙事框架的安排,每一个环节都体现出司光及其编写班子的匠心独运,体现出高超的史学才能与深厚的史学功底,达到了当时条件下历史学求真、求善、求美、求通的至高境界。
《资治通鉴》的“资治”途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历史叙事来表达思想,提出自己的政治关怀
历史学家讲道理不是凭空高谈阔论,而是依托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故事,从可辨识的历史表征出发,在努力还原历史情境和追求历史本相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关怀。
《资治通鉴》在最高层面的思想表达和政治关怀,是通过总结治乱兴衰的规律提炼出“经世大略”。全书以“三家分晋”开篇,通过周威烈王“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样一个事件(历史表征),来探讨这件事情导致礼崩乐坏的历史意义,进而提出以“纪纲”为中心、以“名器”为依托的礼治思想,得出一个具有历史高度的结论:“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在此基础上,司马光进一步强调了教化与风俗的重要性。

在叙述曹操不敢废汉而自立的历史事件之后,司马光提出:“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
他认为曹操之所以不敢废汉自立,原因就在于东汉一朝形成了遵守礼法的社会风气,所以“州郡拥兵专地者,虽互相吞噬,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
《资治通鉴》所传承的政治文化是多方面的,例如关于君道政体、德刑礼法、选官用人、边疆民族、家国兴衰等,无不涉及,是儒家治国理念的汇聚之作。而且,该书在传承中有塑造,以其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特殊贡献,在儒家治国思想的探索和表达方面开辟了新局面。

《资治通鉴》诞生后,被作为历代帝王读史的主要范本,对政治文化的影响至深,可谓不读《资治通鉴》则不足以谈政治。在此影响下,是否读过《资治通鉴》,已经成为衡量古代政治人才的标准。
二、通过历史叙事展开对现实的批判
这种批判不是简单的借古喻今或影射现实,而是带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去研究历史和叙述历史,让历史之光照进现实。
《资治通鉴》叙述的历史事件无论是久远的还是晚近的,都令人感觉切近和真实,总能触动读者的神经。在王夫之看来,司马光通过历史来批判现实,有着不同于一般世俗历史讲述者的高明之处,关键在于他把历史讲得很亮堂,而不是那么阴暗。

当然,要使历史能够真正发挥资治的功能,就必须要有高超的叙事技巧。故事讲不好,历史就很难发挥经世作用。《资治通鉴》在这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遣词造句精练准确,叙事逻辑谨严,善于烘托气氛,既血肉丰满,又无空疏之语,能够把读史之人带入文字背后的广阔历史时空,令人看到即使在现场也无法看清的东西。
近人黄公渚《司马光文》也对“司马光文在文学上之位置”评价极高,认为“其能讲究朴学,摆落凡近,直追古昔者,在宋必以司马光为之巨擘。光所为文,不矜才,不使气,如行云流水,极其自然之妙,而论事透澈,说理精深,尤为独绝”。
《资治通鉴》在文学上的成就,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在历史叙事这个维度上的最高水准。

三、通过历史叙事来达到“知人论世”的目的
人性是无比复杂和多变的,前人的教训不能简单地变为后人的智慧,只有在“知人论世”的反思中,历史才有可能帮助人们变得更加聪明。
《资治通鉴》中大量的叙事和史论,都贯穿着司马光的反思。例如,记唐高宗时期担任吏部侍郎的裴行俭“有知人之鉴”,看重应选时并不知名的王劇和苏味道,而对“以文章有盛名”、受到时人追捧的明星诗人“初唐四杰”并不看好。
《资治通鉴》记述裴行俭的话是:“士之致远,当先器识而后才艺。(王)勃等虽有文华,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邪!杨子(杨炯)稍沈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幸矣。”结果,“既而(王)勃渡海堕水,(杨)炯终于盈川令,(卢)照邻恶疾不愈,赴水死,(骆)宾王反诛,劇、味道皆典选,如行俭言”。

这是一个在裴行俭去世后就在唐代流传甚广的虚构故事,史籍中记载甚多,其中裴行俭的观点性话语作“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到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将这个虚构故事中裴行俭的话进行了符合北宋政治文化语境的改写,形成了“士之致远,当先器识而后才艺”的经典表述。
司马光没有在这里发表“臣光曰”式的议论,而是借助裴行俭之口,在相关史源的基础上,通过叙事表达出自己“知人论世”的观点和主张。
宋人概念中的“器识”已经超越了功利意义上混迹仕途的能力,而是包括了个人的才识和气节品格等。司马光改“文艺”为“才艺”,不仅是对士子的文章之才艺看不上,就是对他们为官的能力也未必看得上。

无论裴行俭是否公开评价过这几位应选的士人,也无论后世的历史叙事中借裴行俭之口对初唐四杰“浮躁浅露”的批评是如何的不公正,但是《资治通鉴》对裴行俭“有知人之鉴”的表彰却有较强的事实依据。而克服士人普遍存在的“浮躁浅露”之性格缺陷,恰恰是北宋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话题和实践性很强的政治举措。
司马光在记载裴行俭去世的事件之后,再作如此追述,其“知人论世”的意图非常明显。从后来的阅读和接受看,其“资治”目的无疑是达到了,其实也就实现了唐太宗所说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历史资治价值。
历史学家决定了历史事实如何说话,在扎实考证基础上的合理想象加上巧妙的叙事,是呈现其卓越见识的不二法门。司马光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资治通鉴》展示了通过历史来资治的基本途径。
来源:人民出版社
编辑:李添奇
责任编辑:李伶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