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大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社会形式诗学三部曲”中,前两部讨论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最后一部《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则是聚焦现实主义。这种回溯的形式别具一格。兴许是因为现实主义这一概念过于复杂,而且奥尔巴赫、卢卡奇、伊格尔顿、雷内·韦勒克和罗杰·加洛蒂等重量级理论家都曾将这一问题作为练兵场,詹姆逊才将之留置到最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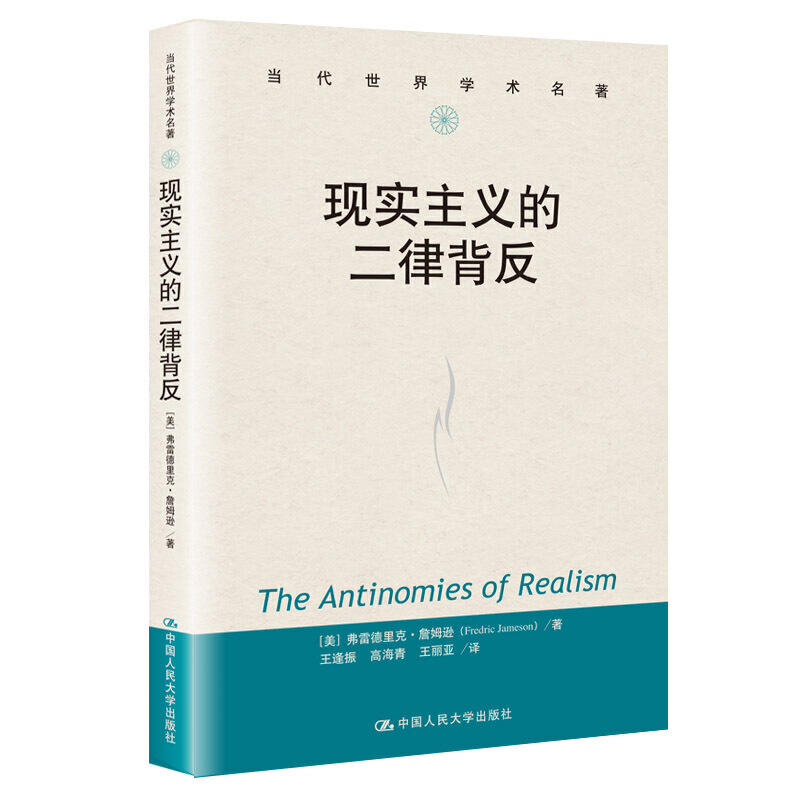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 著
王逢振 高海青 王丽亚 / 译
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事实上,现实主义是年届九十的詹姆逊长期关注的话题,但此次他并没有纠缠于客观性、典型性和历史性等传统问题,而是另辟蹊径,转而强调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力存在于“叙事冲动”和“场景冲动”的张力之中;他不再选取传统左派文论的视角,而是以“情动”这一文论界当前的最热话题作为分析焦点。
詹姆逊认为,“叙事”和“描写”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时间观,“叙事”是线性的,与其对应的是故事的“情节”;而与“描写”对应的是“场景冲动”,其产生的效果则是“永恒的当下”或“情动”。詹姆逊的前辈卢卡奇对二者同样进行过论述,但追求“总体性”的卢卡奇更看重叙事,因为叙事才能推动故事的前进。对于酷爱对细节进行百科全书式描写的左拉,卢卡奇则认为他不过是矜奇炫博,这类描写和故事中的人物命运没有必然联系,司各特、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等才是现实主义的旗手。然而詹姆逊认为“叙事”和“描写”有同等重要性。在他看来,左拉那种不厌其烦的一一罗列正是“情动”的源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称左拉为对“情动”进行编码的高手。詹姆逊还重新检视了托尔斯泰、佩雷斯·加尔多斯、乔治·艾略特等作家的作品,对其中的“情动”作挖掘和评析,由此重构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谱系。
其实,早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詹姆逊就提出过“情动的消逝”的著名论点,用以说明梵高的《农民的鞋》和沃霍尔的《钻石灰尘鞋》这两部作品的高下。詹姆逊对“情动”的关注与他对雷蒙·威廉斯的阅读不无关系。在对社会进行“认知测绘”时,威廉斯曾批评弗洛姆关于“社会性格”以及本尼迪克特关于“文化模式”的说法,认为之前的这些概念过于抽象,无法完整地传达人们对所处时代的鲜活、细腻而独特的体验、感受和情感,因此提出“情感结构”这一概念。詹姆逊关于“情动”的相关论述显然更进了一步,有更为复杂的理论效果——“情动”不同于那些被“命名了的情感”,而是处于体验状态的“身体的感觉”,只能用“独特性和强烈度”表示,“叙事”和“场景”则是“情动”得以孕育的温床。
借助“描写”或“场景”,文学成为传达各种“感觉”的重要场所。在“故事”中引入“情动”,是现实主义横空出世的标志,二者间的动态关系决定着现实主义内部的“变奏”。在越来越理性化的时代,在大众越来越沉浸于光怪陆离的图像或形象中时,在理论对“总体化的感觉”进行抓取、概括和抽象时,总有些部分会逃逸,无法被语言捕获,无法被理性完全笼罩,因此,对“情动”的强调既有理论意义,同样有现实意义。通过召回种种仍无法命名的“感觉”,可以丰富和拓展文学批评的疆域,以描画更广阔、完整和更接近真实的现实空间或“总体性”,同时让“人”得到更细致入微、更好和更全面的关照。
十多年前,在杜克大学访学时,同在的朱国华教授约我一道对詹姆逊做过一个访谈,在访谈中,詹姆逊强调自己的兴趣始终是形式和历史间的关系。就此而言,“情动”这次在詹姆逊理论体系中的“回归”,更为全面地说明了资本主义主体性形成、“形式”和历史间的互动及其内部张力问题。由此,詹姆逊不仅完成了自己对现实主义文学谱系的重构,同时还为“情动”最终进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凿开了一条大道——现实主义由此被重新激活。此外,从五光十色的大众文化文本到对文学“经典”的聚焦,从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回归到更为坚实的现实主义,从艰深的理论演绎回归到“情动”或身体的感受,或可理解为“后期詹姆逊”思想疆场的上空开始漾起的一丝怀旧气息。
作者:何卫华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荷兰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编辑:陈韶旭
责任编辑:李纯一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