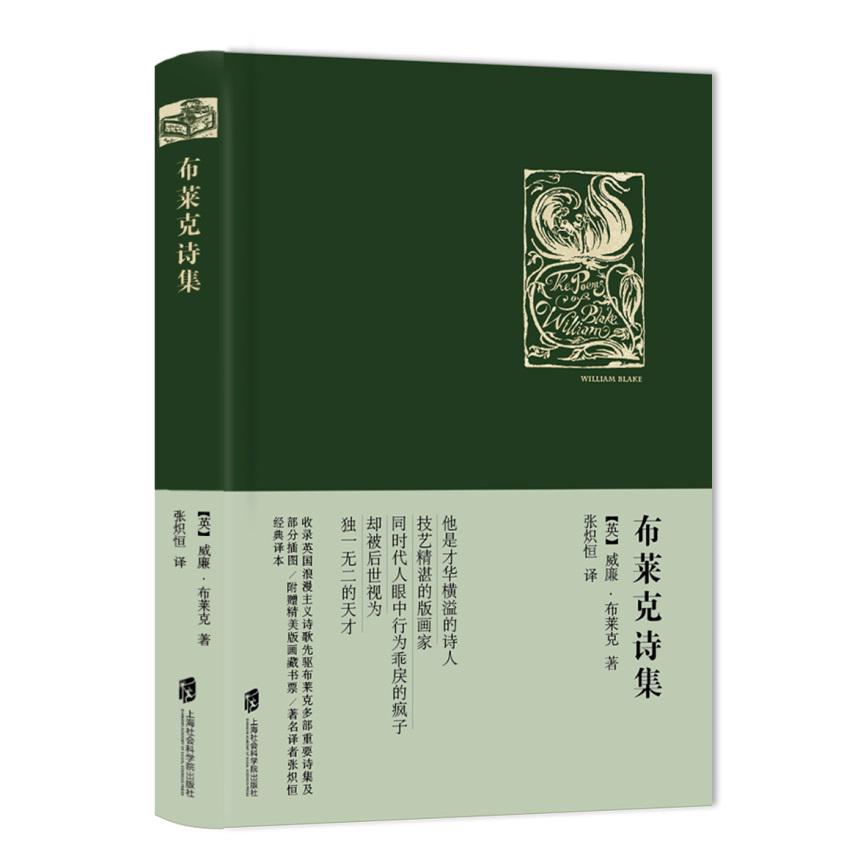
《布莱克诗集》
〔英〕威廉·布莱克◎著 张炽恒◎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年2月出版
69.80元 239千 436页 32开 精装
ISBN978-7-5520-1593-5
我愿意以人子和诗人的名义,而不是以学者或译者的名义来向你奉献这部译诗集。它的作者是一个我们知道得太少的诗人和圣人。在了解他和他的诗之后,我们将意识到,忽视他,对于诗歌尤其是外国诗的读者是一个多么大的缺憾;对于外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工作是一个多么大的缺陷。
他是一名英国诗人,全名威廉·布莱克,属于18世纪末叶和19世纪初叶。从文学史上来说,属于前浪漫主义时代,虽然他与这个“主义”并不相干。即便在本国,在欧美,也曾有很长的时间他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在世时,只有华兹华斯等少数人注意到他,并受了他的影响。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他才声誉日增。其间的原因只有一个:他远远地超越了他的时代。这位生前备受冷落的诗人,从此成了评论界的宠儿、大师所效法的大师。
正如W.P.威特卡特在《对布莱克之心理学研究》一书中所说:“雪莱、济慈、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声名依然如旧,拜伦的声誉已不如他在世之时,骚塞已经被人们遗忘;而布莱克的声望却与日俱增。”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布莱克研究专家达到创纪录的100多位。
英国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W.B.叶芝从1887年起编辑布莱克的诗作,并受到他的很大影响;他在日后模仿布莱克,创造了一个自己的宗教神话体系。
美国20世纪的诗歌大师之一T.S.艾略特曾专注地研究布莱克,“向布莱克学到了不少东西”。
一些批评家在论述诗歌发展进程时说,布莱克和华兹华斯是英语诗歌革命的开路先锋;另一些评论家在褒扬艾略特时,将艾略特和布莱克、华兹华斯一起,并称为英语诗歌革命的三大开路先锋。
布莱克,布莱克,布莱克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我们难以很快地作出回答,因为我们也许已经开始意识到评论界的一个公断:他是英国文学史上最独特、最复杂的诗人。
一、纯真的人,神圣的疯子
布莱克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个诗人。
许多人为他画过像。初次见到他的像,你一定会被震慑住,至少是一惊:这是一副多么不寻常的面容啊!他的异常宽阔明朗的前额,他的一双目光如炬、又略显惊惶的大眼睛。当你再次看他,你会看到他眼睛里的智慧、专注、“疯狂”和纯真。他跨越世纪注视着自己预言过的世界。
1757年,他出生在伦敦一个贫寒的袜商家庭。他从小就“富于幻想,神经过敏”。4岁时,他产生幻觉见到上帝;另一次,他又见到田野里一棵大树上栖满了天使。类似的另一次经历是在他30岁的时候,他19岁的弟弟罗伯特·布莱克患病夭折。他见到临终的弟弟的灵魂冉冉上升,穿过屋顶,升向天空。他乐而忘悲,击掌相庆,欣然歌诵。最后一次,是他临终的时候,他无比安详,面带欢乐的笑容,吟唱着他在天国所见的景物。
这种“神迹”般的经历,无论意味着什么,至少告诉我们一件事:他是个虔诚的人。我们还将看到,他确实超脱了世俗。
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其原因不是家境贫寒,而是他的个性。他不喜欢正统学校的压抑气氛,拒绝入学。这时他还非常年幼,而他极强的个性已经开始显露。他“对任何使他受约束的企图都以不可遏止的愤怒来反抗”。幸好,他的父母虽然是普通市民,甚至是小商人,却非常开明,听凭他不进学校而在家中学习他所喜爱的东西。对于布莱克,这是难得的幸运,但也给他日后的生活带来了隐患。这意味着他将没有阅世能力,与世俗格格不入。
他所喜欢的是绘画和诗歌。他11岁进绘画学校,12岁开始写诗,那些诗后来收入了《诗的素描》。他在绘画学校的3年多中,表现出了非凡的艺术才能,父亲预备让他师从一位著名的画家。但是,为了不影响父亲的小本生意和弟妹的前途,他主动放弃了这个求之不得的机会,去给一位雕刻家当学徒。那一年,他才14岁。这个单纯的人!
他终身靠绘画和雕刻为生,诗歌从未给他的清贫生活以补贴。他的第一部诗集是靠朋友的资助印成铅字的。他的一生便是:创作绘画和雕刻作品,收取稿酬或将其出售;创作诗歌,配上自己作的插图出版,由自己、偶尔由别人谱上曲子,在朋友的沙龙里咏唱。只有一个例外:27岁时父亲去世,他和弟弟一同开了一家印刷店,一年后,印刷店破产;从此,他再没有谋过别的生计。因为生活所迫,他不断地搬家,最远曾经搬到苏格兰;有时,他靠别人的资助生活。他接受别人的资助,但从不妥协,从不出卖自己。他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
他一生最大的幸运是他的婚姻。21岁时,他因追求一位轻浮的姑娘而失恋。这时,邻家姑娘真挚地向他表示了同情。她的名字叫凯瑟琳·布歇尔,本人是文盲,父亲是菜农。4年以后,布莱克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克服家庭的阻力,使邻家姑娘的姓名变成了凯瑟琳·布莱克。布莱克夫妇没有子嗣。温柔的妻子成了他一生的忠实伴侣和唯一安慰。他教会她读书、写字和制版技术,使她又成了他最忠实的助手。同时,他也忠实于妻子。这是他与几乎其他所有诗人不同的地方,他的一生,从未有过绯闻,从未拜倒在什么贵妇人的脚下。
他大无畏。在那个时代,英国是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大本营。然而,他却敢于写诗歌颂法国大革命。著名出版商约瑟夫·约翰逊敢于印行玛丽·沃尔斯莱夫的《为女权辩护》和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可是当他印完布莱克的《法国大革命》第一卷后,竟不敢拿到市场上去出售。
在《天国与地狱的婚姻》中,他竟然否定代表理性的上帝,赞美代表力的撒旦,并且宣称或者说预言上帝退位:“永恒的地狱复兴了……现在是艾登在统治,是回到伊甸园的亚当。”他希望或者说预言天国与地狱结合,成为理想的人世。
在客居菲芬时,他竟然大怒将一名警员逐出花园,被警方指控犯了挑动暴乱、威胁国王罪。几个月后,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在听审者的欢呼声中被判无罪释放。
他的一生就是工作。W.L.伦威克在《1789—1815年间的英国文学》中说:“威廉·布莱克的一生质朴无奇,以雕刻家知名于世。他和出版商相处通情达理,关系融洽;他经常出入于艺术家中间,他们把他视为其中的一员;他有一些爱他并且帮助他的朋友。他的编年史极其简单,传记上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大书特书,只有这些一直延续的简单的事实和紧迫的艺术创作活动。他的生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从中我们只能看出雕刻职业事务、情感关系和哲学思想等方面的强度变化。”简单地说就是,布莱克是一个单纯的人,过着单纯的生活,他一生中最主要的活动就是进行艺术创造工作。直到去世前几天,他仍然在工作。“他叫人用最后几个先令去买碳笔”。他画完最后一幅画,将它放下,说道:“我已经尽力而为了。”他没有立遗嘱,这就是他的遗言。
1855年,塞缪尔·帕尔墨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说:“布莱克,你见过他一次,便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知识博大精深,他谈吐非凡,但有些神经质……和他一起在乡间散步,就是在接受美的灵魂……他是一个不带面具的人……他是那种我们在整个生命旅程中所遇见的绝无仅有的人。”
这就是布莱克: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一生清贫,但具备最独立最可敬的人格、杰出的天赋和非凡的才能;生前没有得到显赫的声名,但毫不介意地沉溺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和精神世界。
他脱俗,但并没有放浪形骸。他只是有些“疯狂”。他的谥号就是“神圣的疯子”。他让人想起美国著名的黑色幽默小说家冯古内特的《上帝保佑你,罗斯沃特先生》中的“疯子”。神圣的疯子。那部小说中多次引用布莱克的诗句,而且只引用了布莱克的诗。他不放浪形骸,他很专注认真。他认真地疯,他在追求什么?
“布莱克当然卷入了男人、女人和他们的社会所组成的普通世界,但他一直固守他称之为‘想象’的永恒世界的非凡价值与非凡真实,实际上可以说他整个一生都极力企图看到这两个世界合而为一并将它展示给别人。”
二、不仅是诗人
布莱克生活在一个“愤怒和喧嚣”的时代。英国工业领先于全世界而飞速发展,这一方面使许多人遭受失业和贫困,另一方面也对文艺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排挤;而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相继爆发,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诗人们的叛逆意识,为19世纪浪漫主义的繁荣准备了条件。但是菲尔丁和哥尔斯密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学处于这两个波峰的波谷之中,诗人们普遍感到压抑和困惑,在抗争中,几乎都沉沦下去。“他(布莱克——笔者注)的时代洋洋得意地把绝大多数诗歌逼进忧郁的孤寂之地和疯人院里。”
作为一个诗人,布莱克在这种环境的压迫下不断成熟。一开始,他为革命的发生而感到欢欣鼓舞,显得乐观而坚定;但不久,现实使他处处碰壁,在外在世界里,他被打败了。但他并没有在精神上被打败,并没有使自己的诗歌变成宣泄不满情绪的下水道。他从外在的现实进入了心灵的现实,而不是进入了“忧郁的孤寂之地和疯人院”。这是使他区别于其他同时代诗人的伟大之处。革命对于他成了“仅仅是一种思想,一种内在世界、精神世界的东西”,他正是在这个世界里进行战斗:
把我那灼亮的金弓带给我,
把我那愿望的箭矢带给我,
带给我长矛,招展的云彩呀!
把我那炽热的战车带给我!
我不会停止内心的搏斗,
我的剑也不会在手中安眠;
直到我们建立起耶路撒冷,
在英格兰青翠而快乐的地面!
这种追求不但造就了他超越时代的诗歌,而且将他本人造就成了一个预言家。他从一个见过上帝和天使、见过灵魂升天的梦幻者,变成了用无韵体诗、用象征的语言来预言上帝退位、预言人类精神世界之变化的先知。
《天国与地狱的婚姻》
《亚美利加:一个预言》
《欧罗巴:一个预言》
……
是的,他所预言的不是外在世界的变化,而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未来。在他的一系列《先知书》里,他用一种奇特的语言,在200年前,预言了今日世界人们在宗教和哲学观念上的变化,包括性观念之解放(这一点,在本译诗集所选的《阿尔比恩的女儿们的梦幻》一篇中可以看到)。
因此,他不但是诗人,还是预言家,1927年“人人从书”版的布莱克作品集书名就叫《布莱克诗与预言集》。同时,他又是一位著名的雕刻家。他在世时主要以绘画和雕刻闻名。他最擅长的是铜版蚀刻。那是他表达思想、幻想和精神世界的另一种语言。他为自己的所有诗卷配上了精美的插画。并且,他曾应出版商之邀为许多著名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集作插图。
他在18岁时即为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作画。
他为诗人托马斯·格雷的《诗集》,为弥尔顿的《失乐园》和《复乐园》,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为班扬的《天路历程》,为华兹华斯的《诗集》,为但丁的《神曲》……作了大量想象力极其丰富的精美插图。
这些作品多为宗教题材。画面上有人,更有神;有正统宗教的神,更有他自己的宗教系统中的神。在他的笔下,它们的饱满、强壮、有时又是扭曲的形象,自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力量;它们所洋溢、所迸发的,是他的超凡的、然而有些怪异和疯狂的想象之美。扭曲、绽开、翅膀、飞翔、光、辉煌、升华……到底是什么?他表现的,正是他所赞美的,是力与美。
对于他的雕刻绘画创作,在他去世后一年,约翰·托马斯·史密斯说:“我坚定地相信,没有一个艺术家像他那样一点也不剽窃别人。”
他的诗,加上他的预言,再加上他的雕刻,便勾勒出了他的艺术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大致轮廓。
三、宗教、哲学和诗歌
他的作品所展现的,不仅是他的艺术世界,而且是他的精神世界。从现象上看,他的作品是诗歌、预言和雕刻三位一体;从本质上看,他的作品是宗教、哲学和诗歌三位一体。
保尔·沃本贝默在《现代主义》一文中说,布莱克“改变了哲学在许多诗人(包括叶芝)的诗歌中的命运”。
首先是哲学在他的诗歌中的命运。好像有人说过,哲学和诗歌永远走不到一起。但是,在布莱克的诗中,我们看到了哲学和诗歌的一个比较完美的结合。浏览一下对《天真与经验之歌》的全部评价,几乎找不到否定的语句。我们可以将《天真之歌》与《经验之歌》比较一下。
这两个部分许多首诗的题目都是相同的,至少是相互呼应的。它们都是非常质朴、非常具体(少数例外)的诗,然而对应的两首诗放到一起,却体现了两种对立的状态,或者,哲学。这种特殊的形式为诗与哲学的结合提供了契机,它使哲学进入了诗,又使诗避免了说教。
布莱克从不说教,从不显示自己的智慧,他并不认为自己有大的智慧。他将一切付诸想象与形象。他着魔似的沉溺于自己的想象,甚至似乎脱离了外在世界。他直接地追求内在性。对于诗人,这是一种大智慧。
这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革命。可叹的是它发生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先。相对于浪漫主义而言,它没有心理与情绪的夸张,没有过度的宣泄;相对于现实主义而言,它更为直接地诉诸事物的本质和心灵的真实而努力地挣脱现象的束缚。这正是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
然而布莱克并没有自己的哲学系统(在哲学上他受斯威顿伯格影响较深)。他有自己的宗教系统。这是又一种革命。他创造了自己的宗教系统。这个系统冠以《先知书》之名。大批评家诺思罗普·弗莱说:“布莱克的象征主义就其本原而言几乎完全是圣经式的。”这个系统便是布莱克的圣经。其代表作除了前面提过的作品之外,还包括本译集中选入的《塞尔书》《永久的福音》和其他许多作品,其中最主要的是他的长篇巨制《四天神》。这个集子里无法将它选入。这篇不长的序里无法、也无必要对它作详细介绍。
那4位“天神”是:尤利壬——理性,鲁法——感情,塔马斯——力量,尤索纳——心灵。布莱克认为,在“经验”世界里,人已经分裂为这4个部分,《四天神》的主要内容便是这4个部分之间的斗争,他企望这4个部分在永恒的理想世界中重新合而为一。这便是他的宗教的核心。仍然是“天真”与“经验”的问题。
在布莱克那里,没有诗歌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问题。一切是一体。从他的心灵出发,统一于他的诗与画。
我们是否想到了前些年很时髦的“异化”这个词?其实200年之前,它在布莱克那里就已经有了。不过,那不是时髦,而是一种痛苦,痛苦变成了宗教。在几十年之前,它作为布莱克对诗歌的革命之一,参与“改变了诗歌在许多诗人的诗歌中的命运”。
四、虎!虎!
只能说我们对布莱克了解得不够,不能说我们不知道布莱克。大概所有学过外国文学的人都知道他的《伦敦》,也许还有《虎》;并且,有些人知道《虎》的前两行,虽然知道的大多是中文意思。其实,这两行诗的所有中文翻译都是错的。而且错得要命。
我有意在此指出这个错误,同时想说,对布莱克的太少的翻译工作错得并不少。并且,想说文学翻译现在错得太多、太令人忧虑。但是这里不适宜再说下去。我只是企图通过纠正这个错误来进入一个重要的话题。
原文是:
Tiger!Tiger!Burningbright
IntheForestoftheNight.
对于知道英文的中国人来说,这似乎是两行太简单的文字。
译文一:
老虎!老虎!你金色辉煌,
火似地照亮黑夜的林莽。
译文二:
老虎!老虎!你炽烈地发光,
照得夜晚的森林灿烂辉煌。
译文一只不过没有完全把握原文,译文二简直是在把原文当打油诗了。
且不说“多”:“金色”是想当然加上去的,多了意思的“林莽”是为了押韵,“照亮”森林布莱克也并没有说。
只说“少”:少了burning(燃烧),少了Forest上f的大写和Night上n的大写。如果只是辉煌和放光,为什么布莱克不说shiningbright呢?如果只是黑夜的林莽或黑夜里的森林,为什么布莱克说theForestoftheNight而不说theforestinthenight呢?布莱克为什么要用大写?
少掉的恰恰是最关健的东西。
因为布莱克是在象征,而不是在比喻。所以,是“黑夜之林”,如同但丁的《神曲》,而不是“黑夜的林莽”或“夜晚的森林”。甚至,他用的是后来“意象派”诗人所说的“直接”的原则:不是“像”,“而是直接就是”。不是“火似地照亮”,而是“燃烧”:burn这个词并没有别的解释。这两行诗何妨译成:
虎!虎!光焰灼灼
燃烧在黑夜之林。
顺便提一下,这两行诗的音步,虽可读作44,但按照英诗格律,第二行诗更应看作43或42,因为没有重音不成音步;并且,严格地讲来,布莱克在这里并没有严格遵循格律。布莱克原本就是传统的反叛者和革命者,他的诗,有时是押韵严格,音步勉强,不成格(抑扬或抑抑扬等);他还开创了大量用无韵体写诗的先河。反过来,如果他过于拘泥于表层形式,他的诗如何能如此准确地表达他的灵魂,奔放不羁!同样,如果译诗过于拘泥于原诗的表层形式,如何能准确地表达原诗的灵魂!既如此,原诗的aabb韵脚译成abcc又有何大不可,较之于尽失原诗之精髓,更何足道哉!
我们从两行原文中窥见了布莱克诗的一斑。现代著名文学批评家沃伦在讨论意象、隐喻、象征和神话时说,“布莱克的‘老虎’就是一种神秘的隐喻”,这种隐喻“和人把自己投射到非人世界的隐喻恰恰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布莱克的老虎是“作者心目中一个幻觉的生物,既是一件事物,也是一个象征”。
他的确说得非常中肯。布莱克的“虎”是虎而非虎,但不能说是一种比喻。否则,比喻什么?它是一种象征。不象征什么。它“直接就是”。因此有人说布莱克是神秘主义者,但他的“神秘主义”不是正统宗教的神秘主义。他的隐喻既不是《圣经》里的隐喻那种类型,也不是玄学派诗人诗中那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隐喻。他是在象征。的确,布莱克的诗,尤其是后期的诗中,很少出现like这个词。但是,像《虎》这样完全是象征的诗并不多。象征,主要还是属于他自己的诗体宗教神话系统。
布莱克的诗质朴(早期的《诗的素描》除外)、清新,但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使他称得上大师的特点之一是,他的诗歌具有美妙的音乐性。前面提到过,他把自己的诗谱上曲子吟唱。其实,它们本身就是音乐。泰戈尔在《一个艺术家的宗教》中曾举他的《手稿》中的一首诗为例:
别试图吐露你的爱情——
那不能吐露的爱情;
因为那和风轻轻飘移,
默默地,不露形迹。
我吐露了爱,我吐露了爱,
我把整个的心儿表白;
打着冷战,万分恐惧——
唉!她启步离去。
她刚从我身边离去,
就有个旅人走过;
他默默地,不露形迹,
叹一声就将她俘获。
整首诗宛若一阵清风,“不露形迹”地轻轻飘过。再如他的《笑歌》就像一条“哈——哈——”地欢笑着奔腾而过的溪流;他的《致缪斯》就像一根游丝,缓缓游移着,直到最后才突然迸发出受压抑的情感。他的《虎》的节奏则是如此铿锵有力,如此明快,一泻到底,韵味无穷:
虎!虎!光焰灼灼
燃烧在黑夜之林。
什么样的神手和神眼
构造出你可畏的美健?
五、现代主义的预言者
我曾经用这个题目写过一篇文章(见《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在这里,已经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我只是觉得,这个题目很适合用来结束这篇不太合乎常规的序言——我不想把它写成一篇面面俱到的、论证式的论文。其实,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对诗人、对诗人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并且,似乎已经可以对诗人下这样一个结论。
也许,需要多说几句的是,从本质上,诗歌是生命的一个部分。诗歌使所有的人,无论他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相隔多远,只要愿意,都能在心灵上获得沟通。而布莱克,因为他的执着与“疯狂”,因为他的奇特的想象和预见,在许多诗人中脱颖而出,更能跨越时间和空间,与现代的诗人,与现代人相会——如果你愿意稍稍深入他的诗歌和他的精神。
现代人所体验的正是在“经验”世界中感到的压抑、惶惑和失落。
我们所体验到的现代文明的痛苦和失落,他体验得太早。他所寻求的答案,我们仍然在寻求。他的永恒的理想世界,太精神世界化了。也许,今天的物质世界太具有压倒精神的力量。所以,我们没有他那么执着和敏感。那是一件太痛苦的事。
但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并没有否定物质和肉体。相反,他所预言和赞美的,也许正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之一。
萧伯纳对我们说:“罗伯特·欧文、塞缪尔·巴特勒、奥斯卡·王尔德、尼采和其他人都是不自觉的布莱克主义者,据我所知,他们从来没有读过《天国与地狱的婚姻》。但是,大首领是布莱克,他是正在到来的时代的灵魂,道德革命的先驱,他写下了这个革命的圣经。”
在“这个革命的圣经”里,在《天国与地狱的婚姻》中,他让亚当来统治世界,让魔王撒旦出来反对上帝。他让魔王和地狱宣称:
生存的一个部分就是创造力的富有。
力是唯一的生命,来自肉体,理性是力之界限或外围。
力是永恒的欢乐。
生机勃勃就是美。
现在得到证实的事情曾经只是幻想。
山羊的淫欲是上帝的慷慨。
女人的裸体是上帝的杰作。
他还说:“够了!或许太多了!”
布莱克,诗人,“神圣的疯子”,象征者,神秘主义者,叛逆者,预言者。
对待这样一个诗人,是不敢也决不能轻率的。这个集子的翻译,是自1981年始,1983年年初完成初稿。其后15年中,又断断续续经多次修改。把它奉献出来,为的是不应被忽视的诗人,也为了诗歌的读者和诗歌本身。同时,也为了对外国诗歌的翻译和介绍。
我想,为了这样一些目的,花费断断续续十几年的劳动,是一件值得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