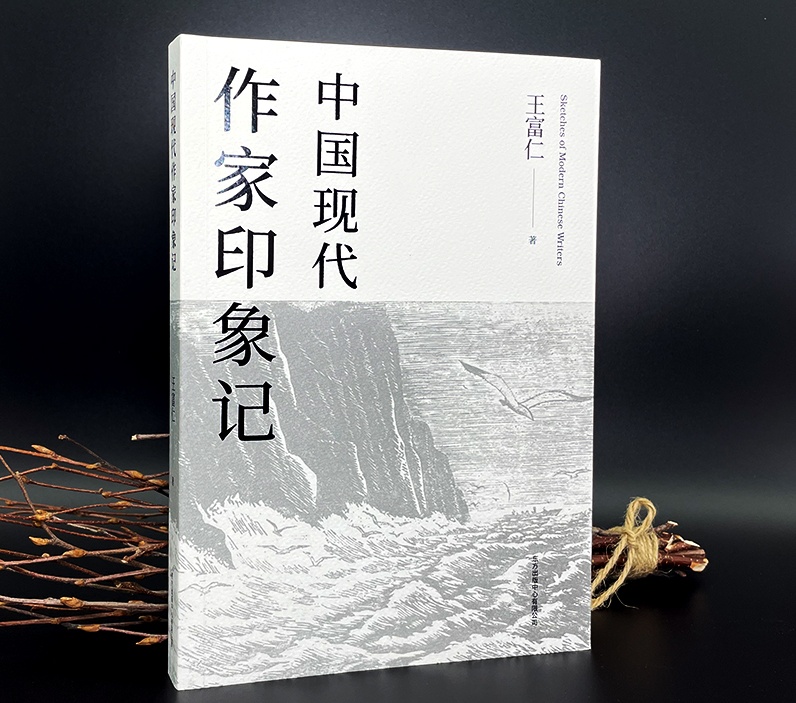
《中国现代作家印象记》王富仁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22年5月出版
【导读】今天(8日)在江苏卫视热播的《数风流人物》将迎来大结局,此剧让很多人想起2021年刷屏的《觉醒年代》,其中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随他迁入北京大学,众多优秀学者加盟,后期曾实施了轮流编辑的制度。参与《新青年》编辑和投稿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今天跳出电视剧的艺术性,向大家介绍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轮值编辑,他们在新文化运动史和五四文学中功过如何?
王富仁(1941-2017)是知名的现代文学史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在20年前曾素描了五四文学中的各色人物,这些学术随笔今天读来,依然形象、犀利且意味深长,起到还原文学史的作用。讲堂以他对蔡元培先生的印象记为首篇,看看这位新文化的伟大母亲,如何孕育了这些儿子们。

蔡元培:中国现代文化的母亲
他是中国旧文化的女儿而嫁给了中国新文化;而生育了“五四”一代新文化的奠基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
儿子长大成人,各立其业。于是社会上的人都与儿子们打交道,记着他们的名字,遂淡忘了他们的母亲。
我们记着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乃至刘半农、钱玄同,但蔡元培却不被现代文学界的人们所注重,但我们仍然要说:蔡元培——中国现代文化的母亲。
蔡元培是联系中国旧文化与中国新文化的脐带,是联系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桥梁。他是中国旧文化的女儿而嫁给了中国新文化;他在辛亥革命中长大成人,创家立业,而生育了“五四”一代新文化的奠基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
蔡元培是清末举人、进士,点翰林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是中国旧文化生的最小的一个女儿,但他后来却嫁给了西方文化,提倡西学,留学德国。他在辛亥革命中创家立业,获得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他不像他的儿子们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家立业的。
蔡元培(中间) 旧文化生的最小的一个女儿,但他后来却嫁给了西方文化,生育了五四新文化的儿子们
蔡元培的伟大成就在于他不是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有些人在社会上一旦有了一点小地位,便唯恐青年人起来占了他的位置,于是便站在社会的入口处,排斥一切新的,打击一切异己。他们成了没有生育能力的女人。在中国,这类女人太多太多,从而也便显示了蔡元培的伟大。
正因为出任了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才被接收到北京大学,陈独秀出任了文科学长;鲁迅在他的主使下进了教育部并随部迁往北京;周作人来到北京大学与蔡元培也有直接关系,后来又来了一个留学美国的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都在北京大学任职。试想,如果蔡元培是反对新文化的守旧派,他们怎能掀起偌大的浪,推起偌大的波。蔡元培就像一只老母鸡,伸开自己的双翼,在自己的身下孵化了这些新文化的鸡雏。
他的兼容并包主义是他的母亲的哲学。一个母亲不会只允许一个儿子生存,他要给每一个儿子一个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有人认为他是中间派,代表中产阶级的思想,这是因为人们忘记了他是一个母亲,不是一个儿子。母亲如若不是一个“中间派”,首先牺牲的便是最小而又最调皮的孩子。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因而也就有各种各样的哲学。有父亲,就有父亲的哲学,父亲的哲学是不能生育的哲学,父亲的哲学永远以自己为标准,排斥一切与自己不同的东西。母亲的哲学是能生育的哲学,它不以自己为标准,而从儿子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出发。父亲的哲学规范这个世界,母亲的哲学生育这个世界。儿子的哲学则既不规范这个世界,也不生育这个世界,而是寻找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使自己能自立于这个世界。
儿子大了,有的成了父亲,有的成了母亲,有的要自己规范这个世界,有的要生育新的一代。
母亲的悲剧在于:自己的儿子越伟大,便越是会遮住自己的身影,让人只看到儿子而不再看到自己;而自己的儿子越是渺小,自己在社会上越是处于显赫的地位。但这时她又会为自己儿子的渺小而伤心。
蔡元培的悲剧属于前者:他的儿子们太伟大了。他被遮在了历史的背后。
胡适:中国现代文化的剪彩人
胡适写了《文学改良刍议》,这个剪彩人一剪刀便剪到了应当剪的地方,偶然与否,你得承认他的这个历史功绩
要说起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谁也没有胡适高。中国现代文化是以白话文运动为标志的,全部现代文化都离不开白话文这个语言的载体,没有白话文的提倡,还谈什么现代小说、戏剧、诗歌和散文,还谈什么现代社会科学著作,还谈什么现代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文化离不开语言文字,中国现代文化是从文言文变白话文开始的。
但要从实际考虑,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几乎什么也没有做。《新青年》是陈独秀办起来的,北京大学文学院的这帮子人是蔡元培当校长时聚集或物色来的,较之后来的周作人、鲁迅,胡适在新文学的建设中并没有做更多的贡献。他只是一个娃娃,当时还在美国留学,像开玩笑一样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新文化的开创之功便落在了他的头上。
这使我想到了剪彩人。万事俱备,剪彩人拿一把剪刀,把彩绸一剪,建筑物才正式宣告建成,于是这个建筑物的落成也就以剪彩人的这么一剪为标志了。
但胡适这个剪彩人到底不同于实际的剪彩人。实际的剪彩人是预先知道往哪里剪的,而胡适一剪刀便剪到了应当剪的地方,不论是偶然也好,必然也好,你得承认他的这个历史功绩。
胡适照片:倡导白话文的《文学改良刍议》的功劳超过了其他费力所做的事
这里还存在着一个历史观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在艰苦中过惯了,总觉得应当把功劳记在那些费力最大的人身上,轻而易举得来的东西不值得我们重视。但历史满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它是以对历史影响的大小为准则的,费力大小不在它考虑的范围之内。要说费力,中国的老百姓一生辛辛苦苦,都比牛顿、爱迪生这类西方科学家费的力气大。
这样说来,不是太让人伤心了吗?我们辛辛苦苦一辈子,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我们现在的生存和发展,为的是我们现在的幸福与追求,为的不是青史留名。
人死了,还要什么“名”呢?
如此想来,我们给胡适一个相当的评价也就不是他沾了什么便宜了。事情是他做出来的,就记在他的名下,为的是我们认识历史,不是为了一个死去的胡适。
当然,胡适也做过很多费力的事情。他的《白话文学史》,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他的中国小说考证,他的《尝试集》,他的《终身大事》,等等,等等。文学史家似乎更重视他的这些贡献,岂不知这些全部加起来也抵不上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重要,否则在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不会高得过俞平伯和朱自清这类学问家兼文学家。
胡适后来也起了很多不好的作用呀 ! 但一个历史人物是不能折算的,他后来的不好的作用要以他的不好的作用来记录,不能从他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功绩中减出去。这正像一个学生做算术题,第一道题对了便得满分,第二道题错了便得零分,不能说第二道题做错了就说他第一道题做得也不对。中国人好算总账,算总账的办法不是历史研究的方法。
钱玄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扩音器
现在看来,这些言论未免失之偏激,但在当时的文化革新运动中,对动摇社会对它们的盲目崇拜心理,是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首先出面反对的是著名翻译家、桐城派古文大家林纾老先生。他在1919年写了一篇文言小说《荆生》,说是有三个狂悖少年,一为皖人田其美,一为新从美洲归国、能哲学的狄莫,一为浙人金心异。三人在京师陶然亭胡说八道,攻击中国的伦纪纲常,叫“伟丈夫”荆生听见,狠狠地揍了一顿,教训了一番。这里的田其美指的就是陈独秀,狄莫批的是胡适,而金心异则是钱玄同。可见钱玄同在当时影响之大,在林纾老先生眼里,他是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第三号人物的。
钱玄同为什么也受到世人的如此青睐呢?
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的作用,是扩音器的作用。他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声音提高了整整八度,从而扩大了它的影响。
钱玄同(中间)和鲁迅一起提出“要废汉字”的说法虽未被采用,但现代白话文却在中国社会上站稳了脚跟
胡适提倡白话文,要以白话代文言,人们并不以为然,认为是过激之论,是对中国数千年优秀文化和它的优美的语言形式的否定。但钱玄同跳了出来,说仅仅以白话代文言还不行,自来的中国汉字,都是宣扬孔学的三纲五伦的奴隶道德和道教妖言的,根本不能发挥新时代之学理事物。所以,要使中国不亡,必须尽废汉字,改用西洋文字。钱玄同此说一出,倒使胡适的以白话代文言成了折中之论。直至现在,钱玄同的说法虽未被采用,但现代白话文却在中国社会上站稳了脚跟。鲁迅后来说,中国多数人不主动求变,要是有人说要开个窗户,大家是不干的,但待到有人跳出来要扒房子,为了不扒掉房子,才允许开个窗户。在五四时期,钱玄同就是要扒房子的。
中国人是爱面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守旧者为了反对任何变革,把中国传统文化吹捧得昏天黑地。什么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了,什么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了,而对于中国的贫穷、落后、受帝国主义欺负的原因全然不提,一味以自我吹捧掩盖自己的失败。这使得五四新文化的倡导者不得不着重从中国贫穷落后的现实原因的角度解剖中国传统文化。一般说来,这种整体的把握方式并不意味着对一家一派的历史作用的否定(例如我们说中国古代是封建社会,并非说屈原、杜甫、李白、关汉卿、曹雪芹的作品是毫无价值的)。
但钱玄同则不但一般地讲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劣迹,还把矛头对准当时最受中国文人崇拜的《文选》和桐城派古文,说它们是“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是些文妖们搞出来的。同陈独秀说的“十八妖魔”(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同为抨击正统古文最激烈的言论。在现在看来,未免失之偏激,但在当时的文化革新运动中,对动摇社会对它们的盲目崇拜心理,是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的。
钱玄同的文风,是一种历史的需要,但也是一种性格的表现。这类性格,只有在和一种符合历史的潮流相结合,在革新倾向尚未被社会公众认识的时候,才显得特别可爱。一旦这种倾向已经被社会群众所接受,这种扩音器就有弊无利了。
在五四时期,是讲进化论的,认为老年人一般趋于保守。这话到了钱玄同嘴里,可就变了味道。他说:人过四十,就得枪毙。后来,钱玄同在政治上又趋于保守。北京大学要开唯物辩证法课,他仍用他用惯的语言形式声言:“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于是鲁迅写诗讽刺他说: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
《教授杂咏(其一)》
刘半农:俗人和雅人
从俗世中走出来,并因俗而干了一番了不起的社会大事业的人,非要雅起来又雅得有些勉强,仍被真正的雅人所小觑
在《新青年》的同仁中,你最不易敬重起来的是刘半农。刘半农可是以身殉职的,在现在是能上知识分子光荣榜的。他到当时的绥远热河一带考察方音民俗,染病回京,就一命呜呼了,死时才四十三岁。
对刘半农,作为一个音韵学家还是尊敬的,但未必尊敬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猛将的刘半农。其实对别的很多作家也有如此的表现。
问题出在何处呢?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脑子里,这个雅俗的界限是更重于实际的贡献的。在中国,同样一句话由不同的人说出来是不同的。你说不出他有什么贡献,但知道他很有“学问”,你就会尊敬他;你知道他有贡献,但却知道他没有太大“学问”,你仍然不会尊敬他。这个“学问”才是区分你尊敬他与否的最最重要的标准。
我们每个人埋在心底深处普遍存在的雅俗之分的价值标准,使中国知识分子大抵不愿干与实际社会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情,不愿研究与现实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课题,因为这是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倒是那些不必冒很多风险、连自己也说不清与社会人生有何关系的“学问”,更得整个社会的普遍尊崇。
刘半农的一生,便在这俗雅之间徘徊着。
刘半农,知名的音韵学家,所写白话诗《教我如何不想她》风靡五四
在《新青年》群体中,刘半农是最“俗”的一个。他的出身也最为低贱,父亲是一个地方的教师(大概有类于现在的小学教师吧)。他中学没毕业便当了小学教员,后来投奔革命军,在军队中担任文书。再后来便与二弟刘天华跑到上海谋生。初到上海,贫寒得像两个流浪汉,有时弟兄二人只有一身棉袍,冬天只能轮流出门。他靠卖文为生,成了一个鸳鸯蝴蝶派的小作家,后因投稿于《新青年》,与陈独秀有了联系,进了北京大学,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复杂的人生挣扎中一个人很难不沾染一点庸俗的、不尽如人意的习性和脾气,像刘半农作为一个鸳蝴派作家所遗留的一些思想情趣一样,但这类在实际人生中走过来的人也更少了知识分子的书卷气。鲁迅说他活泼、勇敢、直率,也正是《新青年》群体中其他人所较少具有的。彼此配合作战,有唱黑脸的,有唱红脸的,这台戏才唱得有声有色,正不必分唱黑脸的高贵还是唱红脸的高贵,因为唱的是同一台戏,什么角色都不可少的。
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是生活在中国社会上的,刘半农也是不能不受中国雅俗观念的影响的。不但《新青年》同仁中一些人有点瞧不起这个从中学肄业跑来的俗人,就是刘半农自己大概在一大群名流学者的中间也有些自惭形秽吧!他得把自己搞得雅起来,于是到伦敦、巴黎苦读了几年书,弄了个法国国家文学博士的头衔回来。这下,认为他“俗”的人可就大大减少了。
在西方,越是“雅”人,越是知识多的人,越得更多地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找出路。可在中国,越是与现实人生贴近的问题越显得“俗”,当自感其雅的时候,就自觉不自觉地不屑于管这些事儿了,反而与社会越离越远了。
在中国,“雅”与“俗”实际是和师与徒的关系密切相关的。孔子就是至圣先师,是管教训人的;俗人则是无文化教养的人,是被教训的对象,但他们也能提出问题,甚至说错了也不算丢面子。一个人是不是自感其雅,有一个最基本的方式,即看他说话和写文章主要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意见、与人交流呢,还是主要为了教导别人。前者把说话写文章的对象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人,后者则把对象视为自己教育的对象,视为自己的学生。前者因是代表自己说话,所以不怕说错,自己怎么想便怎么说。后者则要拣有确定结论的话说,不能叫人说他说错了的。后来刘半农写诗讽刺大学考生试卷中的错别字,鲁迅大不以为然,就因为鲁迅感到刘半农有些以雅人自居了。
其实,不论雅俗,只要与自己从事的社会事业无关,大可不必过问的。令人悲哀的倒是像刘半农这样从俗世中走出来,并因其俗而干了一番了不起的社会大事业的人,仍然有些自惭形秽,非要雅起来不行。而雅又雅得有些勉强,仍被真正的雅人所小觑。 整编:李念
作者:李念
编辑:李念
责任编辑:李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