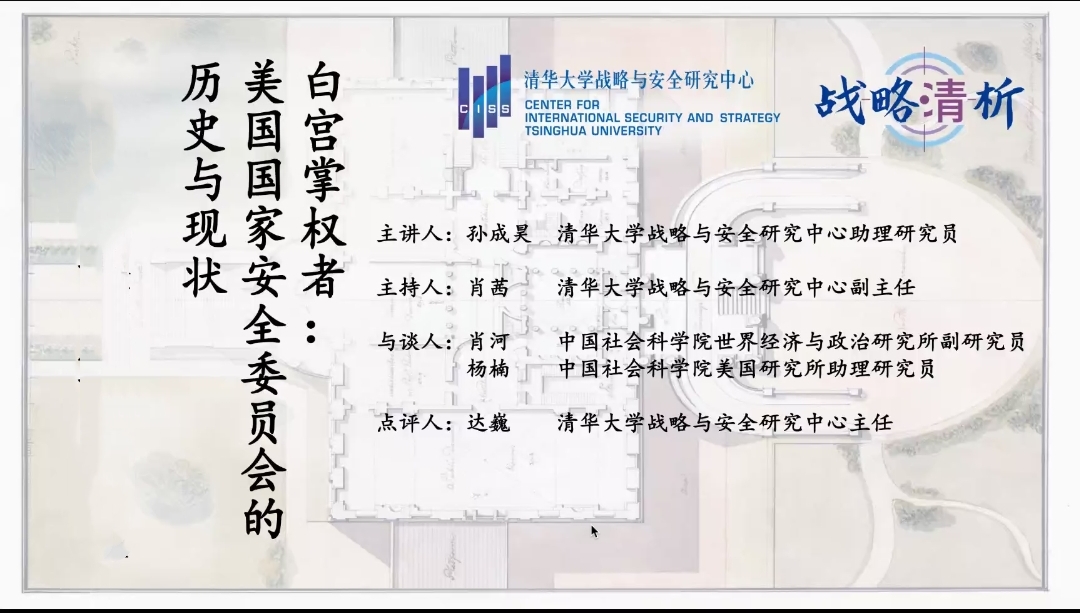
4月22日,清华大学“战略清析”系列论坛首讲主推青年学者阵容
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走向“单边主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会”)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它在对外事务中究竟有多大权重?梳理其“坦诚斡旋人”的定位与沿革,基辛格和尼克松为何能跳“二人转”?特朗普为何能挑起“宫斗剧”?奥巴马的“小圈子”圈住了谁?五彩斑斓的拜登团队又有哪些新动向?
日前(4月22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战略清析”系列论坛首期开讲,在美国“国安会”机制领域深耕的三位青年学者组成“三剑客”,以“白宫掌权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历史与现状”为题展开讨论。曾出版《白宫掌权者:国家安全委员会(1947-2019)》的主讲人孙成昊在历史沿革对比中观察“国安会”机制的角色定位和变革;与谈人肖河、杨楠则从大国博弈中理解制度变化。他们尝试下沉到微观视角,为国关人揭开白宫的权力“盖子”,为中美长期博弈增加知己知彼的权重,为对美外交战略政策制定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撑。

“战略清析”第一期在线上线下同步开讲,孙成昊作为主讲人分享“国安会”发展的三个阶段
坦诚斡旋人:变革中发展的国安会机制
何谓国安会?其定义为“协助总统整合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国内、国外和军事政策,使军方和其他政府部门及机构在国家安全事务上更有效地合作。”关键表述有三个,首先是为总统服务,其次是协调国内外的机制、军方与文职部门,第三是强调有效合作。国安会的成员最初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空军部长和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主席,此后也在不断变化。
身为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孙成昊指出,作为世界上首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47年成立之初,其职能在《国家安全法》中虽然相对模糊,但从历史发展来看,它经历了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里根以及老布什-拜登的三个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无论国内外时局怎样变化,国安会的“大安全观”宗旨、建立在三级委员会模式基础上的“坦诚斡旋人”定位逐步得以确认,而机构和体制在变革中走向开放和独立。

对国安会做深入研究的三本书:《白宫掌权者》,后两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国家不安全》均为戴维·罗特科普夫所写
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应冷战而生,初步走向机制化
冷战爆发带来的一系列安全问题是设立“国安会”的直接原因。而由于更担心国安会分散总统权力,杜鲁门(1945-1953)倾向于绕过“国安会”作出决策,直到朝鲜战争成为转折点。孙成昊分享,杜鲁门在朝鲜战争之前国安会召开60次会议中仅参加11次,而朝鲜战争后的71次会议仅缺席了7次。显然杜鲁门看到了国安会作为协调机制在发挥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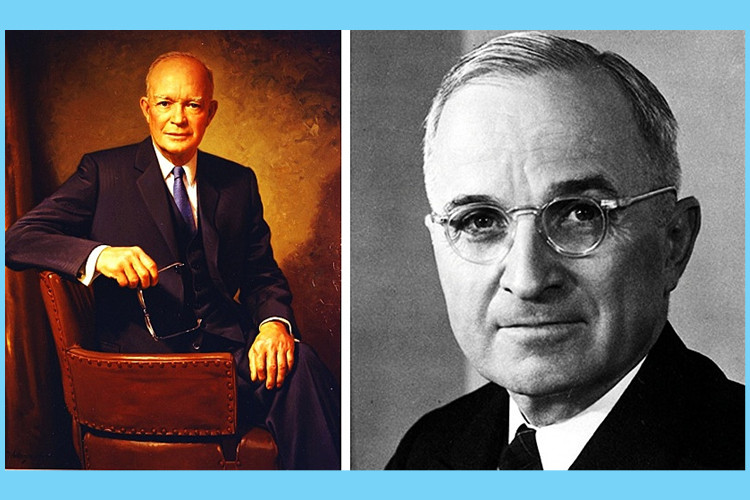
杜鲁门(右)和艾森豪威尔(左)对国安会的认识不同,但都推动着其朝机制化发展
到艾森豪威尔(1953-1961)任上,在他的主持下,新增了“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一职,由该职务总体负责,下设向上提供政策建议的计划委员会,和向下监督政策执行的行动协调委员会,这一组织架构如同“金字塔”的两个坡面,使得国安会初步走上机构化道路。虽然后期组织逐渐官僚化,单纯追求以量取胜的工作方式让国安会背上了政策“工厂”的揶揄,但仍然创新地开辟了跨部门协作的良好实践。
对这个阶段的国安会,一同合著《白宫掌权者》一书的与谈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肖河指出,国安会的诞生源于当时美苏两极对立,必须要从权力机制上产生一个供给性单位,可以搜集更广泛的信息以帮助决策者,而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一职,又可以负责敦促落实,此时,对国安会的考验是是否具备足够的能力和资源。“这种制度既是一般制度,又带有幕僚的协调作用,就具有双重属性。”
肯尼迪—里根:摇摆不定,由总统个人喜好决定
“从肯尼迪到里根,国安会发展进入了长期摇摆不定的年代”孙成昊的分享中,第二阶段的国安会的角色定位不断变化,原因也多种多样,主要是没有形成稳定机制。譬如肯尼迪(1961-1963)将臃肿低效的国安会从71人精简至48人,并着眼于处理眼前的危机。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在危机达到顶峰的2周内,国安会组织召开37次会议,前后70多人参加,其他机构人员纷纷加盟。到约翰逊(1963-1968)任内“国安会几乎被架空”。

基辛格(左2)在外交领域成就卓著,直接促成了尼克松访华,中美破冰
尼克松(1968-1974)时期无疑绕不开基辛格的亮眼表现。美国越战受挫后,内外交困,世界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基辛格抓住机会以“均势外交”策略积极“穿梭”取得斐然成果,并促成了国安会向长期战略规划的定位转型。
基辛格模式高光的原因是多重的。一方面,职位上的双重身份使得基辛格能够组建横跨8个部门的80人工作团队,决定了他对国安会的绝对领导。另一方面,在肖河看来,基辛格的德国移民、学界入仕的多重身份使得他和对华盛顿圈子不信任的尼克松一拍即合。同时,在孙成昊看来,基辛格高光背后也开创了危险的先例,“单靠个人能力是不可持续的,仍然需要有效机制来支撑”。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政治“二人转”虽然有特定功能,能制定高效的国家政策,但也遭到了华盛顿其他政治精英的腹诽。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和国务卿万斯充满了政治斗争,此为1979年2月14日,卡特(前中)在万斯(前右)、布热津斯基(前左)陪同下走向直升飞机。新华社/美联
此后的福特(1974-1977)基本延续了尼克松任内模式,到卡特(1977-1981)则再次削弱国安会地位,“温吞水”的性格使他无法调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和国务卿万斯的政治斗争。而在里根(1981-1989)任内,国安会负责人更是换了6任。动荡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混乱无序,权责不清的积弊呼唤着体制的变革。
老布什-拜登:三级模式框架稳定,安全外延扩展
作为基辛格的继任者,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老布什(1989-1993)任内开启了国安会发展的第三阶段。每届总统上任后都会对国安会的具体职责做出新的承诺,孙成昊介绍,譬如拜登政府的国安会除了民主党特色的服务中产阶级,应对传统挑战以外,新增了经济、健康以及环境的新挑战。新的问题在稳定机制中随着时局和体制变化不断涌现。
* Broker:稳定模式中的隐忧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基辛格团队崭露头角,服务过福特、老布什两届总统
“斯考克罗夫特模式”将国安会改制为一个由部长级、常务副部长级以及政策协调委员会组成的垂直链条,因此也被称为“三级委员会模式”。在孙成昊看来,三级协调的模式构成了跨部门协作的基础,而处于第三级的政策协调委员会更为重要,许多上层下达的战略需求将在这里生成具体有效的反馈,堪称“政策起重机”。
“此后的历届总统基本继承了这一模式,并以此为基础再做调整”。孙成昊介绍,克林顿(1993-2001)参照国安会模式另设国家经济委员会,部分法定成员“双肩挑”并行拓展了经济职能;小布什(2001-2009)则细分出涵盖6个区域方向和11个职能领域的政策指导委员会,因为9·11事件的重创,并新设了国家情报总监一职。
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楠看来,资本主义体制下,美国政府的企业式运营必然使得“Broker(中间人)”问题显现。“Broker能够在我和我的目标之间搭起桥梁”,但与生活中的各类中介类似,为了“达成目的”给出的信息往往会趋于非理性,而总统作为最终决策者需要为国安会提供的政策选项支付成本。
*难以平衡:广场型政治与宫廷性政治

奥巴马的小圈子,(从左至右)苏珊·赖斯,丹尼斯·麦克多诺,本·罗兹,多为越战后一代的1960后,出生竞选团队,为外交政策团队主力
国安会的机制在奥巴马(2009-2017)任内的战略决策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法定成员增加能源部长以外,还增设网络安全协调专员和网络安全办公室,国安会规模一度达到400余人。孙成昊介绍,奥巴马喜欢亲自充当“坦诚斡旋人”的角色来鼓励多方辩护并由自己最终决策,并且不忌讳频繁换将。虽然广开言路,但任期内仅副部长级会议高达4000余次,而参会人员权责不匹配也导致政策难落地,会议基本流于形式。此外,重用出身于竞选团队的苏珊·赖斯等人又形成了新的“小圈子”。
在杨楠看来,美国虽然以规则强调机制化,但“人情世故”仍然难以避免,“圈子文化”其实一直存在,某个幕僚的建议有时举足轻重。在对叙利亚要实施军事行动前,奥巴马和白宫办公厅主任麦克多诺在草坪上散步,后者的一席话让奥巴马收回了要军事打击叙利亚的既有决定。而基辛格似乎找到了机制和人情之间的巧妙平衡点,但与孙成昊看法相同,这种基于个人能力模式不可持续。
特朗普的个性导致其幕僚队伍非常不稳定,常常物是人非,此张照片中阁僚,在执政过半时已走大半
相较于奥巴马,特朗普(2017-2021)从上任起就不重视外交与安全团队的建设。人事的频繁调整使得国安会权力逐渐集中到国务卿蓬佩奥手中。“不守规矩”的个人风格也体现在很多方面,孙成昊举例,由于缺乏耐心,特朗普将每日简报改为一周2到3次,并且要求配合图片视频口头汇报。而决策也经常被国安会成员之外的非正式意见干扰,“最后推门进入者往往是总统决策的决定者”,这样的坊间说法广为流传。既强调内部竞争又要求忠诚度的决策风格让白宫“宫斗剧”轮番上演。
肖河分析,美国属于广场型政治,根据投票数量赋予权力,但白宫则属于宫廷型政治,总统是权力核心。而票选出来的总统权力高于非票选出来的白宫幕僚,而幕僚与总统的距离决定了国安会的负责人必须是受总统信任的身边人。
*多元化色彩:以复杂制度解决权力分配矛盾

女性、少数族裔、性少数,“五彩斑斓”是拜登团队特色(来自澎湃新闻)
“五彩斑斓”是拜登(2021-)团队的特色。在肖河看来,拜登政府“Colourful”的团队,符合亨廷顿对“现代性”的描述,相较于古代,现代政治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权力的分配中,设计复杂的制度则是为了解决权力分配的矛盾。
目前拜登政府除了恢复特朗普任内“基本坍塌”的决策定位和原则外,还就“印太”“Covid-19”等重要地区事务和议题设置“协调员”,也恢复了全球卫生安全和生物防御事务高级主任的职务。值得注意的是,本届政府中负责印太事务的人员多达20人,是欧洲事务的三倍。
具体到对华问题,“旋转门”机制使得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坎贝尔等主张美中全面竞争的鹰派代表利益集团活动频繁,肖河介绍,事实上,“拜登本人并不认为中国构成了巨大威胁”。在决策风格上,拜登经常推翻国安会幕僚的决议,比如力排众议要求阿富汗全面撤军。孙成昊介绍,在现任国安顾问杰克·沙利文看来,“拜登是一位有着反思精神的总统”。
打开盖子:复杂关系中看大国战略的安全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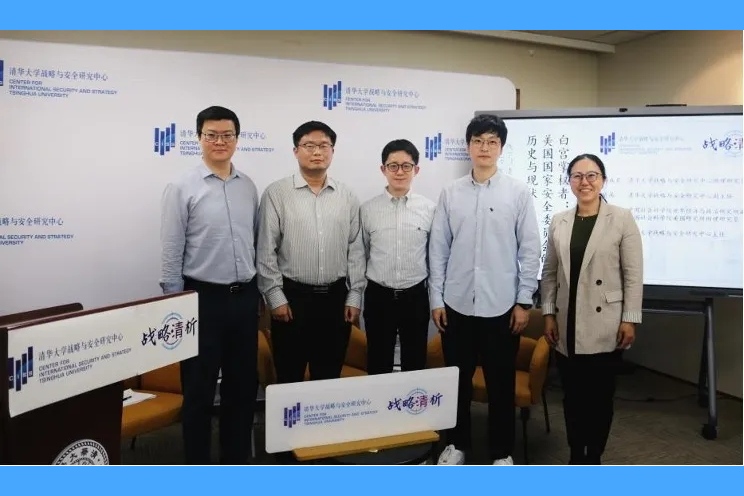
参与首期论坛嘉宾,(从左至右)达巍、肖河、孙成昊、杨楠和主持人肖茜合影留念
国安会的研究材料非常有限,孙成昊提到,一般本届政府不会公开太多内部信息,往往要等到任期结束从报告或者回忆录中寻找有用信息,这使得研究国安会变得不那么容易,但是一旦厘清国安会的决策机制,就受益颇多。
在互动问答环节,肖河和杨楠再次强调,国安会作为政策协调机制,并不能独立做出决策,因此国安会本身并不会对具体问题持有态度或底线,他应该持有中性立场,决策权力都在具体的人手中;事实上整个机制内外对同一问题也存在分歧。而对于美国频繁以“安全”为由高举制裁大棒,肖河认为安全问题其实没有严格的标准,但当今环境日益复杂,追求某领域绝对安全肯定会付出巨大代价,可行的方案是营造相对安全,即考虑可能的风险,而什么问题会成为安全问题,肖河认为,从国安会的行事看来,他们遵循于背后的推手从中能获得哪些利益。

达巍对话题和形式做总结,提出微观研究的重要意义
“许多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正如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总结时所说,没有完美的政策决策机构,战略的形成往往因时因势而变,相应的机制作为战略形成的微观存在,值得我们去不断观察。“把白宫这个盖子打开,看看国家机制内部如何运作”,有助于对比、反思体制改革的内涵和大国互动安全战略。
2月24日的美国新闻里有一则是,拜登就俄乌危机召开国安会会议。而此前也曾有报道称,在对华态度上,同在国安会的沙利文、坎贝尔和气候特使克里、商务部长雷蒙多意见相左。听完首场“战略清析”论坛,大家会豁然开朗,而让青年研究学者发声,对大话题见微知著,给学界和社会听友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中美长期博弈中,中国的智库也在开拓着研究视角,这仅仅是开始。
作者:毛鹰 李念
照片: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主讲者PPT、线上截屏
编辑:李念
责任编辑:李念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