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赵修义(文汇讲堂第96期嘉宾)
【导读】20日,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制定了《关于加强数学科学研究工作方案》引发关注。方案指出,数学已成为航空航天、国防安全、生物医药、信息、能源、海洋、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不可或缺的支撑。而今年新录取的大学生也争相进入人工智能能前沿科技专业。对此,讲堂分享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赵修义(文汇讲堂第96期嘉宾)回忆四十年前“科学热”的文章。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之际,增加全民科学兴趣和素养,培养献身科学的大学生,是民族复兴路上的必然选择。
《哥德巴赫猜想》点燃学习科学知识的热情,科普读物大受欢迎
闲来无事,整理藏书。理出了一大堆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的书。其中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出版物居多。边理边翻,把思绪带回了四十年前。勾起了许多记忆。突然发现,原来四十年前除了“萨特热”、“尼采热”之外,还有一个“科学热”。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都不会忘记,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的提出,激动人心的“科学的春天”的来临。诗人徐迟充满激情的《哥德巴赫猜想》,让陈景润这位蜗居斗室、连自己生活都不善料理却矢志不移埋头破解世界级难题的数学家,成了国人崇敬的偶像。套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他拥有无数的粉丝。由此带来的就是对科学知识的敬畏和对发现科学规律、发明各种新技术的科学家、发明家的崇敬,成为一代风尚。一度流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舆论被一扫而光。
最直接的一个效果,就是引发了国人学习科学知识的热情。科普读物成了畅销书,我自己也被卷入其中。比如,著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的许多作品,就在藏书之中。翻开其中一册《宇宙、地球、大气》一书的版权页,1979年第二次印刷的印数为329650。足见其发行量之大。想想,那时,大家收入不高,定价0.65元,大体相当于我这样的教书匠月收入的百分之一。月薪36块的青年人,也有不少投入到这场读书热之中。再翻下去,可以看到,许多地方都有铅笔划的杠杠和记号,可见都是认真读过的。其实在那个低收入的年代,没有多少人会为装点门面去买书。书是用来读的,这是当时的常态。大量发行的科普读物,涉及面极广,除了宇宙地球,还有从元素到基本粒子,生命的起源和人体及思维。科学史包括各门学科的发展史和涉及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宏大叙事( 如梅森的《自然科学史》、丹皮尔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都有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丹皮尔这本45万字的厚书,1979年重印时总印数达30500册之多。更加令人惊讶的是手头两本量子力学史话,第一次印刷的数量分别为10万和200410。

左:徐迟《哥德巴赫猜想》右:阿西莫夫《宇宙、地球、大气》
巴德斯等对科学的热爱和牛顿的谦卑引发读者崇敬之心
这一时期的科学读物中有关科学研究的方法、艺术书籍也有较大的读者群。我手头就存有《漫话科学假设》《科学与思考》《科学研究的艺术》等。其中影响面比较广的就是贝弗里奇的《科学研究的艺术》,1979年第一次印刷的时候,就达到152400册之多。打开这本封面被翻破的小册子,就可以发现,这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综合了一些著名科学家的经验和见解,结合自己的经验教训,用风趣的语言,通过一个一个科学史上的故事,将科学研究中做出新发现所需要的思维技巧——艺术,娓娓道来。
对并非直接从事科学研究的读者来说,比这些思维技巧更具吸引力的是,此书对科学研究人员、科学家的品格的描述。在作者的笔下,最基本的品格是两条——“对科学的热爱和难以满足的好奇心”。所以,尽管科学家很少因自己的劳动获得大笔金钱,但是新发现带来的激动是科学家最大的报酬,人生最大的乐趣。
作者引用巴斯德和贝尔纳的话说:“作出新发现时感到的快乐,肯定是人类心灵所能感受的最鲜明而真实的快乐”。对科学的热爱,带来了极其可贵的德性——完全的诚实。“从长远来说,一个诚实的科学家是不会吃亏的,他不仅没有谎报成果,而且充分报道不符合自己的观点的事实。道德上的疏忽在科学领域中受到的惩罚要比在商业界严厉得多”。
这种诚实,还带来了科学家心灵深处的谦恭,深知比起广阔的未知世界,他们的成就只是沧海一粟。牛顿暮年的话——“我不知道世人怎样看我,但在我自己看来,我只是一个在沙滩上玩耍的男孩,一会儿找到一颗特别光滑的卵石,一会儿发现一只异常美丽的贝壳,就这样使自己娱乐消遣;而与此同时,真理的汪洋大海在我眼前未被认识、未被发现”。——就是最好的佐证。
贝弗里奇笔下的科学家的品格让经历了“假大空”的国人,耳目一新。心中不由得升起对科学家由衷的崇敬。科学家不仅因为他们的科学发现给人类带来的福祉而受到崇敬,而且因其品格的高尚而受到敬仰。科学家的传记,他们对人生的感悟,都成了更广大读者关注的热点。诸如《爱因斯坦谈人生》之类的书籍,也随之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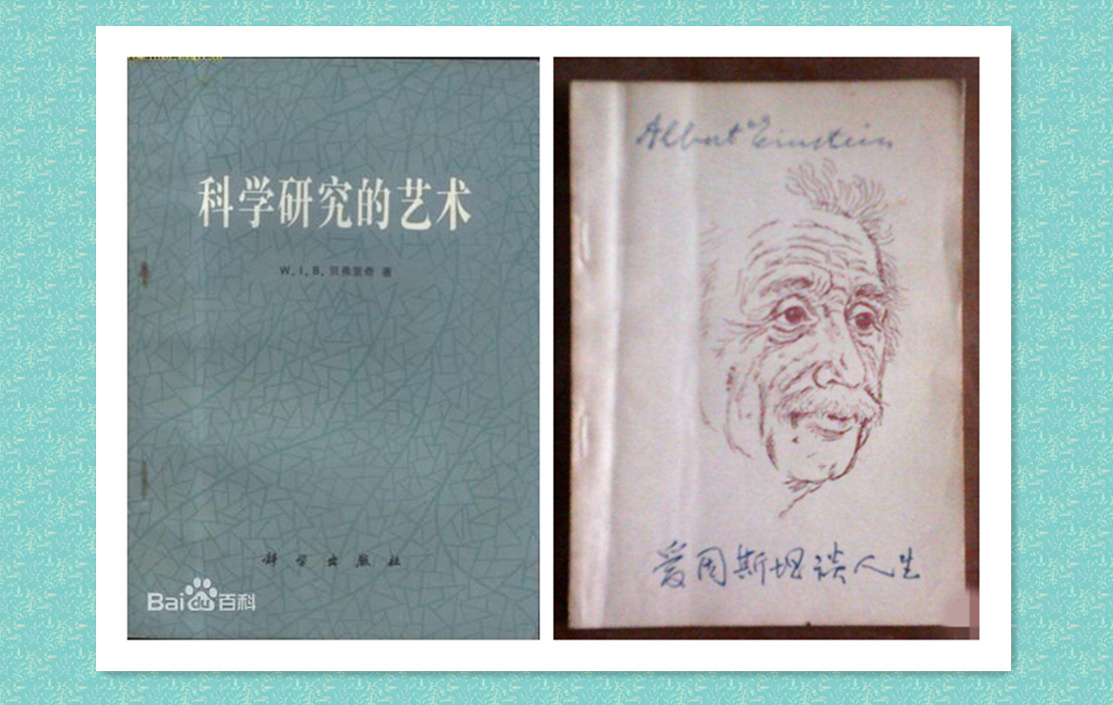
左: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 右:海伦·杜卡斯《爱因斯坦谈人生》
从对科学方法的推崇到延伸到决策者有兼听则明的座右铭
对科学家的崇敬和对科学的敬畏,带来了对于科学方法的热衷,科学方法的书籍和刊物蜂拥而起。社会科学界有些同仁开始尝试将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和学说(如熵定律、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等)引进自己的研究领域。更具时代特色的是科学方法引起了广大的实际工作者的兴趣和关注。最具开拓性的是“科学决策”这一概念的提出。沪上的四位学者夏禹龙、刘吉、冯之浚、张念椿,写了很多文章阐发这一概念,成为舆论场的热点。他们一度被戏称为“四条汉子”。
1982年他们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的《论决策科学化》一文,首先论述了决策科学化的必要性。文章在对科学决策的内涵和类型作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可供操作的“决策程序”,列出了发现问题、确定目标、价值准则、拟制方案、分析评估、方案优选、试验证实、普遍实施等八个步骤。文章还强调要实现科学决策,需要特别重视不同意见和民主讨论。指出不同意见会提出更多的可供选择的方案;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可以取长补短,可以激发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作者认为陈云同志以下的论说,应该成为决策者的座右铭:“领导干部听话特别要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容易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事物是很复杂的,要想得到比较全面的正确的了解,就必须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经过周密的分析,把它集中起来。”

当年科学学所四位学者:一排右一夏禹龙、二排右三刘吉、二排右四冯之浚,三排中间张念椿
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体现科学思维变化,人工智能、机器思维新事物出现
“科学热”还相当集中地体现在哲学界,最典型的就是科学哲学成为热门。当时有的用“自然辩证法”,有的用“科学哲学或科学技术哲学”来称呼这个分支学科。所关注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科学技术的新进展及其给哲学提出的新问题;另一个是国外的科学哲学在当代的新进展。
就前一方面而言,有一部分论者关注的是诸如“宇宙大爆炸”之类的新学说,对写在教科书中的哲学原理提出的挑战,而多数的论者更加关注的则并非原有学科中的新进展,而是反映科学的整体化趋势的“新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科学哲学研究者认为这才体现了科学思想的根本性变化。他们对于“新三论”的内容及其相应的技术应用领域(诸如系统工程、通讯工程、控制工程)引介,对其产生的背景的分析,使大家知道了“新三论”与电子计算机发明和推广息息相关。这些新科学的介绍让国人大开眼界,于是电子计算机、电脑、人工智能、机器思维等以前闻所未闻的新事物、新概念成为舆论场上的热点,也成了公众追逐的新知。还有一些论者,就科学发展到当代该如何分类,科学与技术之间该如何把握,提出了各自的见解。比较流行的一种看法是需要将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加以分疏。基础科学着重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则着重于解决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拓展了人们的眼界,也为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落到实处做了铺垫。

《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浅说》是杨春时、邵光远、刘伟民、张纪川编著的一部哲学科学著作
国外科学哲学成为热点,大学生讨论“我们能否贡献一个爱因斯坦”
对国外科学哲学的关注,也是那个年代的热点。刚刚打开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在起步之初,就把现当代的科学哲学作为一个重点。在1979年召开的第一次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上,卡尔·波普的证伪主义和三个世界的学说,就受到了与会者的关注,会后学界就出现了“波普热”。此后,以“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动力学”为重点的科学哲学一度成为读书界的热点。邱仁宗先生编著的系统介绍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和近二三十年来的演进的《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动力学》一书,第一次印刷就达四万册之多。
深受青年人喜爱的还有赵鑫珊先生的散文,可视为科学热中开出的一朵奇葩。汇集他数十篇文章的两本书《哲学与当代世界》《科学·艺术·哲学断想》一直摆在我的书架上。富有诗人气质的作者,用充满激情的文字,极其丰富的哲学史、科学史、艺术史的知识,结合著名科学家的故事,将科学、艺术和哲学的关系娓娓道来,使人对科学的理解拓展到了一个新的维度,原来科学与哲学、艺术是紧密相连的。许多大科学家,不仅有丰厚的哲学素养,而且对宇宙天地人生有自己的哲学思考。许多科学家都热爱艺术,尤其是音乐。在音乐中找到精神家园,也从中激发出科学创造所必须的想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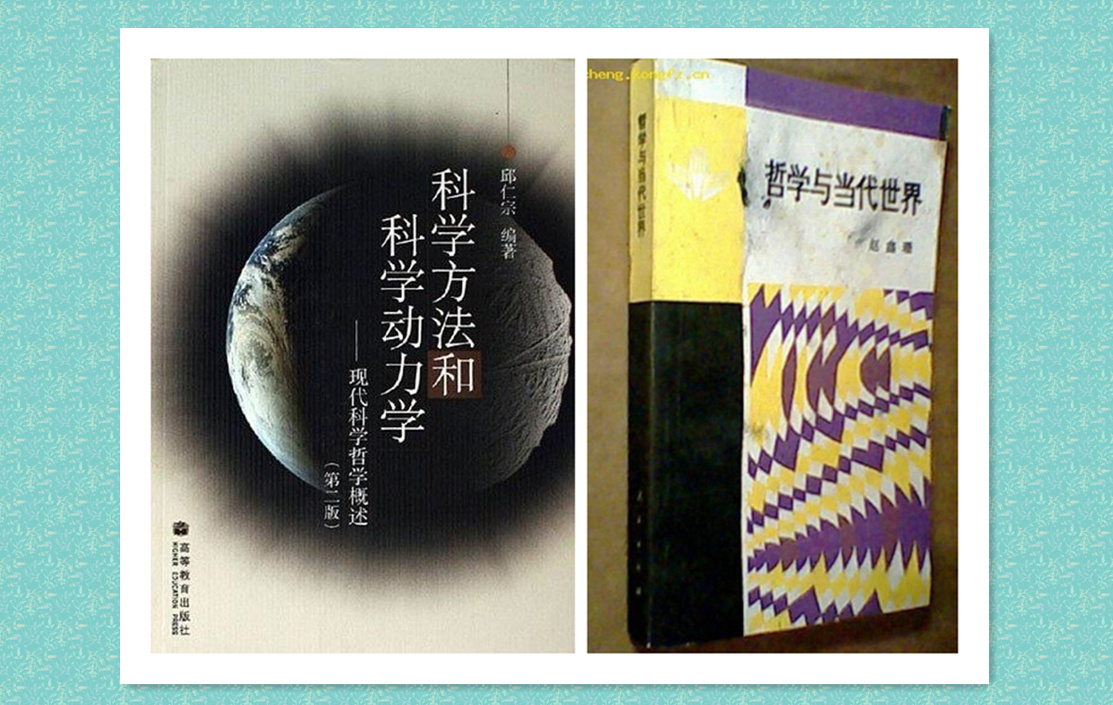
左:邱仁宗《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动力学》 右:赵鑫珊《哲学与当代世界》
最能反映这个时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的一篇,专门讨论大学生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能否贡献一个爱因斯坦?”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足以反映一代青年的宏大志愿和满满的自信。
与1956年短暂的“向科学进军”的热潮相比,此番“科学热”持续数年。但同任何的热潮一样毕竟为时不长。但它确实存在过,它留下的积淀至今还在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它所折射的时代,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之所以值得怀念,因为这股科学热多多少少反映出恩格斯所称颂的伟大理论兴趣——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都照样致力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开始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
来源:《探索与争鸣》《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修义
编辑:袁圣艳
责编:李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