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的意义与意义的边界》活动海报
即使是没受过严格训练的爱乐者,你也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听到现场弹奏,即使是不熟的曲子,也会因为某个音的不和谐而判断出了错音;一首新歌,有时候听到上句,就能与作曲家心有灵犀似地猜出下曲的走向。
这是因为音乐是有“语法规则”的,因而也就具有意义。
但如果你对古典音乐有所了解,也许会质疑到为何专业人士也很难判定贝多芬的《降B大调第29钢琴奏鸣曲“槌子键琴”》第一乐章发展部的结尾一处重要的音符应当是还原A音还是升A音?肖邦的《第2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呈示部在错误的地方反复,居然近二百年来少有人察觉?美国著名钢琴家、音乐学术大师查尔斯·罗森在新书《意义的边界:三次非正式音乐讲座》中有明确的回应:“音乐就是常常在无意义与不明确的边缘徘徊的”,因此很多人在听习惯了以后,就算是“将错就错”。
那该如何理解音乐的意义,又该如何理解罗森所言的意义的边界呢?日前,著名音乐学家杨燕迪与《意义的边界》的译者、华盛顿大学古典学博士罗逍然,以《音乐的意义与意义的边界》为题在沪上展开了一场关于查尔斯·罗森的跨时空讨论。

杨燕迪与罗逍然对谈
贝多芬的地位是原生性的,而巴赫的地位是被建构出来的
也许很多音乐爱好者都有这样一个困惑,古典音乐是不是就是过去的流行音乐?其实并不尽然,如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如今在中国的演出频率比它刚刚问世30年之内的演出频率都要高。但这就涉及到了另一个疑问,既然在当时像《费加罗的婚礼》这一类的经典作品在当时并不受欢迎,那么这些作品与它们的作曲家在音乐界的重要地位又从何而来的呢?罗森通过引用大量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的文学家、评论家、音乐家等文化界重要人物对当时的重要音乐家与音乐作品的相关评述与回忆,证明某部音乐作品的经典地位,往往是在首演时就已在听众心目中奠定了,而这种地位并不受这部作品演出次数的影响,也就是说,即使当时的人们最爱听的并不是这部作品,但人们往往依然承认它是绝对的经典。
杨燕迪对罗森的这一观点进行了补充,他认为罗森是针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音乐学”认为作曲家的声望是后天建构的这一观点进行的回应。如“新音乐学”的一位女学者迪娅·德诺拉(Tia DeNora)就认为贝多芬并没那么优秀,之所以后来具有这样高的经典地位是后人不断把他建构起来的。而罗森则反驳道,经典音乐与作曲家的地位是与生俱来、不为时代所改变的。杨燕迪在这一观点上对罗森表示赞同,尤其是最顶尖级的作曲家和作品的地位,不是后人能随便左右或来评判的。
但杨燕迪同时指出,也有完全相反的例子,如巴赫的地位完全就是后人建构起来的,特别是到20世纪越来越加强,可以说在20世纪巴赫的地位是没有人可以撼动的,巴赫的价值是19世纪至20世纪的某种事后追认。可以说,这一观点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作曲家与其作品的经典意义是需要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才能深入理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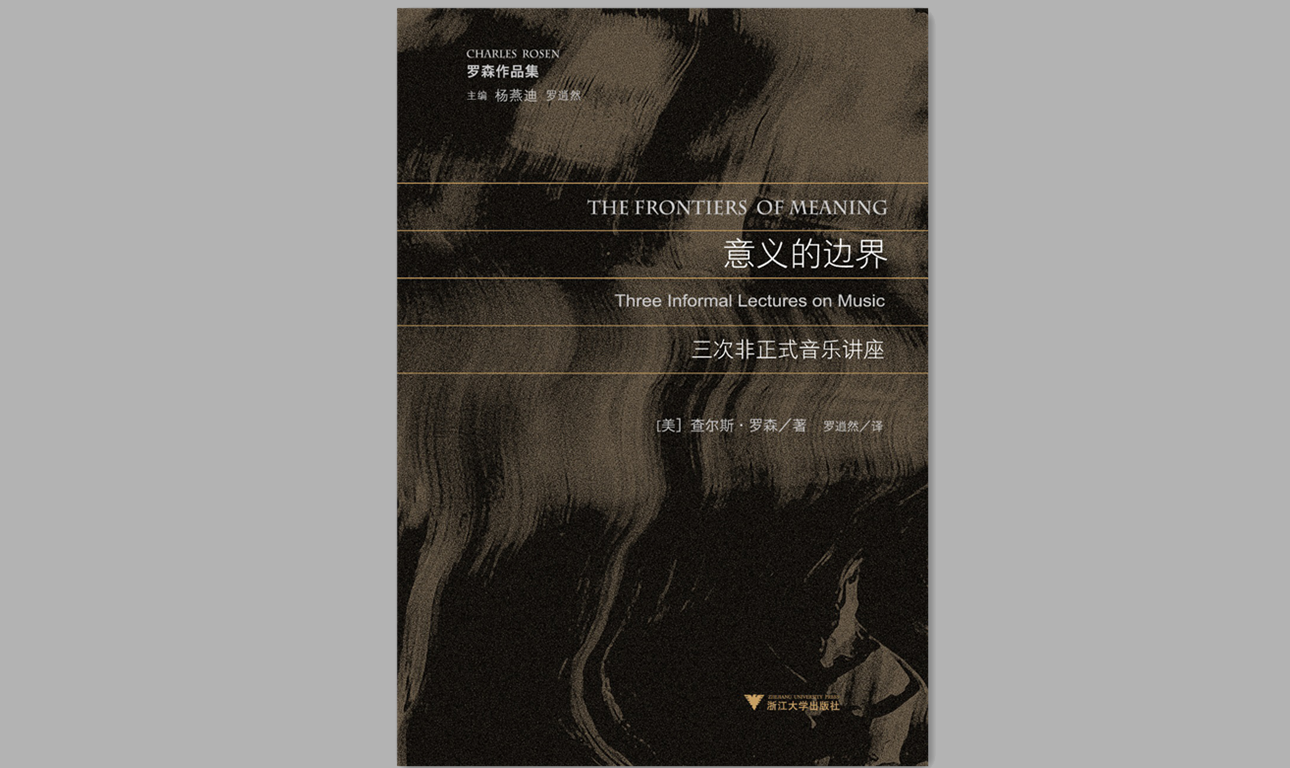
《意义的边界——三次非正式音乐讲座》(The Frontiers of Meaning: Three Informal Lectures on Music)的原书出版于1994年。罗森在其中讨论了什么是音乐的意义,这种意义与语言或绘画所承载的意义有何不同。
“好的音乐分析在你看不到风景的时候帮你指出来”
作为普通音乐爱好者应该如何发掘音乐的意义呢?《意义的边界》为读者提供了进入音乐的方法论启示。
杨燕迪表示,音乐是某种感性的语言体系,但很难看到像文学理论界或者美术理论界那样构建起多个完整而丰富的理论阐释体系。以罗森为代表的欧美音乐批评家能够针对一个艺术作品,把它最突出的艺术特征抓住,用清晰的语言把它说出来,这是非常值得借鉴与学习的。
只用形容词永远不能够真正抓住音乐本身
谈到用清晰的语言表述音乐特征时,罗逍然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在描述音乐的时候,使用形容词好像是一种引诱,是把作者自己的观点强加在读者身上。
杨燕迪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应,他指出主要在于形容词永远不能够真正抓住音乐本身,因为形容词是非常表面的。当然在形容音乐时是一定不可能脱离形容词的,我们总归要概括音乐的情感为快乐或是悲哀,但仅用形容词又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纯音乐,同一首音乐,每个人的内心感受都不一样,描述情感会带入自己的经验,这个经验每个人又是完全不同的。形容词对音乐而言太空洞、太宽泛了,音乐需要非常具体的描述,因此需要像罗森一样要下降到音乐的技术语言去把它说清楚。罗森也有他的情感立场,但他不会太多卷入自己在听音乐时的那种遐想,而是尽可能的落实在谱面上。可以说,乐谱是音乐中唯一一个真正客观不变的东西。
在技术语言的层面,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实际上运行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技术语言体系。就罗森而言,他对于古典音乐的表述得最好,这也与古典音乐的调性语言有一整套非常成熟的形式语言有关。而现代音乐,尤其是20世纪的音乐的形式语言就没有这么容易被清晰的表述出来,这不是因为它的形式不成熟,而是它的这套语言不共享,每个作曲家或音乐批评家心中有一套自己的音乐语言体系,所以进行交流就会产生困难。

莫扎特手稿
旋律不可以被分析,但是可以被感受
在音乐学院里,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旋律究竟是不是音乐技术的一种?音乐技术的四个方面是和声、对位与复调、曲式,以及配器(管弦乐队的写作技术),但却没有系统的旋律课。可以说,旋律到现在为止都是非常神秘与玄妙的,一个旋律怎样产生、为什么好听,即使是作曲家本人也无法回答。旋律好像是自然流露的,无法被教授,于是它也是无法分析的。总体来说,旋律没有形成一整套像和声分析、曲式分析这样的规范。
但罗森提供了理解旋律的某些方法,同时又不破坏对旋律的直观感受。
他在《古典风格》中专门分析了莫扎特的《C大调钢琴协奏曲》K.467的第二乐章,这本是莫扎特最优美的旋律写作范例之一。
对于作曲家为何构思这样的旋律,这个旋律中每个乐句之间的组合,旋律中为何会突然出现大跳等细节,都从音乐史和音乐分析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他将整个旋律视为一个物体一样去观察它的结构,如他对其中出现的三小节乐句结构和五小节乐句结构进行了解释(这在古典音乐中相当反常),又对主题旋律的高潮点布局以及整体上的对称感进行了透彻而到位的分析。
而在《意义的边界》这本书中,罗森在最后一章末尾对舒伯特的旋律写作进行了极为精彩的分析点评,让我们进一步看到《致音乐》《你是安宁》和《降B大调钢琴奏鸣曲》D.960这些似乎大家都已很熟悉的作品中,作曲家的旋律写作旨趣和艺术品格究竟是什么。对此,罗逍然不禁感叹道:“所以分析不会给你煞风景,而是在你看不到风景的时候帮你指出来。”
乐谱原旨与话题理论的对抗:不同维度下的音乐意义
由此如何理解音乐的意义?杨燕迪指出音乐学界主要有两个思考方向:
一是谈论音与音之间的联系,认为音乐有一整套形式语言,作品分析、音乐分析、曲式分析这些学院派的音乐研究主要就是在处理这样的技术语言的意义。
另一个方向是把音乐与音乐之外的世界关联起来的意义,比如音乐是否表达了某种时代的气氛、某种人的情感方式。有音乐学家将这两种意义分别称之为“绝对意义”(the absolute meaning)与“指涉意义”(the referential meaning)。
罗森在他的著作《音乐与情感》与《意义的边界》中表达了他对音乐的“绝对意义”的重视,书中具体说明了音乐是如何通过其本身的形式和语言规则传达出自身意义:在某一部作品中,通过不协和音带来的张力与协和音带来的张力释放、不同动机在不同时间点上的衍化或蜕变,在作品内部建立起这部作品、作曲家、音乐风格所专有的意义框架,只有在对新作品与新风格的不断熟悉与习惯中,才能获得音乐的意义。
罗逍然强调了罗森研究的最大特点,他始终是以乐谱为绝对中心,通过认真分析乐谱,从每一个动机或每一组和声等最小的细节出发,力图在读者面前建构起音乐作品的某种图景。他作为一名乐谱“原教旨主义者”,非常重视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严格的语法规则。罗逍然以一个极端的例子向现场听众进行了解释:贝多芬或古典风格的任何一位作曲家的任何一首作品,如果它的最后一个音或和弦不响或者不弹出来,就会是非常严重的语法问题——因为音乐最终没有得到解决,就好像我们说话没有说完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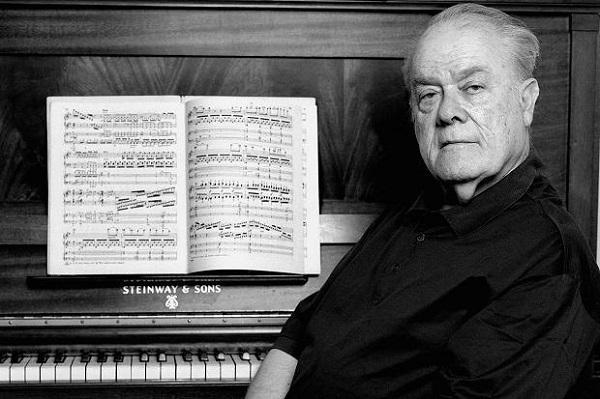
杨燕迪对罗森的评价是,“对音乐艺术百科全书式的掌握了解以及他对西方文化传统各类知识的博闻强记,在西方音乐界和文化界早已成为传奇”
虽然罗森十分强调音乐的形式规则及其带来的意义,但他对音乐作品的过度解释保持着十足的警惕:“很多内容会在互无关系的作品中反复出现,而为这种反复出现的内容加上意义,有时甚至是非常具体的意义,那就是走向荒谬的最后一步了。”
罗逍然指出,罗森是在回应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后来成为西方音乐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的“话题理论”(Topic Theory)。话题理论认为,音乐与语言类似,是特定文化中形成的特定的符号体系,某类动机、某种节奏型或某种曲式,甚至某个组成音乐作品的元素都有可能是一个指涉外部世界的音乐符号,这种研究方法是将音乐与更宽广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比如老施特劳斯的《拉德茨基进行曲》、罗西尼在《威廉·退尔》序曲的终曲部分、海顿的《D大调第93交响曲》的小步舞曲乐章等运用了最早起源于作曲家在创作中对军号声的模仿的音乐符号。
罗森与话题理论的两种研究方法所展现的恰恰是音乐的两种不同维度的意义:前者专注于音乐本身的结构与语法规则,而后者所重视的则是如何将音乐正确地还原到历史与文化背景之中。
面对这两种互相对立的选择,罗逍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为喜爱音乐的读者,我们并不需要做出取舍,不同的研究方法为我们说明了音乐在不同层次上所含有的意义。如果能够兼容并包,那么我们对音乐的理解一定会比仅仅抓住一种理论、从单独一个出发点考虑要深入得多。”
杨燕迪也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他认为罗森在美学立场上是比较保守的,而音乐让人神往恰恰是因为作曲家们能够把音乐内部的一套封闭的语言运作与外部世界的指涉和象征恰当地联系起来;聆听和理解音乐最好的状态应该是平衡的状态,一方面要理解音乐内部的语言运作的规律,另一方面,也要把音乐与人的生活,包括与作曲家的生平、时代、个人、甚至是听者自身的生命感受连接起来。

《费加罗的婚礼》(LeNozze di Figaro)是莫扎特最杰出的三部歌剧中的一部喜歌剧,完成于1786年,意大利语脚本由洛伦佐·达·彭特(Lorenzo da Ponte)根据法国戏剧家博马舍(Beaumarchais)的同名喜剧改编而成。
查尔斯·罗森为我们现今的音乐学与音乐学子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榜样,他的文字表述非但没有将读者、包括普通音乐爱好者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感觉,恰恰是以一种邀请加入的态度在引导读者进行更深入的音乐探索,这不仅是一种能将音乐特色清晰表现出来的语言能力,更是一种开诚布公的学术态度。在讲座的最后,杨燕迪与罗逍然都鼓励大家在阅读罗森的这些音乐批评时,一定要跟着去听相关的音乐,网络时代为音乐爱好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爱乐者们更要珍惜这一机会去感受音乐、珍惜音乐。
作者:夏佳丽
编辑:周俊超
责编:李念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