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威廉·麦克尼尔
【导读】麦克尼尔的学术如一条河流,《竞逐富强》就是河上的浪花一朵。纵而观之,《西方文明史纲》(1949年)、《西方的兴起》(1963年)和《欧洲史的形成》(1972年)是他谱奏的“西方文明三部曲”。这之后,他推出《瘟疫与人》(1976年)和《竞逐富强》(1977年)。二者堪称姊妹篇,又可视为《西方的兴起》的续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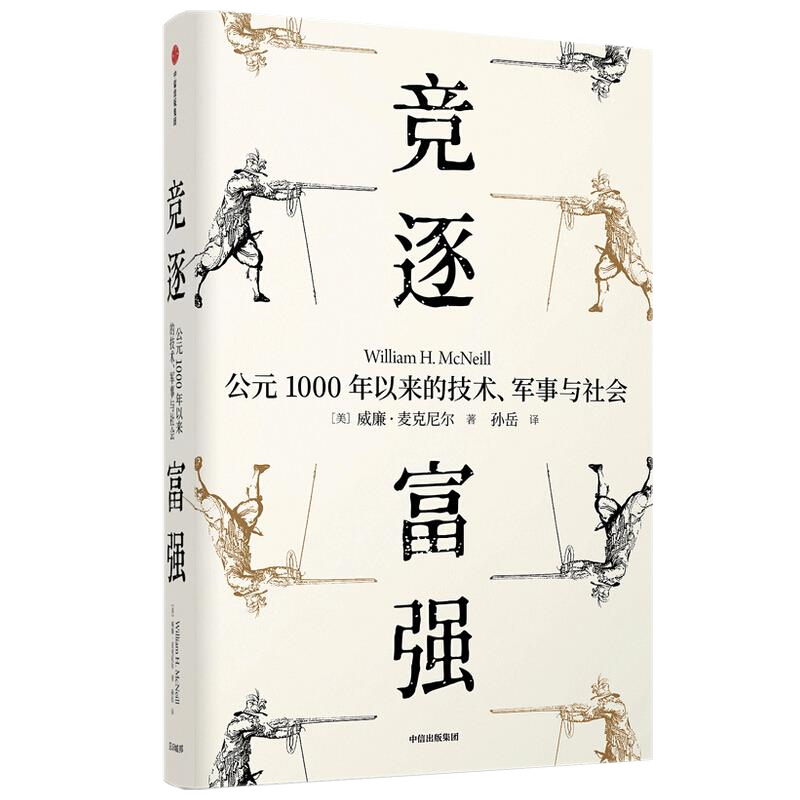
▲ 《竞逐富强》,中信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汤因比在天庭之上,麦克尼尔在尘土之间
考察威廉·麦克尼尔的知识背景,西方谱系是一条悠长的河流。在他以前,有奥古斯丁式的基督教普遍史、启蒙时代的人类进步法则、康德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兰克的民族-实证主义范式以及维多利亚自由观。在他左右,涌动着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形态论、鲁滨逊的“新史学”和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这一谱系,对麦克尼尔来说,是他不可选择又必须有所选择的史学遗产。
麦克尼尔揭示了 “世界史”要义,其成名著《西方的兴起》被视为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标志。该书检讨了启蒙运动以来盛行的以民族国家为认识单位、以西方为价值规尺的历史写作传统,展现了“西方兴起”背后的全球景深和历史合力。反对“西方中心论”者不止麦克尼尔一人,但对 “文明多元论”者,他却并非一概苟同。比如,麦克尼尔赞赏汤因比的“文明”范型,但二人分歧明显:汤因比首先是哲学家,或者说是哲学家中的历史智者,他那思辨的历史哲学总是在天庭之上藐看万物,而麦克尼尔则钟情人间烟火的趣味,始终“在尘世的土地上挖掘”,渴望理解形塑人类生活的各种物质能量,极力发掘着技术、贸易和生态等历史要素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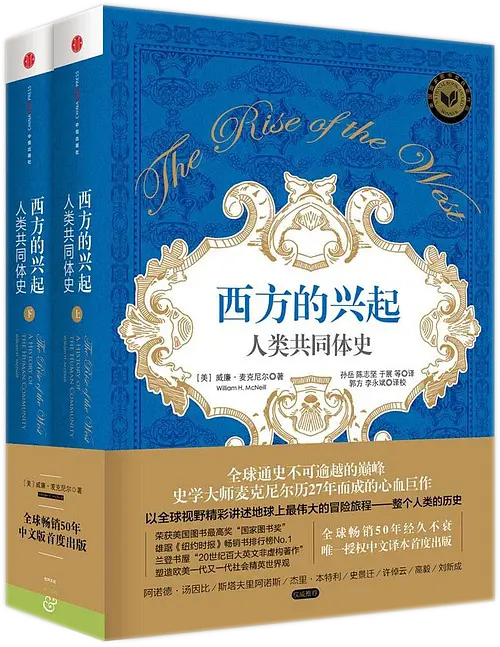
▲ 《西方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15年1月版
然而,与其他秉持实证原则的史家又有不同,麦氏对于历史经验的重视另有深意。试看他对“新史学”的批判。1919年,鲁滨逊提出“新史学”,倡导历史研究主题的拓展。可在麦克尼尔看来,此等“新史学”并不能疗治“旧史学”的痼疾。政治史之外的另找话题和技术翻新,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史学应答世界之变的偏颇与乏力,它只是为政治史包裹上 “自由的外衣”,用陌生的不清晰替代了熟悉的混沌。回避“根本问题”的新史学,只能制造满地的碎片。身为职业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并不反对作为工具的历史实证,惟坚信历史真相的复原和解释,应当服务于一个“高尚的梦想”。在笔者看来,这个梦想倒是和奥古斯丁和汤因比的思辨之史心有灵犀,那就是“从各种零碎的细节中去寻找一种概括性的通论”。或许,在麦克尼尔看来,如此方能重拾崇高的历史经验。
军事史外的经济和社会,全球史下的东方与西方
麦克尼尔自身的学术亦如一条河流,本文欲求理解的《竞逐富强》就是河上的浪花一朵。纵而观之,《西方文明史纲》(1949年)、《西方的兴起》(1963年)和《欧洲史的形成》(1972年)是他谱奏的“西方文明三部曲”。这之后,他推出《瘟疫与人》(1976年)和《竞逐富强》(1977年)。二者堪称姊妹篇,又可视为《西方的兴起》的续写,皆关注影响世界历史形成的重大要素。前者补足世界历史进程的生态背景,于今炙手可热的医疗社会史奉之为经典;后者着意在千年变局中冷观西方现代威权优势的形成,从而为李约瑟难题贡献了一个全球史版本的答案。笔者的观感是,此书虽然聚焦军事,但却秉持着作者一贯的“整体史观”,紧扣历史全局中的“关键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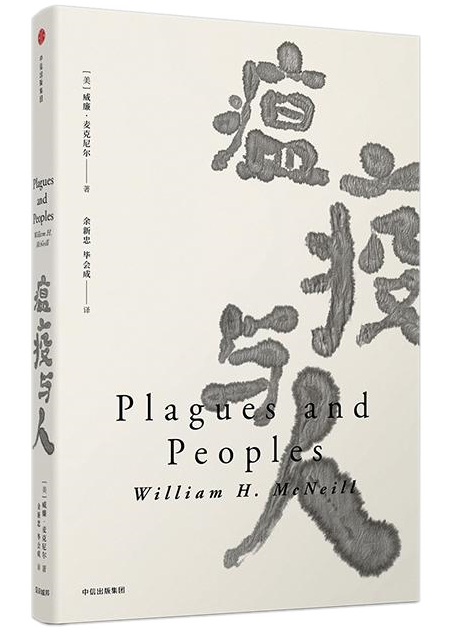
▲ 《瘟疫与人》,中信出版社2018年5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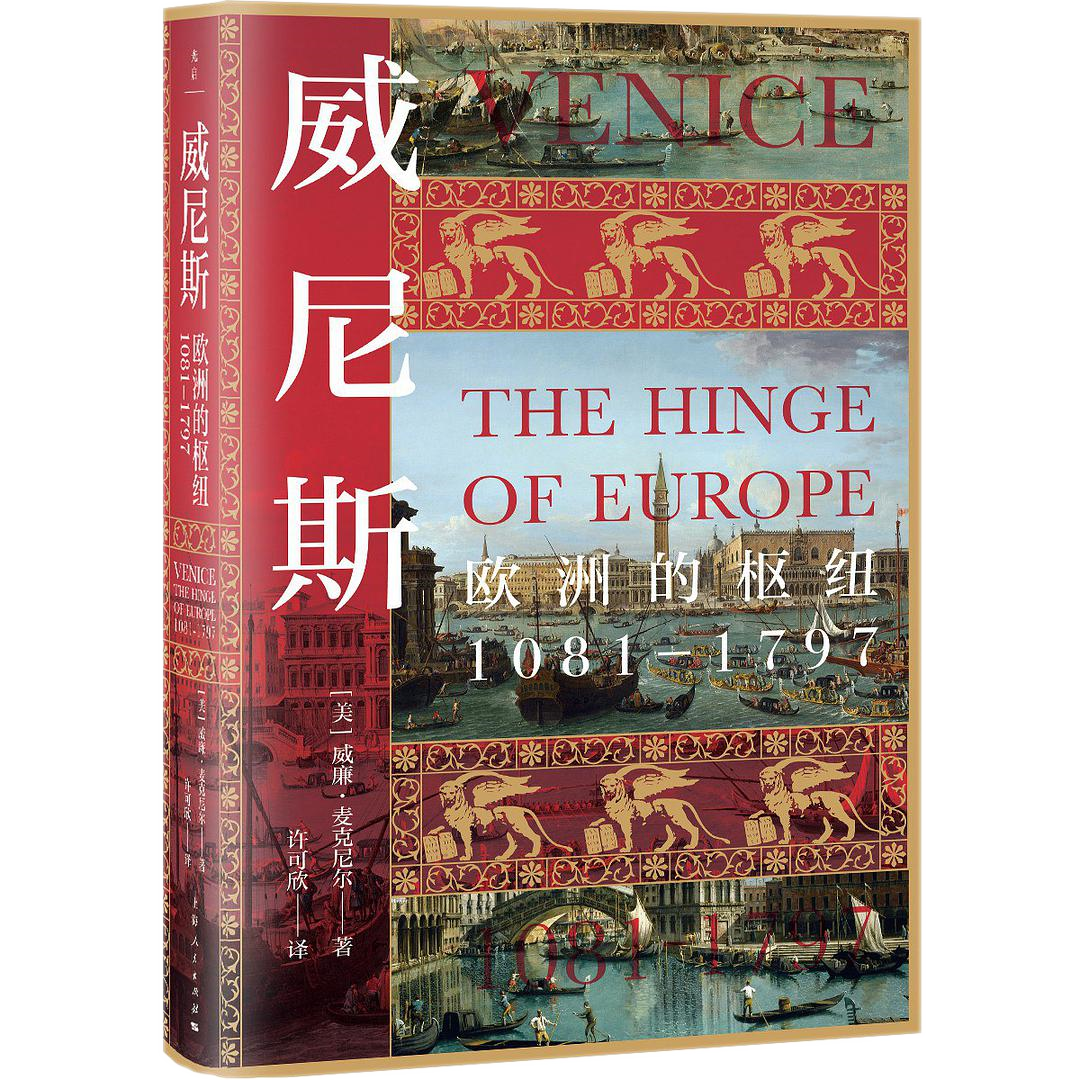
▲ 《威尼斯:欧洲的枢纽》,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版
历史学是对历史的有限定的选择性书写。在海登·怀特的叙事理论取景框中,史亦为诗。一流的历史解释框架,既是历史客观的再现,更映见历史学家的匠心。在此种意义上,麦克尼尔创造的史学范式,即具有诗学的意味。那么,麦克尼尔又是如何建构他的世界历史诗学的呢?在《竞逐富强》中,他针对欧亚大陆的文明实体,展开了内外两个维度的剖析。
其一,社会组织的内部运转。诚如此书副标题所示,作者意在“技术、军事与社会”所构成的“系统”中,而不是单纯的军事史语境中解释富强竞逐的根由。读麦克尼尔的书,仿佛拆解一个阿德里亚诺线团,抽出一条线索便会牵扯出另一条线索,发现一个话题便会追问另一个话题。在他解释威权博弈的因果链条中,卷入了火药革命、市场争夺、交通运输、海外贸易、官僚机制,及至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这样宏大的变量。国家或地域文明体间的实力较量,表面上看是枪林弹雨,实际上却是社会整体动员力的综合较量。技术、经济与政治构成互动的三角,武力是这个体系的输出产品。公元1000年前后率先起步的中国武器制造巨变,首先得益于市场机会的增多和社会的大规模商业化。15世纪大西洋欧洲在军事上的异军突起,得益于“军事-商业复合体”的体制发明和军事管理的官僚化。战争为国家所带来的财富,反过来又增持军工投入,加速国家实力增长的内循环。麦克尼尔旁征博引地告诉我们,称雄一时的政权,无不在社会组织的顺畅运转上领胜一筹,晚近以来,没有上限的实力竞逐同样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巨大隐忧。上层建筑体系业已成为支持霸权争夺的顶配,欲望、谋略、发明、权力和市场这些曾经塑造文明的部件,日益绑缚于国家资本驱动的战车之上,孕育出无法驯服的“利维坦”。
其二,文明实体的对外交往。《竞逐富强》在第二章中描绘了宋至明中期的中国历史,并把它命名为“中国称雄的时代”。此种写法不仅是为补上《西方的兴起》中少写一笔的空间盲点,更铺设了竞逐所由的宽广历史语境。中国在这幅竞逐版图中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地方性知识”,而是“人类之网”中的一个枢纽。中国人在11世纪时的开放表现,特别是路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为全球市场关系的建立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通过和文明社会的接触而不断提高,至13世纪达到了顶峰。蒙古帝国的建立,使中国技术传播到欧亚大陆更远的地方,构成了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东方因素”。15世纪之后,西方一跃成为最耀眼的竞逐者,这一胜出同样离不开文明互动的全球背景。现代西方军事的胜利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在全球的胜利,是现代世界体系中不均衡的资源流动的结果。到了19世纪,在战争工业化的进程中,以武力征服为先锋,辅之以现代交通和通讯手段,欧洲人将遥远的亚非拉美世界纳入一个由他主导的交换和生产体系之中。不难看出,《竞逐富强》再次重申了麦克尼尔的经典世界史观:西方的兴起是世界历史的合力聚变。其中值得镜鉴之处在于:在长时段的历史流变中,每一次全球竞逐中的领先都受力于文明的交往。要想保持长盛不衰,文明体必须具有海绵一般的持续不断的养分吸纳能力,和把外部能量化为已用的自我改造机制。
一个并不乐观的未来,一剂看似天真的药方
历史学关注过去,但一流的历史书写总是逼近关乎整个人类的现时命运问题。在麦克尼尔笔下,欧亚列强竞相登场的舞台被置于公元1000年以来的背光灯下,在幽深又宏阔的布景中,区域的胜出如江山轮转,每一轮竞逐所造就的或胜或负的结局,留下高低错落的连绵痕迹,隐约勾勒出文明盛衰的轨程。
立足长时段的经验,《竞逐富强》在尾声部分为我们的世界预见了一个并不乐观的未来。20世纪以来,新技术的开发逐渐失控,理性的规划反倒催生出非理性的结局。国家内部的组织日趋完善,由之组成的世界却冲突加剧。处在全球权势金字塔尖的人陶醉于 “威胁论”的想象,“不信任感”增多。人类所发明的新式武器,已超出所能驾驭的限度。那么,21世纪呢?在某些人眼中,它可能是 “最好的时代”,但以人类处境观之,它也可能是“最坏的时代”。
如何面对因竞逐无序而带来的不确定的人类未来?麦克尼尔开出了一剂看似天真的药方:成立一个至高无上的 “全球政府”,以消除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纷争。如果不这样,人类的灭绝可能随时发生。由国家体系向全球帝国的转变,注定是一个很难证实的假说,热衷于竞逐的现代世界似乎一点儿也没有为这个远景做好准备。一个深谙世界历史法则的智者,也许更应当提出一种适合人类未来的“竞逐之道”,在只能维系“脆弱平衡”的武力砝码之外另寻“永久和平”之舟的压舱石。抛开各种不可控的变量,当下的世界公民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急迫地需要达成一种 “共同体伦理”,以自证人类作为 “类存在”的共存智慧。
作者:王邵励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编辑:孙欣祺
责任编辑:杨健
来源:文汇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