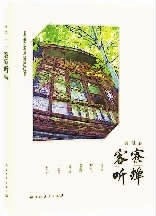
《客寮听蝉》
曹旭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史伟
《客寮听蝉》是曹旭的第三部散文集。书名取自于文集中同名的一篇散文。客是客居,寮是作者在日本的居所———光华寮,蝉是一个异乡异客的孤旅朝夕对待之物,就是作者自己。作者说:“窗是蝉声的世界。”
作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多次到日本访学,文集所收文章大部分是日本寮居时所作,其中很多即依当时日记改成;小部分是回国后的追忆之作。如作者在《后记》中所叙:这本散文集,是我访学日本的笔记;是前所未有的、最真实、最难忘的内心记录;是感性和理性搏斗的痕迹;是我挣扎,像五月的梅子在风中不停地摇摆并成熟起来的标志。
逐渐“成熟”,就像作者多次提到的“阅读日本,也阅读自己的内心”的过程。所以,《客寮听蝉》是反思之作。
文集分为六个部分:寂之美、物之哀、寮之缘、居之思、忆之灯,分别代表作者阅读日本、阅读自己的不同面向和不同阶段。
“寂之美”写京都四时风物。作者在代序的《阅读日本,阅读自己》中说,初到日本,“首先阅读的是空气”,“接着阅读的是四季”。
作者写京都的春樱、夏铃、秋夜、冬雪,写冬雪中的“木屋与柴门”:柴门是风雨的朋友,柴门甚至可以像留住朋友一样地留住风雨,可以让风雨在门隙里穿来穿去地做游戏。(《木屋与柴门》)
这里有“风雪夜归人”况味,也有“风雪夜归人”的温暖;但这温暖是不真实的,是寄托的。
他也写人,那些遗落在樱花中行将迟暮的妇人:花飘过来的时候,她们脸色如玉,一点也不惊慌;风过去以后,她们重振衣袖,轻轻地拂去身上的花片;在相互拍去对方肩上、头上落花的时候,也互相品尝对方眼中的自己。(《樱花与美人》)
这些都很美,也很寂寞———确切地说,是落寞。不难想象,其间欣羡与自卑交织的心绪。
“物之哀”“寮之缘”“居之思”都是写光华寮的生活,因寮居生活的不同心境和情感,而各有侧重。
“物之哀”是文集中最为沉重的部分,《客寮听蝉》就出自其中。作者在《光华寮祭》中叙述了光华寮的前生今世,称“光华寮是悬在海外的孤儿”。他说:我把文章写在纸上,当风焚烧并遥祝光华寮早日涅槃。这让我们想起郭沫若《女神》中浴火重生的凤鸟,这也正是作者的祈望。同样的表达也出现在《光华寮看烈火金刚:日本观剧》中,作者说:最深情的是我们———一群去国怀乡、受人欺负,内心敏感并且已经受伤的卑微者。真正的爱者,才是真正的了解者。所以,在离开光华寮时,作者会长跪不起,泪流满面。
作者在作为题记的小诗中写道:与走到天涯也无法回家的狗尾巴草相比你算是幸运的。凄怆而决绝。这样的经历会带来什么呢? 就像作者在《独坐吉田山》所写的,它可以让人“感受到,一个人孤独时生命与真的零距离”。我们可以由此理解,为什么我们前面提到的还有其他相类的日本风物描写,总是带有寂寞和伤感的色彩,这是巨大的孤寂中才能呈露出的风景;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作者会投入极大的关注,为自己定下“阅读日本,阅读自己”的课程。
“寮之缘”“居之思”就是这样的结晶物。
作者写盂兰节“大文字”山的祭祖,两次提到和老冯的谈话,提到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当作迷信的祭祀(《秋的“大文字”山》)。写“天天吃泡面,把伙食费一点一点省下来,每年举办一次没人来看的书法展览”的东京大学大学生,作者感慨:“我有一种震撼的感觉。”(《涩谷雨》)作者也探讨日本的社会结构,他说:“日本社会由一个一个圈子组成,圈子与圈子之间,观念相去甚远,互不干涉,这就是日本人多元的生活方式吧!”(《看日本探索电影》)这些与我们平素直观和臆想的日本颇有不同。
最令我震惊的是 《日本米》。1993年,作者赴日第一年,日本遭遇灾荒,从中国、美国、泰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大米,接下来,就是“以米为中心,围绕‘日本米’发生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首先是码头工人不肯搬运,然后是米店老板拒绝进货,即使日本家庭主妇也不买中国米,偶尔买,也只买东北米,为什么? 日本主妇答:“中国东北米是日本传过去的种子呀!”作者补充:“后来知道,东北米是伪满时期日本的种子,她们没有忘记。”不是说日本人不了解他们的侵略历史吗? 作者写道:“对中国米的歧视,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歧视。”这令人警醒。
《六月的一件小事》,写作者误打误撞进了“大京都展”促销会,导购是七十多岁的日本老妇人,“她一路逢熟人就讲,今天接待了一位买不起和服,买不起皮夹克,什么都不买的中国人。她的日语说得很快,以为我听不懂,其实我都听懂了。”然而在同行回来的路上,作者知道,每年一次的导购会给这位孤寡老人带来一点收入,却被自己浪费了。分手时,作者写道:不知什么原因,我的泪水一下子涌出眼眶,呆呆地站立着,然后朝她渐渐远去的佝偻的背影,深深鞠了 一躬———久久没有直起身来。他说,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平心而论,这次经历受伤害的,其实是作者。这样的伤害在日本经常发生,就像作者在题记诗中写的:“在京都光华寮,我生活在生命对我特别吝啬的那一部分里。”但善良的心,即使自己在受苦,也会天然地推己及人,去同情比他还苦的人。作者说:“我在日本人鄙视的眼光里成熟起来、丰满起来、透彻起来。”
“屐之痕”、“忆之灯”两辑近于文集的尾声。“屐之痕”写出航也写归航,作者甚至还有兴趣抽空揶揄一下那些坐头等舱的政府官员和富商(《晕船》)。“忆之灯”则写了作者客居日本时对祖国、对江南的思忆,和回归后对日本的追想,《春子》就收在此章。这段尾声美而意味深长,但不同于“寂之美”的孤寂伤感。作者在题记诗中说:界碑上的鸟/从一个国家飞到另一个国家/不知道什么是国籍。但人是有国籍的:不管春天在哪里/天涯在哪里/马蹄声在哪里/我都要抛弃家产归来/重携小乔的手/过江南平民的生活。
从“寂之美”到“忆之灯”,笔致宛如水流,由冲突激荡渐至于涵澹澎湃,有时呈现一种沉静的深美。在回顾这段心路时,作者写道:随着对日本异文化的理解,我敏感地注意到我对日本人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我在每一个变化的地方种一棵树,竖一块碑,命一个名,建一个驿站,它们是:寂之美———物之哀———寮之缘———居之思———屐之痕———心之灯。
曹旭是一位优秀的、卓有成就的中国古典文学学者。学者张瑞芬教授在评价曹旭散文时说:“语言简洁,真挚凝练,熔铸古今,意味隽永”,并非过誉之词。
作者写水田中的稻草人:和我家乡江南的一样,又不一样;写日本人对花的迷狂:日本人的花国精神,令我悢悢不能言。作者写这些话时,心里一定想着中国。事实上,文集中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是在写中国。 《客寮听蝉》 既非“闲情偶寄”,亦非游记,没有猎奇似的异域风情,甚至没有思古之幽情,有的是强烈的现实感。作者说:
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今天,寮客和蝉不甘寂寞的歌唱,会有见证历史、对比现实和意味不尽的意义。
未来的世纪,怎样和日本做邻居? 阅读日本,阅读自己,仍然是一个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