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博物学的知识建构开始与旅行写作结合起来,“标本搜集、藏品积累、新物种命名、未知物种确认,成为旅行和旅行书中的标准主题”。博物学在欧洲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在近代具有了塑造全球统一的知识体系的作用。】

苏格兰探险家芒戈·帕克
1799年4月,一本名为《非洲内陆旅行记》的旅行书在英国问世,初版1500本在一个月内销售一空,作者从中得到了1050英镑的收益。同一年又印刷了两版。在1800年1月之前,作者告诉他的妻子,他从3个版本中获得的收益已经达到“大约2000英镑”,而且还会得到更多。1800年,该书的法语译本、德语译本和美国版问世,“自那时起,这本书不断被收入选集,被节选、重编”,成为一代又一代欧美读者的精神食粮。
这本书的作者名叫芒戈·帕克(Mungo Park,1771—1806),生于苏格兰,曾服务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后受雇于英国非洲协会,致力于尼日尔河的探险工作。非洲协会的全称是非洲内陆发现促进会,成立于1788年,总部设在伦敦,由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1743—1820)创立和领导。班克斯曾以博物学家的身份进行环球科学考察,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长期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及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园长。
非洲协会是一个由贵族和富有商人组成的联盟,其目的在于扩大人类的知识储备,而其实施的唯一一项任务是查明尼日尔河的河道、走向、源头和终点,并考察其周围地区的商业潜能。帕克之前,非洲协会已先后派出了三个探险家领队前去考察,或无功而返,或病死他乡,或杳无音信。1795年,帕克开始他的探险之旅,期间经历了种种磨难,如热病、抢劫、囚禁、饥饿、干渴等,终于在1796年7月看到了“寻求已久的、庄严的尼日尔河”。随后,他又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返回英国,并写出“他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一本旅行书”。
非洲协会因为帕克活着返回英国并带回了有关尼日尔河及其附近地区的确切信息而欣喜若狂:“很难想象如此辽阔和人口稠密的国度,对我们国家制造业的要求可能会达到的程度。”在非洲协会的监督下,帕克开始撰写他的旅行书。在帕克的书问世之前,非洲协会就相信它会引起轰动,被指派监督他写作的官员宣称:“他最近寄给我的某些部分,堪与任何用英语写成的作品比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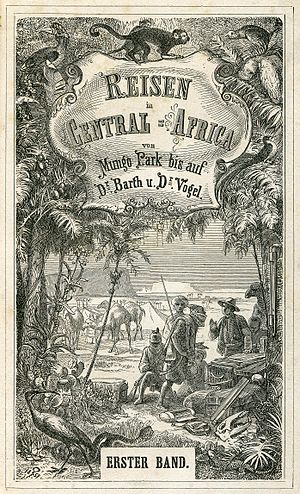
《非洲内陆旅行记》,1859年德文版
《非洲内陆旅行记》的畅销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学者谢尔在《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一书对1746—1800年期间,包括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在内的115位苏格兰作家们在英国出版的360种书籍进行销量统计后,列出了46种最畅销的书,芒戈·帕克的《非洲内陆旅行记》正在其中。
这本书在欧美世界的影响可谓深远。勃朗特家的孩子们由于受到《非洲内陆旅行记》的影响,利用歌尔德斯密所著的《普通地理入门》中的地理知识,编撰远离英国、发生在非洲大地的故事。凡尔纳在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中,刻画热衷于冒险探奇的主人公塞缪尔·弗格森时,写他自幼就梦想着得到芒戈·帕克那样的荣誉。帕克的经历在《白鲸》中被调侃:“像可怜的芒戈那样,全部的经历只是饿着肚子在非洲的黑人腹地里漫长而孤独地徒步跋涉——这种旅行,我看,可能不是一种获得上流社会的修养的最佳方式。”甚至,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第三章“梦的遂愿”中引述帕克的经历作为案例:“芒戈·帕克有一次在非洲旅行时近乎受煎熬,不停地梦见其故乡多水的山谷与低湿地。”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结束语中写道,还不如成为芒戈·帕克,“探险你自己的江河海洋”。
在谢尔列举的18世纪下半叶苏格兰最畅销的书籍中,还有一本名叫《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的旅行书,讲述了作者詹姆斯·布鲁斯于18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在非洲的冒险经历。因为这本书,伦敦书商向詹姆斯·布鲁斯支付了“惊人的6666英镑”。此前,大卫·休谟曾在临终前的自传中说:“书商给我的版税数量之多,在英格兰是前所未闻的:我不仅变得独立自主,而且变得富裕了。”这些版税大部分来自他最受欢迎的作品《英格兰史》,而休谟通过《英格兰史》得到的总收入大概在4000英镑到5000英镑之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于出版者和作者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成功”,而“从出版到作者去世的14年间,支付给作者的版税总数在1500到1800英镑之间”。《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面世于1790年,1794年布鲁斯和巴黎书商签订了国外销售的协议。然而一个月后,布鲁斯突然跌倒而失去了行动能力,并在同一年去世,结果他们的协商意外地终止了。谢尔认为,“如果布鲁斯能活得更久一些,《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给他带来的收益可能会超过18世纪的任何单部作品带给作者的收入”。
美国学者普拉特在《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一书中指出,“欧洲人写的关于非欧洲世界的旅行书”,“赋予欧洲读者大众一种主人翁意识,让他们有权利熟悉正在被探索、入侵、投资、殖民的遥远世界”,因而“旅行书很受欢迎”,“它们创造一种好奇、兴奋、历险感,甚至引起对欧洲扩张主义的道德热情”。在这个过程中,博物学在欧洲兴起,并与旅行书写相结合,逐渐产生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意识和知识体系。
博物学在欧洲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在近代具有了塑造全球统一的知识体系的作用。瑞典博物学家林奈于1735年出版的《自然系统》一书,提出了一个基于植物生殖器特点的分类系统,“旨在将欧洲人已知或未知的地球上所有的植物形态加以分类”。在林奈以前,也有不少博物学家提出了各种植物分类方法,但林奈的分类方法“具有一种其先行者未曾达到的简单和优雅”,“凭借他的方法,任何曾学过这个系统的人,都有可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将任何植物归入即使不是正确的属类,也是正确的种类和秩序之中,无论这种植物先前为科学界知道与否”。林奈有意地复活拉丁文用于其命名法,这是因为它是不属于任何民族的语言。林奈本人来自瑞典,在全球经济和帝国竞争中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参与者,这“无疑增加了整个大陆范围内对其系统的接受度”。在这个基础上,林奈的分类系统发起了一场“在规模和吸引力上都前所未有的欧洲知识建构事业”。
在这个过程中,博物学收藏成为整个欧洲大陆富人们的重要兴趣爱好,与此同时植物园“开始在整个大陆的城市和私家场所涌现”。更重要的是,植物采集逐渐成为有机会前往非欧洲地区的欧洲人共同热衷的一项活动。除了海员、征服者、俘虏、外交家这样的开拓人物外,到处都开始出现温和的、显然有文化的“植物采集者”,这种人物只装备一只采集用的袋子、一册笔记本和一些标本瓶。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博物学的知识建构开始与旅行写作结合起来,“标本搜集、藏品积累、新物种命名、未知物种确认,成为旅行和旅行书中的标准主题”。在帕克的《非洲内陆旅行记》中,最令人难忘的场景是,他遭到土匪抢劫,被留在沙漠等死,“精神开始垮下来”,而被一种博物学家的顿悟所救:
这时,虽然我的身体反应令人不快,但一小块丰厚的苔藓的非同寻常之美,吸引了我的目光,难以抗拒。我提及此,是为了表明,心灵有时将会从何等微不足道的情形中汲取安慰;因为虽然整棵植物并不比我的一个手指尖大,我却无法不无钦佩地注视根茎、叶子和被膜的精致构造。在世界上这无名之地种植、浇灌、成就它,创造这么一件看起来如此无足轻重的东西的那个存在,会对模仿他自己形象形成的造物之处境和苦难无动于衷吗?——当然不会。
从植物学到动物学再到其他学科,博物学将世界设想成一片混沌,各种分类系统的任务则是为地球上每一个物种定位,“将其从独有的、任意的环境(混沌)中提取出来,并将其置于系统(秩序名册、收藏或花园)中合适的位置,附上其正式世俗的欧洲新名称”。于是,在遍布全球的欧洲旅行者的共同努力下,“这颗行星的生命形态,一个接一个地被从它们纷繁纠缠的生活环境中抽离出来”,重新编织进以欧洲为基础的全球统一的知识体系中。正如普拉特所指出的,“拥有这个系统的(有文化的、男性的、欧洲人的)眼睛”,一旦接触新场所或新场景,可以马上将之整合进语言系统,以这种方式熟悉(“归化”或“自然化”)它们。英国人约翰·巴罗的《深入南部非洲内陆之旅》一书,绝大部分篇幅由风景和自然描述构成,“叙述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连串的场景或背景”,旅行者们则主要是作为记录场景或场所的一种“集体移动之眼”在场。除了描述,还有阐释,“为了解释矿物质的存在、沼泽的构成、山脉和河流的走向,提出各种化学的、温度的、地球物理学的假定”。这些来自西方科学的解释力量,把这些非欧洲区域都纳入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知识框架中,而其目的则是着眼于“欧洲殖民未来的种种可能性”,将这些非欧洲世界“编码成有待开发的资源、有待交易的剩余、有待建设的城市”。正是在此基础上,普拉特认为博物学引发并由之生产的旅行话语创造了一种“不需要诉诸征服和暴力的占有方式”。
18、19世纪,欧洲旅行书被大量地制造出来,为一代又一代足不出欧洲的读者创造了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秩序——让他们坐在欧洲“家里”,便产生了一种“主人翁”意识,认为欧洲以外的世界需要由他们去探索、认识、开发和建设。这样一种思维助长了欧洲殖民帝国的扩张,也促进了19世纪全球化的进程。
(本文引文来自普拉特著《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谢尔著《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等)
作者:冯志阳(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辑:陈韶旭
责任编辑:李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