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末,法国最负盛名的思想评论杂志《争鸣》(Le Débat)宣布停刊。创办于1980年的《争鸣》是伽利玛出版社旗下杂志,议题偏重政治与文学,但核心使命是非常法国式的思考——即社会科学与哲学的结合。创刊人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是研究法国文化记忆的历史学家,后来荣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早期撰稿人中有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和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争鸣》曾经在法国左翼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

创刊人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也是一位“天才的编辑”——他负责福柯在伽利玛的作品
近日,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发表评论,说法国各界的知识分子认为,这份杂志是在从美国“进口”来的更意识形态化的身份政治大潮下,逐渐不支的。
在许多法国人看来,美国式的“社会正义”政治是一种恶变。去年春天,乔治·弗洛伊德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美国各地的抗议和骚乱导致雕像和其他公共象征被大举拆除。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即警告说,法国不会效仿。到秋天时,马克龙开始猛烈抨击外国大学的传统:“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建立在另一种历史之上,不是我们的。”接下来,他特别提到“从美国引进的某些社会科学理论”。2007年,《争鸣》杂志主编马塞尔·戈谢(Marcel Gauchet)曾提醒说,身份政治关注的不是人民的主权,而是个人的主权——个人权威至高无上。如今,始终拒绝“进口”理论的《争鸣》杂志应声倒下。

不过,安托万·忒内(Antoine Traisnel)在《高等教育纪事报》上撰文说,马克龙剑指后殖民研究和批判种族理论,保卫所谓法国传统,是为他2022年选战做准备;他说那些历史和传统“不是我们的”,是在否认法国的殖民历史和社会现状。法国一直害怕美国化,也一直有着文化上的优越感,而这次马克龙的姿态是意在用法国“例外论”唤醒他的极右翼票仓。
这看起来是“理论武器”进出口的倒转。曾经,“法国理论”风靡美国。直到二三十年前,也就是福柯和德里达的时代,人们还可以说美国在智识问题上服从法国。有趣的是,如忒内指出,今天“从美国引进的某些社会科学理论”正是从早前的“法国理论”发展而来,斯皮瓦克、朱迪斯·巴特勒、霍米·巴巴等等都是基于法国知识分子的概念和分析再作阐发。
“法国理论”的“推手”之一,把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介绍到美国的文学理论家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1923—2015)曾经打趣说,他这是“把瘟疫带来美国了”。法语里没有“法国理论”一词,这是一项美国人的发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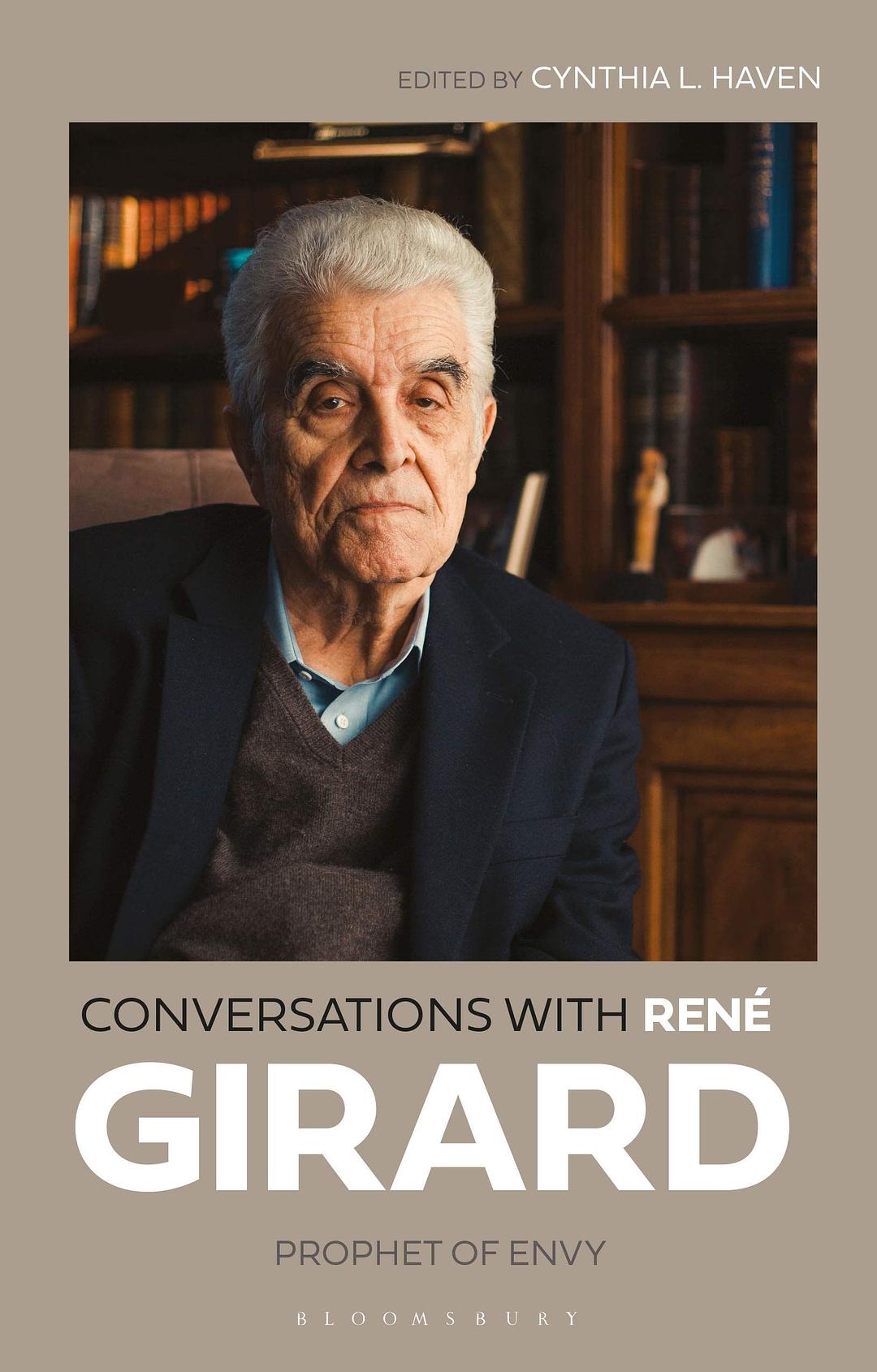
近日,恰有一本吉拉尔的访谈合集《与吉拉尔对话》(Cynthia L. Haven编,Bloomsbury Academic,2020)出版,可以读到当年他对“法国理论”被美国人文学界食洋不化地奉为真理的进一步“吐槽”。例如,如果拉伯雷再世,“会对我们现在的经院哲学”大加取笑,以及:
下一代会想知道,是什么冲动可以让那么多人无休止地写作,而且完全是无中生有地写出最复杂难解的文章,不仅同他们的生活现实,也同伟大的文学文本断开连接。
他认为,这些现代的经院哲学一直“无耻地寄生于伟大的文学文本之上”。而最让吉拉尔沮丧的是他在学界同仁中观察到的残暴与虚无主义——尽管这是对他著名的“模仿”理论的又一证明。这一理论认为,欲望是模仿而来,不是我们自己的;人们因为想要同一样东西而产生冲突,也就是说,冲突是因为我们互相雷同。吉拉尔发现,他的同行们代表了一种最奇特的狂热:一种什么都不相信的狂热。他们可以毫无理由地发动最血腥的智识战争,中伤和羞辱他人,甚至毁掉他们的事业:
当人们真正相信某种比学术界更大的真理时,他们就不会像那些什么都不相信的人那样狂热地追求学术上的成功……当前的虚无主义非但没让人变得更放松、更大度,反而让学术生活变得更加艰苦,也没有过去那么富有同情心。
吉拉尔不是那种“孤独的思想者”,他喜欢“与人合作解决问题”,常在发表正式观点之前先进行“内测”,邀请谈话伙伴提出质疑。编者说,阅读吉拉尔多年来的对话,犹如看他在暗房中慢慢显影。
在法国出生长大的吉拉尔在斯坦福大学任教近四十年,平素举止优雅而严肃,也正因此,他拿刺儿蜇起人来可真是要命:“看看学术界,那一大群像羊一样的个人主义者。”他的幽默嘲讽也针对自己,回忆起到美国的头几年,他说自己“最大的愿望是得到一辆车”。在另一次采访中,他评价萨特“在内心深处是一个自得其乐的小资产阶级,热衷旅游,是个喜欢过太平日子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天才”。
编译:本报记者 李纯一
编辑:陈韶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