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松梢风:“魔都”词语与意象的制造者
徐静波
《文汇学人》2017.7.14
村松曾自述为何会有1923年的上海之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受了芥川中国之行的刺激,但主要是自己想去上海寻求自己人生的新的生路。”

村松梢风(1889—1961)的作家地位在20世纪的日本文坛大概连二流也排不上,尽管他生前发表过几十部小说和人物传记,曾经有过不少的读者,他撰写的六卷本《本朝画人传》被数家出版社争相出版,一时好评如潮,1960年中央公论社在建社100周年时又以精美的装帧将其作为该社的纪念出版物推出。在日本出版的各种文学辞典和百科全书中,对他也有颇为详尽的介绍。不过对于梢风的小说,评论界一直很少给予关注,他撰写的作品,大部分是历史人物故事,人文的内涵比较浅薄,除了作为大众文学作品集出过寥寥两种选集外,在文集、全集汗牛充栋的日本出版界,迄今尚未见到有梢风的著作集问世。这大概可以映照出梢风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指数。不过当我们将目光投向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日文化关系史,特别是这一时期日本的作家文人在中国的活动时,村松氏却是一位不应被忘却的人物。自1923年至1933年的十年间,他大约来过中国近十次,足迹北及东北、热河,南涉台湾、广东、香港,有关中国的文字,仅结集出版的即有十本之多。
梢风生性比较放浪,喜好游乐和冒险。他觉得大正时期的日本,气氛太沉闷,很想脱出列岛,到海外的世界去游荡。恰好在此时,他读到了1921年芥川龙之介作为海外特派员在《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发表的《上海游记》。梢风后来在以第三人称撰写的自传《梢风物语———番外作家传》(载东京新潮社《新潮》杂志1953年2月号)中这样写道,1923年的上海之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受了芥川中国之行的刺激,但主要是他自己想去上海寻求自己人生的新的生路。从这意义上来说,他的意图可谓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与同时代的作家芥川龙之介和佐藤春夫等人相比,梢风的中国文史的学养是比较浅薄的,然而1923年3月22日坐船来到上海时,在长江口初次目击的大陆景象还是令他深深感动,他后来在《支那礼赞》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感受:
不知何故,此时无限的亲切、喜悦、感激等诸般情感一下子都涌上了心头,最后变成了一种舒畅的伤感,禁不住热泪盈眶,怆然而涕下。我不知道世人是否都有我和宫崎滔天这样的感觉,不过我在此处见到了我们这些热爱支那的人的纯澈的心灵。这似乎并不只是广袤无涯的大陆风光使我们产生了盲目的感动。我觉得这是由于支那广阔的土地唤醒了潜意识般长期深藏于我们心灵深处的远祖传下来的梦。这种内心的感动有时会比较强烈,有时会比较朦胧,但当我们去支那旅行,双脚踏在支那的土地上时,这种感动便一直持续着,不会消退。像我这样缺乏汉学修养的人,并不是在学艺知识上被支那所深深吸引的。尽管如此,每当我踏上支那的土地,我心头立即会强烈地涌起一阵从未有过的来到了梦寐之乡的情感,说来也真有点令人不可思议。
这应该是真切的感觉,有一个时期,他对中国的喜爱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他在《支那漫谈》序中说:“说句老实话,我有点几近疯狂地喜欢支那。喜欢也有好几种,我是恋爱的那一种。支那是我的恋人。”(《支那漫谈》序,骚人社书局1928年5月)江南清丽的风物自然是他向往的,上海的纸醉金迷更是令他流连忘返。1923年的初访,他在上海逗留了两个多月,接触了各个层面,返回日本后,撰写了一篇近5万字的长文《不可思议的都市“上海”》,刊载在1923年8月号的《中央公论》上,此文后来又与数篇记述上海的文字合集成《魔都》一书于翌年出版,他将自己在上海感受到的复杂的意象,用创制的“魔都”一词来加以浓缩,长期以来,一直浸渗在不少日本人的脑髓中,不意在将近一百年后的中国,由梢风创始的“魔都”一词竟然成了“上海滩”的代名词,其热狂的使用频率,远在日本之上,这恐怕是梢风当年始料未及的吧。

在近代中日文学关系史上,日本作家与上海新文坛的关系发生,大概肇始于1923年3月末村松梢风与田汉等的交往。与此后大部分日本文人是通过内山书店的媒介与中国新文坛发生接触的情形不同,村松是自己径直寻找到田汉的,日后在田汉举行的家宴上又认识了郭沫若等一批创造社的新锐作家,彼此间的交往,一直持续到1920年代末期。这些活动,国内传统的田汉和郭沫若的年谱传记几乎都没有记述,这里译出的若干文字,也许可以聊补不足。
1927年6月,田汉以南京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宣传处电影股长的身份前往日本访问考察,据其同年9月30日发表的《日本印象记》,他在启程前委托内山书店给作家谷崎润一郎和村松梢风发了联系电报。在知晓田汉来到日本的消息后,梢风于23日撰写了《来朝(即“访日”之意———引译者注)的田汉君》一文,发表于两天后的《读卖新闻》。梢风在该文中写道:“我与田汉君初识于此时(指田汉供职于中华书局的时期———引译者注),我是带着佐藤春夫君的介绍函去访田君的。田君与易氏在静安寺路安了家,并将老母接来同住,夫妇间还诞生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当时被视为南中国新兴文坛牙城的《创造》同人,其同志有现在广东大学的郁达夫、成灏,在汉口政府担任政治部长的郭沫若(实际上曾于1927年4月29日被国民党武汉中央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引译者注)诸君。……田君在创作之外还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翻译了莎士比亚的作品作为少年读物的丛书由中华书局刊行,在日本文学中翻译了菊池宽的《父归》和其他数篇。田君自己的创作,剧作比小说多,且剧作好像更出色。用日文撰写的发表于《改造》支那专号上的有《午饭之前》。用本国语撰写的作品中,《咖啡店一夜》等似较有名。最近一年多来参与电影公司的工作,主要埋首于拍摄少年电影。……在我所交往的支那文学家中,田汉君可谓是最质朴的一个人。他的作品即使拿到日本文坛上来,无疑也是在水平线以上的。”(载《读卖新闻》1927年6月25日)抵达东京以后的行踪,在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中引述的日记中有较为详实的记述,日本方面较为重要的文献有村松梢风的《骚人录 (一)》《骚人录(二)》(分别刊载于1927年8月和9月发行的《骚人》杂志第2卷第8期和第9期),佐藤春夫的《人间事》(先后刊载于1927年10月和11月发行的《中央公论》杂志)和小堀甚二的《佐藤春夫氏和田汉君》(刊载于《文艺战线》1927年12月号)等。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可参阅拙文《日本作家村松梢风与田汉、郭沫若交往考》,载《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4期)。
郭沫若在1928年2月因遭到蒋介石的通缉而流亡日本,这段经历他后来在1947年发表的《跨着东海》和《我是中国人》中有记述。不过梢风在1953年发表的第三人称的自传《梢风物语———番外作家传》中对此的叙述与郭有些差异。据梢风所述,郭到了东京后去骚人社找梢风,梢风通过一位居住在千叶县市川的朋友找到一处空房子安顿了下来,又通过这位朋友与当地的警察署长和小学校长打了招呼,于是孩子也得以在当地学校上学。半年后郭遭到了日本警方的逮捕,梢风也受此连累而被关进了拘留所。数日之后,梢风设法联系上了有些熟识的警视厅书报检查课的老资格警官大谷,经大谷的努力,终于在一周后获得释放,出狱后的梢风在向大谷致谢的同时,求见外事课长,为郭沫若详细辩解,于是外事课长下令释放了郭沫若。而郭的叙述是,他的释放,是由于安娜奔走的结果。事实究竟如何,似乎也难以妄下定论。不过,在上海及日本与中国文人的交往,对梢风的一生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他的长孙、后来成为作家的村松友视于1983年带了母亲到上海来寻访他祖父浪游的旧迹后写道:“被上海所迷醉的梢风的感动,当然并不只是魔都上海的意象,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中国文人的交往,肯定大大改变了梢风(的人生)。”(《上海摇篮曲》,东京文艺春秋社1984年,第182页)
需要指出的是,一直标榜热爱中国的梢风,在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发生后,其政治态度就主动与日本当局靠拢,为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辩解,抨击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抗日言行,对此我曾详细撰文分析过,这里就不赘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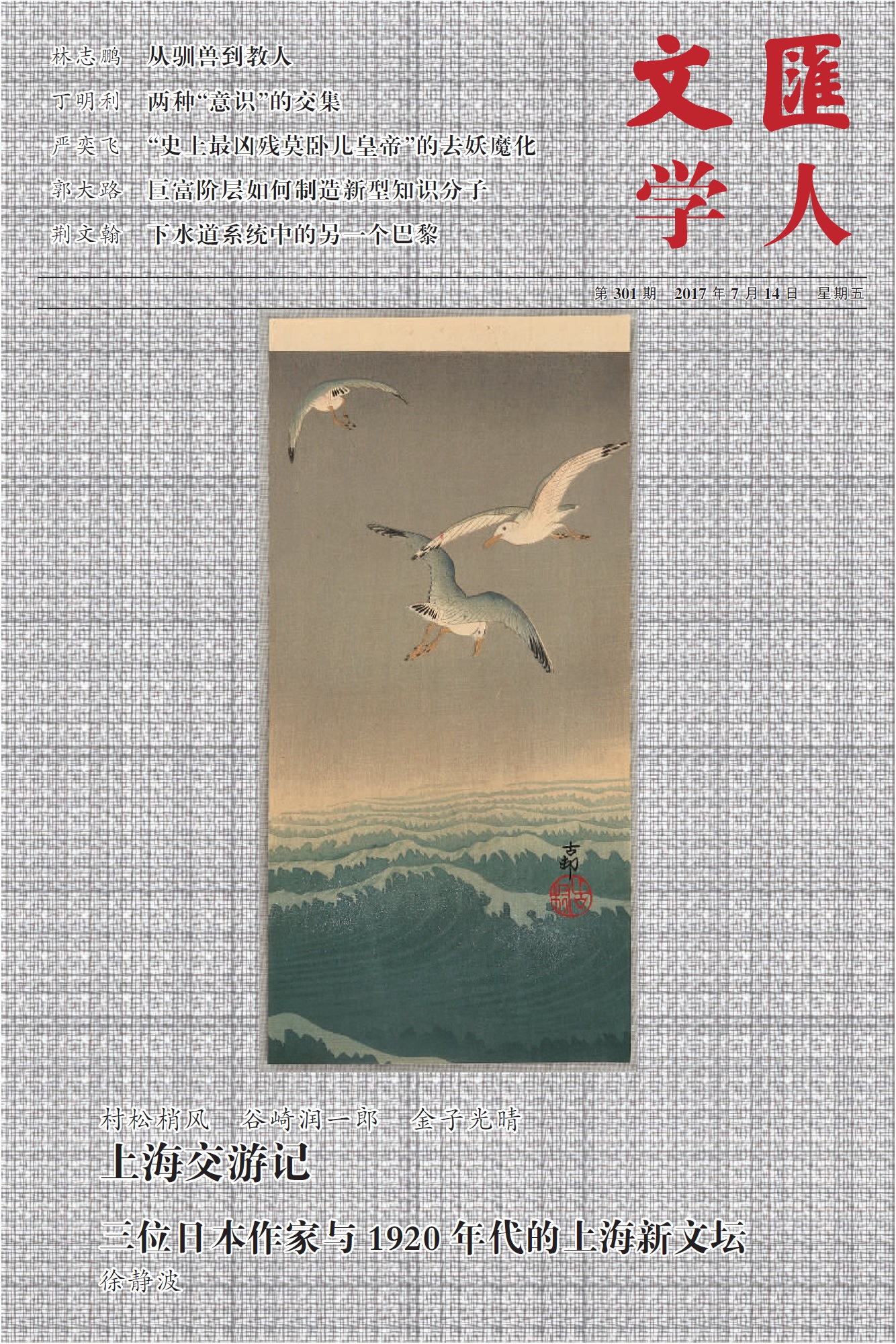
责任编辑:李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