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种奇怪的传染病似乎从法国波尔多蔓延开来。数十位男性发现自己在无知无觉的状态下漫游欧洲,明明心里没有目的地,却穿越国境,乃至跨越大陆,最后或被警方拘留,或被关进疯人院。当时的医生诊断其患有“神游症”。在《疯狂旅行者:一种精神疾病的诞生与消散》中,现代科学思想巨擘、加拿大科学哲学家伊恩·哈金创造性地考察了这一鲜为人知的疯狂旅行流行病。他横跨精神医学、历史学、科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等多个领域,不仅讲述了第一个“疯行者”阿尔贝·达达耐人寻味的人生故事,而且探索了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包括精神障碍的真实性、催生疯癫的社会“生态位”,以及这个一百多年之前的案例对备受精神疾病困扰的现代世界的意义。
一个迷失自我的魔怔行者,一位坚持自我的专一医者,拉开一场流行疯病的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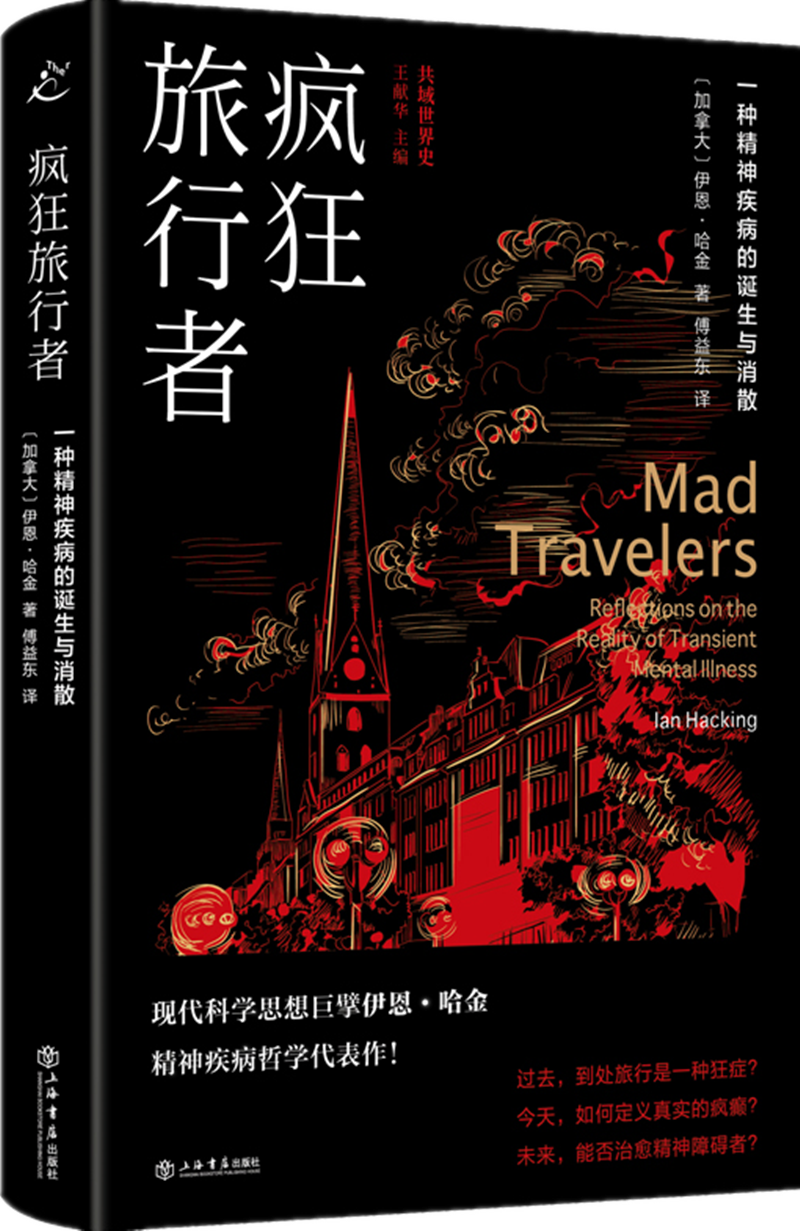
《疯狂旅行者:一种精神疾病的诞生与消散》
[加拿大]伊恩·哈金 著
傅益东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第一位神游症患者
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去年7月的某个清晨,我们注意到皮特医生的病房里有位26岁的年轻人在卧床哭泣。他刚经历了长途旅行,徒步归来,已是筋疲力尽,但这并非他哭泣的原因。他哭泣,是因为一旦被那种渴求占据,他便难以自控地踏上旅途,为此不惜抛弃家庭、工作和日常生活,以最快的速度行走,有时每天步行70公里,直到最后流落街头、被捕入狱。 ”
我们的故事从波尔多那历史悠久的圣安德烈医院的病房中开始。年轻人的名字叫做阿尔贝,他是当地煤气公司的临时工,也是本书所提及的第一位神游症患者。他因在阿尔及利亚、莫斯科、君士坦丁堡的离奇远游而尽人皆知。他沉迷于旅行,几近着魔,然而总是不携带身份证件,有时连身份证明也没有;他不知自己是谁,不知为何旅行,只知下一站行往何处。当他“苏醒”时,他几乎不记得自己行之所至,但在催眠状态下,却能回忆起那些逝去的浪迹时光。
关于阿尔贝的医学报告起初在波尔多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流行病,染病者挂帆出海、所向无前。热潮很快蔓延到巴黎,接下来是整个法国、意大利及至德国和俄国。“神游症”本身成了一种医学意义上的疾病,携带着类似于“流浪癖”这样的俗语标签,也有恰如其分的拉丁语或希腊语标签,如“漫游自动症 ”“主观性自动症 ”“旅行狂热症”“漫游症”。神游症,也就是在神志不清状况下进行的怪诞不经的旅行,一直为世人所知,但直到1887年,随着一篇医学博士论文的发表,其所意指的疯狂旅行才成为精神错乱中某种特定的、可诊断的类型。
阿尔贝的离奇经历是一个流浪汉式的冒险,其中不乏痛苦感伤,但为何如今旧事重提?因为我们被精神疾病所困扰,这种疾病更多倾向于神经质,而非精神质,且我们力图探明其中哪些是装腔作势,哪些受文化塑造,哪些被临床强化,哪些又是盲目模仿综合征,以及哪些被我们要言不烦、隐晦其词地归结为——真实。我们对精神障碍群体深感困惑,觉得他们的症状既是后天形成,又是与生俱来的;既含道德属性,又带神经病学的内涵。
例如经前综合征,它到底是一种生理紊乱,还是一种以男性为主的精神病学家写进疾病分类学的东西,以此来应对烦躁易怒的女性患者?儿童烦躁症绝不罕见,接下来发展为多动症,然后是注意缺陷症,再接着便是注意缺陷性多动综合征。于是只能由医生开处类固醇药物利他林。这真的是精神障碍吗?或者是一种文化所要求的精神病学的产物,这种文化想把困扰父母、老师、校车司机以及其他所有群体的每一个烦恼都医学化?又如厌食症和贪食症给患者本人及其家属带来深重不幸。尽管痛苦显而易见,但我们是在谈论女性美的刻板印象——辅之以对父母的反叛精神——产生的不当行为,还是在谈论一种“真实的精神障碍”?
多重人格障碍,现在被称为分离性身份认同障碍,它困扰着5%的大学生,同时也困扰了5%的入住急症照护室的成年精神病人,它是“一种真正的精神实体,一种真正的精神障碍”,还是一种由临床医生和媒体培养出来的,表达真实深刻的不安情绪却不含医学因素的自我放纵方式?
我们是否应认真对待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或间歇性暴怒障碍,将大量暴力犯罪归咎于这些精神病学意义上的实体?或者说我们是否应该将其看作法医学的组成部分——司法和医学合谋定义并控制犯罪因子,却始终掩盖作为犯罪关键因素的系统性匮乏?
不仅仅是过去的神经官能症这一指称的真实性遭到质疑。精神分裂症,确切说是“精神分裂症人群”的概念亦是如此,它于20世纪头十年在瑞士被首次提出。相关诊断曾风行一时,但此后其影响力却日渐消散。这不仅是因为代际更新的精神药物使相关症状得到了极大的缓解,而且是因为在很多医疗司法辖区内实际诊断的比例也在明显下降。大多数试图帮助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病医生都将其视为一种可怕的疾病,它对年轻人造成的袭扰尤甚,不仅击垮了患者,还殃及其亲朋好友。然而,却总有人一再辩称,此类病症并不是一种真实存在,而是一种“科学错觉”。诚然,症状表现呈多样性,但20世纪不同年代出现的症状集合也不相同,且尚不能找到这些症状产生的确切医学证据。

路德维希 ·维特根斯坦认为,心理学中存在各种实验方法,也存在概念上的混淆。与之相比,我们如今有更多治疗精神疾病的方法。我们有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的临床方法;我们有数不清的关于精神分析方面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实例;我们有自我救助、团体救助、牧师和精神导师咨询体系;我们有流行病学和群体遗传学的统计方法;我们有生物化学、神经学、病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实验方法;我们有认知科学的理论模型;当然我们也存在概念混淆的问题。
或许,当我们掌握足够丰富的客观科学知识时,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我有其他的看法。人类所知领域确实浩如烟海,而概念上的混淆,使得新知识对于缓解苦痛无能为力。其原因多种多样,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为纯粹信仰体系的科学知识,改变着人类对于自身的思考,改变着我们拥有的诸多可能性,改变着人类如何理解并定义自我和芸芸众生。知识与人类相互作用,与日益广泛的实践活动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便产生了症状与疾病实体的社会许可性组合。
我们时常询问某些既定疾病或其表征是否真实存在,借此表达对上述那种尚未被正确认识的现象的不安之情。我最近关于多重人格的专著的第一章题目是“是真的吗? ”。我接下来写道:“我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 ”“我希望本书的各位读者,断了意欲弄清楚这个问题的念头。 ”徒劳!读者们一次次把我拉到一旁,悄悄问我到底相信什么,多重人格到底是真是假?
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对多重人格症持有一种特殊怀疑态度。提问者希望我心怀善意(或者确切说,站在善意的一侧),他们会希望我说确实有这样一种疾病,症状要描述准确,同时要抱有深切同情心;或者他们会希望我说没有这样的疾病,所描述的讽刺现象是“社会建构”的一部分;或者是医生造成的“医源性”疾病,以及由治疗者和媒体巧手制造的一种信仰体系下的“病症”。
人们会不断使用与有争议的精神问题相关的词汇,例如“真实”及其近义词“真正”。原因多样,从财务到责任,从语义理论到科学形而上学。健康保险应该只为真实的精神疾病付费,难道不对吗?我们对疾病有着深刻的道德态度,因此责任是关键因素。如果疾病真实发生,你不需要对此负责,或者仅当是你的堕落导致此疾病时才需要负责。性、酗酒、懒惰是典型的堕落之源。但是,如果你打篮球的习惯从少年时代持续到中年,却导致昂贵的髋关节置换手术时,你不会受到责备或承担责任。这是因为在我们的世界里,坚持进行年轻时的运动是一种美德。在精神疾病领域,如果疾病真实存在,责任可以减轻或完全免除。真实疾病有着客观的、区别化的指称。科学形而上学和通俗科学都要求被指称物是生物化学的、神经学的、有机体的以及某些囿于身体里的东西,原则上可以在实验室里被分离出来。
我认为,关于最重要的概念的阐释,存在难以解决的困难。因为它们产生于我们思想深处,存在于一些根本不连贯的内在组织中,而我们不会放弃它们,因为它们对我们的思考方式至关重要。真实性和责任感,如同文献、科学和身体,都是组织概念的绝佳典型。纵使分析和激辩再多,也无法使深层次的困惑消逝蒸发。但我们并非完全无能为力。一种方法是详细审视某可控范围内的病例,在该病例中造成困惑的诸多因素显而易见。那么,让我们一起走进阿尔贝的故事,走进19世纪90年代的“神游流行症”……
作者:[加拿大]伊恩·哈金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