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法国的美好年代,和平与快乐的经典之地,艺术与上流社会的最后一次繁荣。他既是法国现代妇科医学的先驱,也是周旋于众多情人间的“爱情灵药”,作为疯狂岁月的难得清醒之人,塞缪尔·波齐医生会选择怎样度过一生?
英国文坛巨匠、布克奖得主朱利安·巴恩斯的全新非虚构力作《穿红外套的男子:妇科医生波齐与19世纪末的法国》,以波齐医生无处不在的人生为线索,串联起一战前巴黎美好年代的一众风流人物,重现了那段优雅、暴力、歇斯底里、腐朽与自恋共存的魅力时光,同时也讲述了波齐医生在妇科领域做出的卓越成就。媒体评价说,该书“集历史、传记和哲学于一身,引人入胜。巴恩斯是一个理想的向导,带领我们愉快地漫步在美好时代的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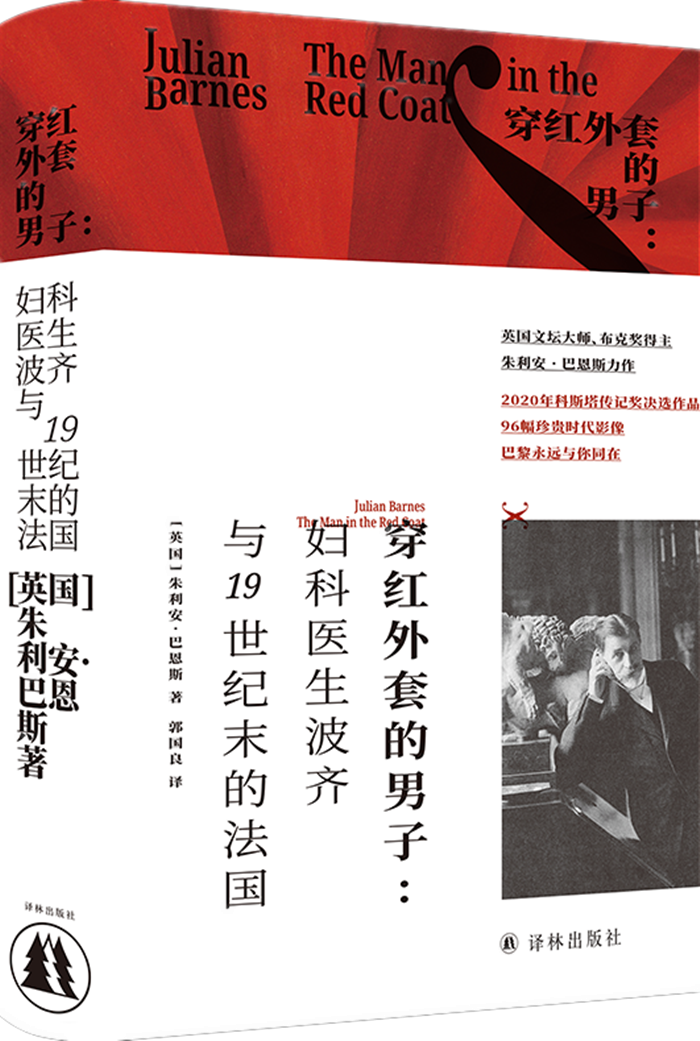
《穿红外套的男子:妇科医生波齐与19世纪末的法国》
[英] 朱利安·巴恩斯 著
郭国良 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身着那件红色长袍的交际医生
1885年6月,三个法国人抵达伦敦。一个是王子,一个是伯爵,还有一个是带意大利姓氏的平民。伯爵后来称这是一趟“智识与美学的购物之旅”。
或许,我们可以从前一年夏天的巴黎说起,那时奥斯卡·王尔德和康斯坦丝·王尔德还在度蜜月。奥斯卡在读一本刚出版的法国小说,尽管在度蜜月,他还是兴致勃勃地频频接受记者的采访。
或许,我们可以从一颗子弹和开火的那杆枪说起。通常的套路:戏剧的一条铁律是,如果第一幕中有杆枪,那最后一幕它一定开火。可是,是哪杆枪,哪颗子弹呢?当时有很多杆枪,很多颗子弹。
也许,我们甚至可以从 1809年大西洋彼岸的肯塔基州说起,那时伊弗雷姆·麦克道尔,一个父母从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来的医生,给简·克劳福德动手术,切除她有15升囊液的卵巢囊肿。至少,故事的这一脉有个圆满的结局。
然后画面就是一个男人躺在布洛涅河畔的自己的床上——或许他的妻子就在身旁,或许他独自一人——不知如何是好。不,这样说并不十分准确:他知道该做什么,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或者是否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
或许,我们可以从那件平淡无奇的长袍开始。如果称它是晨衣,可能听上去就不会这么普通。它呈红色——更确切地说,呈猩红色——很长,从脖子直抵脚踝,手腕和领口处可看到些许白色褶皱亚麻布。画面的最下方,是一只带有黄蓝光影的锦缎拖鞋。
从长袍开始,而不是从身着长袍的人开始,这是否不公平?但是这件长袍,或者说,我们对这件长袍的描述,就是我们今天对他的记忆,如果我们还能记得他的话。对此,他会有什么感触呢?会觉得如释重负,觉得有趣,还是觉得有点受辱?这取决于我们时至今日如何解读他的个性。
不过他的长袍让我们想起另一件长袍,是同一位画家画的。它裹在一个英俊的年轻人身上,他出身名门——或至少显赫。然而,尽管这位年轻人站在当时最著名的肖像画家面前,但他并不快乐。当时天气和煦,而他被要求穿上一件厚重的粗花呢长袍,一件完全不属于这个季节的长袍。他向画家抱怨这样的安排,画家却回答说——我们只知道他说的话语,但无法判断他的口吻到底是温和的揶揄、专业的命令,还是盛气凌人的轻蔑——“主角不是你,而是这件长袍。”的确,就像红色晨衣一样,人们对这件长袍比对那个年轻人印象更深刻。艺术超越个人奇想、家族尊严、社会正统;艺术永远偕时间同行。
好,那就让我们继续讨论这一有形、具体、日常的红色长袍。因为当初我就是这样首次邂逅这幅画以及画中人的:2015年,此画从美国被租借而来,悬挂在伦敦国家肖像美术馆。我刚才称之为晨衣,这也不完全正确。他里面没穿睡衣,除非那些花边袖口和衣领是睡衣的一部分,但这似乎不太可能。或许,我们不妨称之为“日衣”?它的主人几乎刚刚下床。我们知道这幅画是在临近中午的时候画的,画完后画家和画中的主人公共进了午餐;我们还知道,主人公的妻子对画家的巨大胃口惊愕不已。我们知道主人公是在家里,画的标题已告诉我们这一点。“家”用较深的红色来表现:勃艮第的背景衬托出中心的猩红色;用一个环把厚重的窗帘系在后面;此外,还有一层不同的布料,所有的布料都融入同样酒红色的地板,没有任何明显的分界线。这一切都极具戏剧性:不仅在姿势上,而且在绘画风格上都透着凛凛霸气。

▲《在家中的波齐医生》 约翰·辛格·萨金特 (1881)
这幅画是在伦敦之旅四年之前画的。画中人——意大利姓氏的平民——年方35,英俊,蓄着胡子,目光自信地越过我们的右肩。他颇有男子气概,但身材细挑。逐渐地,当我们满以为“画的主角是长袍”之后,我们的第一印象开始改变,才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画的主角是双手。他的左手放在胯部,右手放在胸前。手指是整幅肖像中最具表现力的部分。每根手指都展示着不同形态:完全伸展,半弯曲,完全弯曲。如果让我们凭空猜测此人的职业,我们可能会认为他是个钢琴大师。
右手放在胸前,左手放在胯部。或许比这更具启发性:右手放在心口,左手放在腰间。这是画家精心设计的吗?三年后,他画了一幅名媛的肖像,在沙龙上弄得声名狼藉。(美好年代的巴黎会震惊吗?当然。它或许和伦敦一样虚伪。)右手在把玩一个貌似扣绳的东西。左手钩住长袍双股腰带中的一股,与背景中的窗帘环相呼应。视线顺着它们直抵一个复杂的结,结上悬挂着一对羽毛般毛茸茸的流苏,流苏上下交叠,正好挂在腹股沟以下,就像猩红色牛鞭。这是画家精心设计的吗?谁知道呢?他没有留下任何解释。但他是一位机灵又了不起的画家;一位了不起的画家并不害怕引发争议,甚至这正合了他的心意。
画中的这一姿势既高贵又豪迈,但这双手却使它显得更为微妙而复杂。事实证明,这不是钢琴家的手,而是医生,一位外科医生、妇科医生的手。
而那猩红色牛鞭呢?一切恰如其分。
好,就这么着,让我们从1885年夏天那趟伦敦之旅开始说吧。
王子是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
伯爵是罗贝尔·德·孟德斯鸠-费赞萨克。
意大利姓氏的平民是塞缪尔·让·波齐医生。
他们这趟智识购物之旅的第一站是在水晶宫举办的亨德尔音乐节,在那里他们欣赏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纪念这位作曲家诞辰两百周年。波利尼亚克说:“这场表演影响巨大。四千多人热情参与了这场庆典。”
三个购物者也带来了一封约翰·辛格·萨金特的介绍信,他是《在家中的波齐医生》那幅画的作者。这封信是写给亨利·詹姆斯的,1882年他在皇家学院看过这幅画,多年后的1913年,詹姆斯70岁时,萨金特画了一幅他的肖像画,笔法炉火纯青。信是这样开头的:
亲爱的詹姆斯 :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对您而言,在伦敦偶识一位法国人并非一件令人不快的消遣,于是我就斗胆给了我的两个朋友一张您的名片。一位是波齐医生,那位穿着红色长袍(并不总是)的人,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另一位是独一无二、超出人类之外的孟德斯鸠。
奇怪的是,这是萨金特写给詹姆斯且留存下来的唯一的一封信。画家似乎不知道波利尼亚克也是这个团体的一员,而波利尼亚克的加入肯定会使亨利·詹姆斯兴高采烈。或许也不一定。普鲁斯特曾说,王子就像“一间废弃的地牢被改建成了一座图书馆”。
当时波齐38岁,孟德斯鸠30岁,詹姆斯42岁,波利尼亚克51岁。
此前两个月,詹姆斯一直租住在汉普斯特德荒原上的一间小屋里,正准备返回伯恩茅斯,于是推迟了离开的计划。1885年7月2日和3日,他花了两天时间招待这三位法国人,这位小说家后来打趣道,他们“渴望看到伦敦的唯美主义”。
詹姆斯的传记作者利昂·埃德尔将波齐形容为“一位交际生、藏书家和有教养的健谈者”。谈话并未记载下来,藏书早已散落各地,只留下“交际医生”这个名号。身着那件红色长袍(并不总是)的交际医生。
作者:[英] 朱利安·巴恩斯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