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居室求学(十八)
3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在西长安街的宿舍里,我一口气读完《三松堂自序》,马上拿起毛笔,在书尾写下“寻找安身立命处”几个字。当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读书感受?说来话长,以后当详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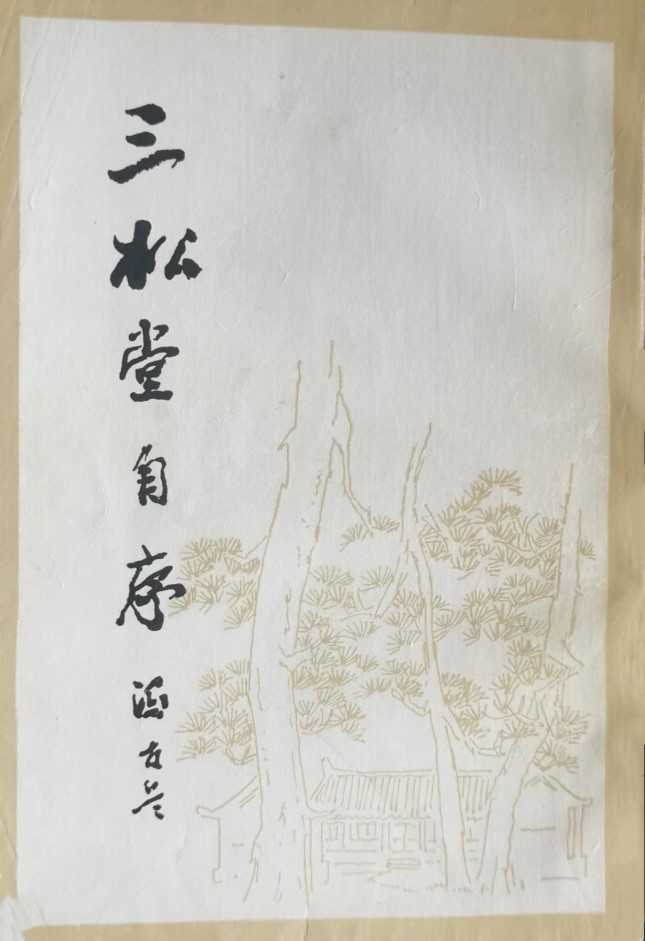
冯友兰先生的这部自传,随我30年,长在身边;完整、片段地读过无数次。读书时虽时有会心,却没想到过幽默和冯先生有什么关系;因为表面上看冯先生长鬤飘飘,仙风道骨,不苟言笑。近年独处陋室,闭目反刍,脑子里在重温读过的书,突然发现冯先生是个富于幽默感且对幽默能够欣赏的智者。
当年留美回国时取道欧洲,冯友兰顺便去苏联,观察那里的新变化。回国后,他应邀去几个学校演讲,讲他看到的社会主义的苏联。那时,讲社会主义和苏联,有“宣传赤化”之罪。1934年,他果然因言获罪,被警察局带走。带到局子里时,警察文书是一收条 ,叫“收到冯友兰一名口”。当然,名、口都是数量词,这样写也不错,但这个收条的表述,反映了旧时代对人、对大学教授的态度。冯先生到老还记得收条的几个字,是以幽默的口气讲的。
在《三松堂自序》里 ,冯友兰还回忆他特别欣赏的一句话,他说他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谈教会学校的文章,其中有一句是:“有人说教会学校也出了些人才,我说这些人才并不是因为受了教会学校的教育而成为人才,而是虽然受了教会学校的教育也还是人才。”这个幽默,是逻辑思维的肯定和否定,冯友兰到老还在欣赏这些高级笑话,说明他是个懂得妙赏的哲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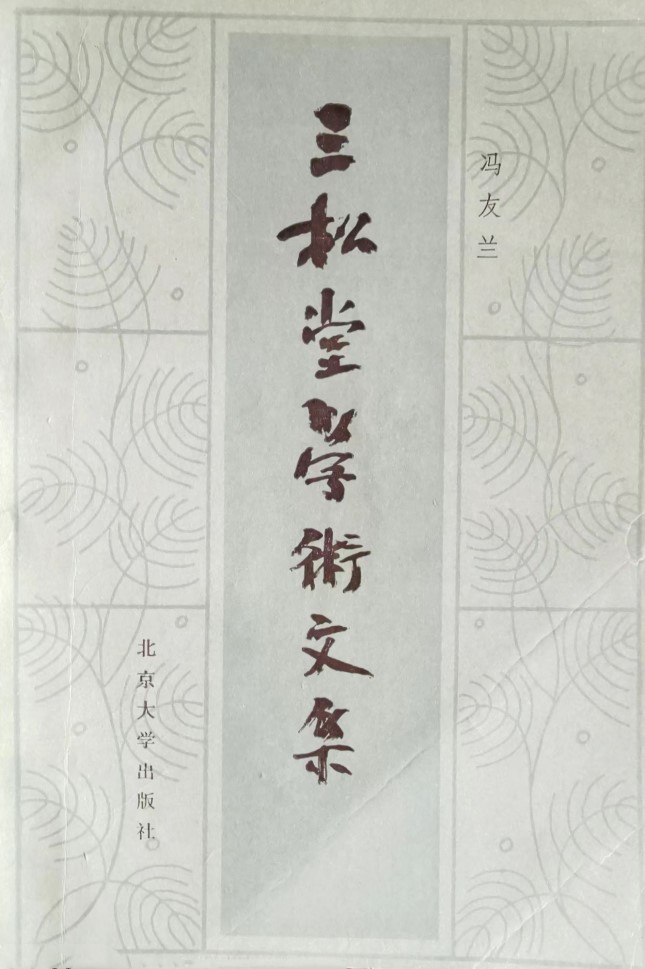
学外语,我们知道有个口型问题,没想过学汉语也有个口型问题。冯先生讲过一个笑话,我现在想来,实质上他说的是汉语发音,但以笑话表之。冯先生说:
有一女郎,嫌自己门牙太暴突,长得不好,准备镶金牙,把门牙拔了。碰巧有人上门,她要答话;为掩饰答话时露风,就用“合口音”的字:
贵姓?
姓胡。
住哪儿?
保府。
多大了?
十五。
贵庚?
属虎。
贵干?
唱大鼓。
等女郎的门牙镶好,为了向人显示,再回答他人问话就用“齐齿音”:
贵姓?
姓李。
尊住?
京西。
岁数?
十七。
贵庚?
属鸡。
贵干?
唱戏。
冯先生一肚子学问。在他那睿智的头脑里,除了千年的中国思想,还有这些轻松的笑话。这个笑话,是在工作间隙,他亲口跟身边人讲的。
我最喜读冯先生的一篇文章《论风流》。他从《世说新语》入手,对风流定义:第一,真名士,真风流的人,必有玄心;第二,真风流的人,必须有洞见;第三,真风流的人,必须有妙赏,所谓妙赏就是对美的深切的感觉。风流是一种美。冯先生讲笑话,就是妙赏。在《三松堂自序》里,他回忆辜鸿铭在北大讲课,对新词语咬文嚼字,表明他对新事物的不满。辜在课堂上摔着长辫子,很生气地说:改良?你要改良为娼吗?先前说王法,王、法(停顿,高声,拍桌子)!谁不害怕?现而今说什么“法律”(低声),谁还怕?冯友兰在回忆辜的逸事时 ,用写话剧剧本的格式,详细记下了辜当时的表情,我在百年后阅读,还能感受冯友兰的幽默。
晚年,冯友兰视力下降,几近失明。他的回忆录,除“哲学”部分是先前自己亲手写的外,其他全是口述,由助手记录整理。冯先生这一代人,真正亲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记个人史,同时也是记中国史。在西南联大时,他痛遭母逝,接到丧报,就和弟弟冯景兰自昆明坐飞机到重庆,又在重庆坐船出三峡,在宜昌上岸,爬山涉水,过老河口,最后回到唐河,为母亲治丧。我曾在地图上细看他们兄弟当年携手回家哭母的路线,深深感到当时的行路难。“漂泊西南天地间”,是唐朝人在安史之乱后的遭际,也是民国人在国难时的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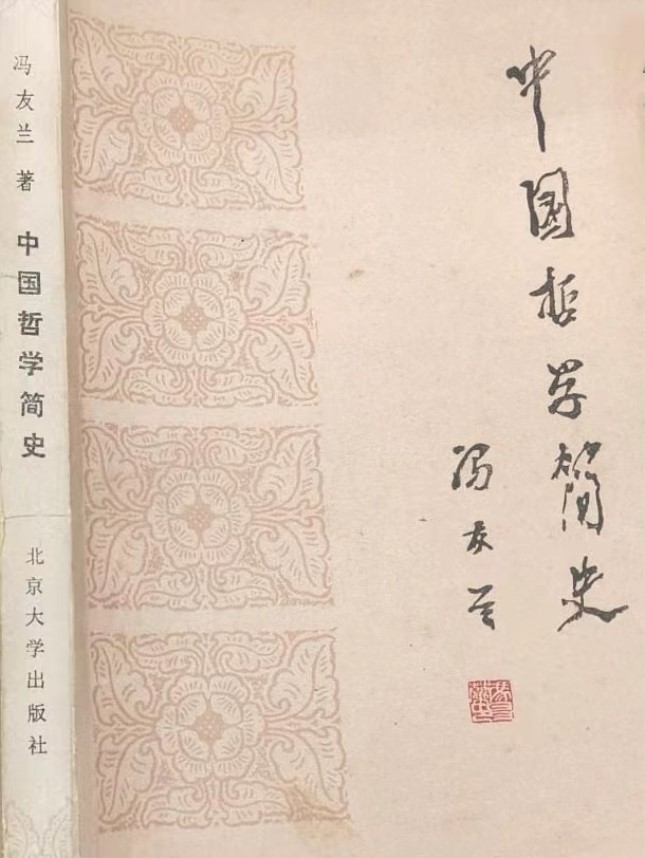
《三松堂自序》和涂又光先生翻译的冯著《中国哲学简史》,是我常读的经典。《简史》还有几种译本,我比较过赵译和涂译的风格,感到赵译在个别地方更精确,但涂译更能体现冯著“气足而不怒张”的文章风格。碰到熟悉的青年朋友,我就积极向他们推荐这两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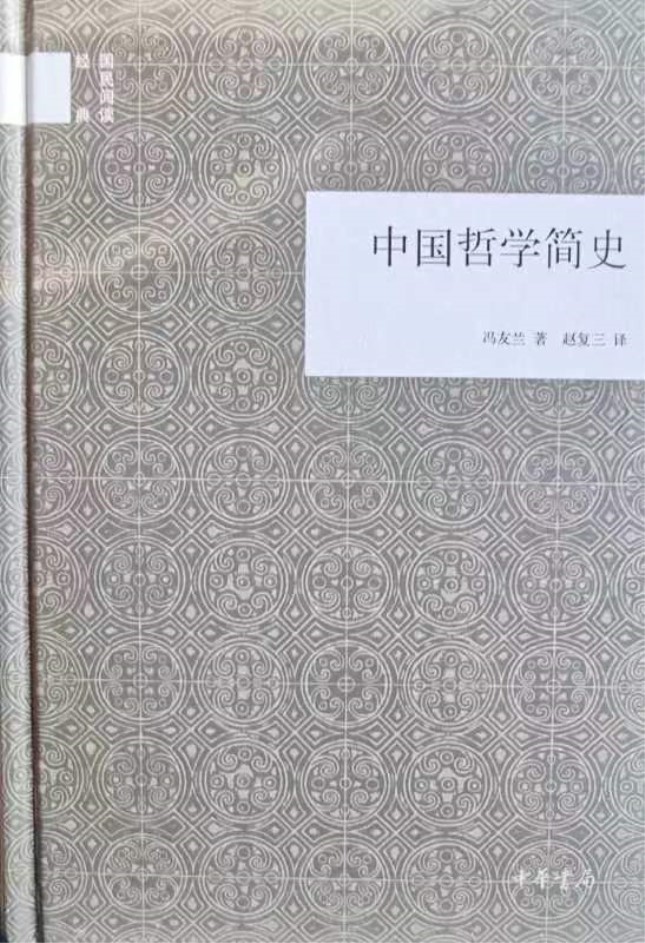
冯友兰在燕南园的旧居,北大挂牌列为故居开放,校方还举行了一个挂牌仪式,证明学校当局重视著名教授身后事。去年夏天去燕南园,看见那个又长又宽,跟三松堂抢戏的牌匾,我就想对校方建议:燕南园的这十几座别墅宜统筹考虑,保持原貌,将来给每一栋楼都钉一个小铁牌,牌子上注明谁人旧居,雕刻一个头像,这就行了。现在冯先生旧居门口高悬的牌匾尺寸太大,喧宾夺主。
>>作者简介:
卫建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著有散文随笔集《寻找丹枫阁》《陈谷集》等。
作者:卫建民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