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流到了今天,与任何一段河流都不一样,生命的河流、文明的河流、历史的河流,都是新的,写出个人,写出自己,写出时间河流里的“这一段”,才有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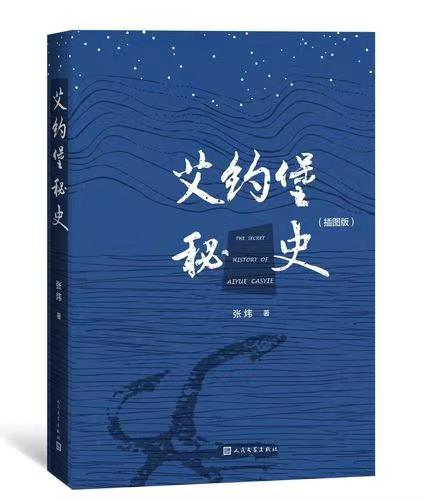
我从十几岁尝试写“儿童文学”,前前后后写了许多,积累到后来竟然也有了上百万字。它们非但没有令我满意,而且让我苦恼。一度想放弃写作,文字的经营是很难的。一开始写作,自己也是少年,那时候总觉得自己在为同年龄段的人,为身边熟悉的伙伴在写作。这等于是一种相互转达和倾诉的需求,有特别的愉快。就这样形成了一种口吻、一种语调,它是我的开始,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写作:有一部分特质最终保存和延续下来了。这也许很重要,儿童文学的写作对我来说既是一种起步,又是一种延续和一个基础。

设身处地讲故事是一个好习惯
我认为设身处地讲述各种故事是一个好习惯,像儿童那样单纯地感受和表达,可能更加质朴和生动。回顾自己的文字生涯,最初的写作训练非常辛苦,也充满了乐趣。用文学的形式表达自己,述说内心,将所思所见描绘出来,这种创造性的工作极具挑战性,也是最新鲜的生命体验。这些构成了深刻的刺激,所以一旦进入文字语言的世界,就再也不能放弃不能遗忘了,那是充满感激的记忆。没有那些日子的欣悦和煎熬,也许现在的写作早就坚持不下去了。
记得最早的书写内容,包括了我熟悉的身边生活,特别是那种在自然环境中发生的故事。最难忘的是这其中有许多“恐惧”:儿童对大自然中一切未知的惧怕,特别是对陌生的事物,主要是对人的惧怕。那里地广人稀,丛林茂密,人是很少的,幼小的我对偶尔见到的人,特别是那些猎人,常常感到害怕之极。努力克服这种胆怯,讲出一个个故事,就是我当时做的事情。孩子是欢乐的无忧无虑的纯洁的,一般人都这样看待儿童,其实在我看来不是那么回事。我认为令人惧怕的东西也有不少,除了人,还有林子里的传说。我知道自己认识的这个世界太小了,从未见过的那个世界太大了,那里隐藏的东西更加神秘莫测。
虽然有恐惧的打扰,我的写作还在继续,相诉不曾停止。书写眼前或回忆以往,都是战胜和振作的过程。人如果屈服了,生活也就更加无望。这时候讲述的不是一个故事,也不是一个主人公,而是一束故事和许多角色。因为太多的人与事,就像翻开了一本厚厚的记事簿,打开了长长的流水账。作为一个上年纪的人,他的回忆文字,要变成活泼的儿童故事,要花一番心思,一般意义上的儿童文学的笔调是不适用的。文学就是文学,儿童文学当然不能是一个例外。

如果孩子喜欢看,那么就是“儿童文学”了,成人觉得有趣可读,那就是成人文学了。当一个少年写作者长成了中老年,写作的时候就会提醒自己正在给孩子讲故事。这种提醒既很重要,不可忽略,同时又极可能限制了自己。他的讲述一旦拿腔拿调,用人们特别熟悉的那种“儿童”腔调,也会十分蹩脚。实际上所有好的“儿童文学”,都没有那种特殊的“发音”和“气味”,那严格来讲只能是另一种套话。凡讲套话都不让人喜欢,顶多只会是二三流的。安徒生和马克·吐温不讲什么套话,我们也不必讲。
所以说一个作家从小到大,写“儿童文学”也不必“改行”,他总会有一部分文字适合少年们看。人的天真是天生的,即便到了老年,也仍然能讲出少年儿童爱听的故事。老人讲给孩子听,身边围拢着他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们看到很多专门的“儿童文学”,其中有一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并不太好,因为它们拿腔拿调,是故意做出的一种幼稚天真的口吻。
现在做事情讲究专业化,仿佛越专业越好,分工越来越细,这种事是利弊互见的。文学分得这样细,什么“成人”和“儿童”,儿童又分成“幼儿”,再分成从少年到少年中间的部分,所谓的“桥梁书”。写作者搞懂了这类名堂,也陷入了很大的麻烦。这成了一门“科学”,或许在一部分研究者那儿真的很重要,但是到了作家这里就不妙了,他要想着自己正干的活儿是不是符合行规,要考虑那些细密的、讲也讲不完的门道或禁忌。专业性的恐惧就开始侵蚀他自由自在的心灵了。技术性专业性会让他缩手缩脚:文学给分割成一块一块,每个人只携起自己那一块回家,专门家也就产生了。不过这样的专门家往往并不是文学家,而常常是熟练的制造文字读物的技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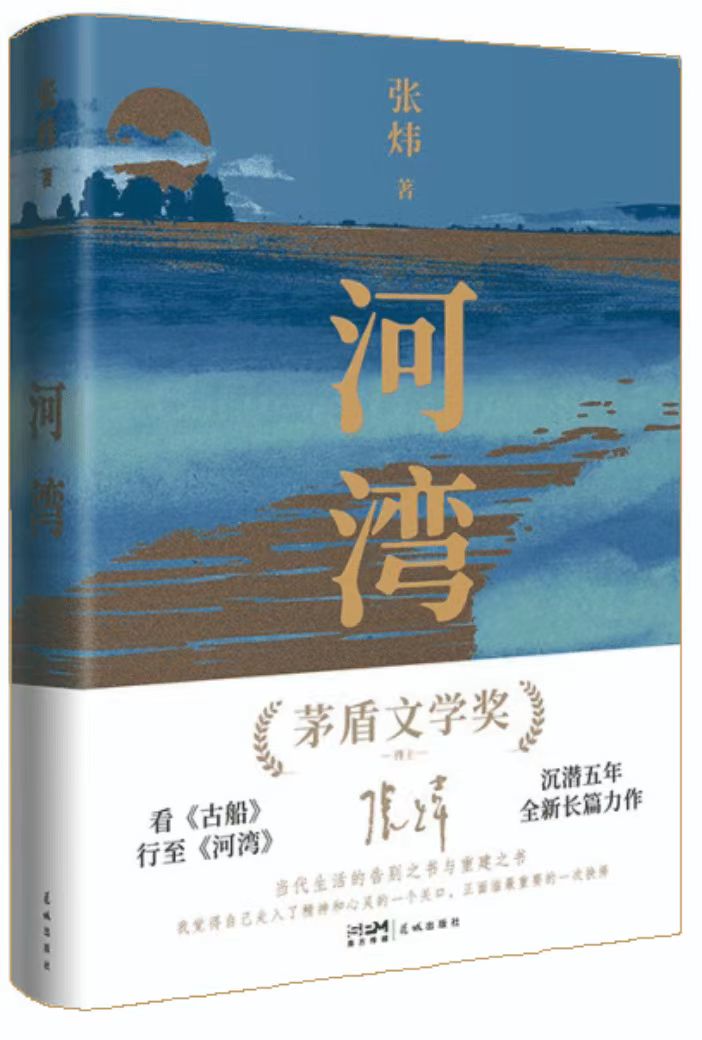
最难处理的问题是文学的深度
我非常警惕随着年龄增长而带来的“专业化的恐惧”。沾染上胆怯的粉末,就很难揩掉。特别像作家的“作家”,特别像诗人的“诗人”,总让人持怀疑的态度。同样对特别像儿童文学的“文学”,也要保持距离。文学哪有这样复杂,又哪有这样简单。我以前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去,当地人告诉我:“十年前这里来了一个作家,所以我们很熟悉你们这种人。”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稍有不解和苦恼,说我不像一个“作家”,我听了很高兴。“作家”没有固定的举止和形貌,也不该有固定的语言方式。有的“作家”“诗人”到了一个地方,遇到什么事情突然就激动了,结果吓人一跳。这虽然能够让人过目不忘,但总是不太好。“儿童文学”也是同样的道理。马克吐温和安徒生的这类文字,就不太有我们时下的这种专门分工的气味。在我看来,恰恰这才是真正的、好的“儿童文学”。时下有一些“儿童文学”,很可能并不是什么文学,而是写给儿童的各种“读物”,因为这个市场很大。当然这类读物如果写得好,也是需要的。
无论写怎样的题材和体裁,都不能拿捏出专门的腔调,不能追求那种专有的“气息”;还是要放松,要沉入到自己的生命品质里去,这才有可能创造出个人的世界。有些气味我们太熟悉了,一看就知道是“儿童文学”,没有办法,对某些写作者来说,不捏着鼻子就不会说话。半岛地区有个笑话,说的是这样一件事:有个孩子看到自家的一头小牛掉到了井里,惊恐万分地跑回家告诉父亲,因为结巴,越焦急越说不成句子。父亲急中生智,让他“唱着说”,并且哼出一个现成的调子。孩子跟上唱起来,很快就把整个事情唱明白了。这里说到的某些“儿童文学”,其实也是一样的。文学的结巴往往也需要一个现成的调子,不然就无法开口。这里的“调子”,就是我们都熟悉的那种流行腔。这怎么会产生杰作?所以我们要警惕自己。这也是一种专业性的“惧怕”。
我们熟悉的这类问题大致是一样的。“儿童文学”许多时候和“生态文学”差不多,倡导爱“自然”,爱“儿童”,这永远不会错。关心这个领域,呼吁和投入,再大的热情都不为过。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也会隐含极大的危险。一个写作者进入这些领域,似乎是获得了无需太费心思的一种主题、一种观念、一种立场、一种视角,其实这种题材和方向,很容易让人进入概念化的表述,要怀着更大的谨慎和惧怕才对。

我少年时代写儿童文学,与现在的不同是什么?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个行当的特别禁忌,没有那么多同一曲调的合唱。我只是在一个地方自己哼唱,尽管不成调子也不太动听,但却是原生的、自发的、自我的。现在就不行了,专业知识多了,合唱之声响亮,想要不跟着走都很难。所以有时候要写一部新作品,我总是迟迟下不了笔。多少人在写猫,多少人在写爱,多少人在写人和动物的那种情感。这种“极容易写”的东西实在是太难了。我会不会在这个题材上犯错误?因为这里面有许多陷阱。
所谓的自然生态、人和动物、儿童文学,这一类写作要超越新闻和公文的观念化的表述并不容易。我们的作品比那些成套的文字讲出了更多吗?我们不过是用一种通用的腔调,做了再次的堆积和重复。将文学的套话说个不休,是很无聊的。严重一点讲,这是一种文学的自戕行为。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流到了今天,与任何一段河流都不一样,生命的河流、文明的河流、历史的河流,都是新的,写出个人,写出自己,写出时间河流里的“这一段”,才有一点意义,这其中就有动物与人的、大自然的、社会的关系。今天的人爱动物,当然不是常说的什么“生态自然观”,这里沉浸和弥漫的是特有的社会空气、历史空气和文化空气,需要特别的文明的“解码”。为什么在一个个特别可爱的动物面前,人表现得那么胆怯?人真的需要这样懦弱吗?人在它们面前表现出来真实的恐惧,这种“恐惧”需要用“爱”去覆盖,需要去倾尽全力说服自己。因为说到底人还得活下去,为什么要更好地活下去?要回答又不能是大词,一旦把它具体化了,那真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它的难度就在这儿。儿童文学中一定会写到“恐惧”,无论作者愿意还是不愿意。这里的“恐惧”,是最大最难处理的问题,要进入它应有的深度,这是文学的深度,要触及人性和人生的这个层面。

“爱力”在作家的生命里就和炉火一样
生命中巨大的、永远难以消除的不安全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且会在各种生活形态下一直存在下去。如何表现和表达却是很难的。天灾人祸,美与丑的对峙,都会带来“恐惧”。处理“儿童文学”中的“恐惧”,是一个大的命题。这里超出了直接写恐惧故事的意思,而是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任何事物都是两极相通的,在浓浓的爱的里写恨,写“恐惧”,在“恐惧”中大声吟唱,这如同在浓浓的夜色里、在呼叫的北风里讲述春天一样,是极有魅力的。
去年春节我回海边,遇到一个人戴着“撸头帽”,海边的风特别大,这种帽子一撸下来,只露着眼睛和嘴巴,要不人就冻得受不了。他见到我就把帽子卷起来,我认出这是初中时候的一个同学。关键是,他就是我们当年一起从事文学写作的少年挚友。他让我想起了当年对文学的酷爱,我们的执着与奋斗。我好像突然发现自己早就不年轻了,已经写了这么久。持续下去的力量在哪里?活着就有爱,却不能有太多的幻想。我们需要把爱一点一点表达出来,强化自身的“爱力”。“爱力”,它在生命里边就和炉火一样,要不停地往里填柴。“爱力”这个东西不是虚幻的,不是套话,它具体存在于个人的写作和生活中。
作家应该是一座活火山,要喷发几十年,需要很大的张力。“爱力”决定喷发力、喷发的频率。有的火山过几年喷发一次,因为内在张力在积蓄,一到了临界点就会喷发。
作者:张炜(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
编辑:王雪瑛
策划:王雪瑛
责任编辑:邵岭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