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一套真正称得上是图文并茂的“永玉三记”。“三记”依次是:《罐斋杂记》《力求严肃认真思考的札记》《芥末居杂记》。这套别具一格的奇书刚在书市流通,就使知识界人士产生浓厚的兴趣。
一部有生命力的书,自会像清泉甘露一样渗入读者的心田,不必赖什么“权威”来鼓吹。
事隔八年,已“乘槎浮于海”的黄永玉先生,又在“古椿书屋”刊行了四记、五记、六记。依次排列,新三记的书名是:《往日,故乡的情话》《汗珠里的沙漠》《斗室的散步》。新三记的封面,分别是三种不同纹理的油画框样,印制精美绝伦;才刚上眼,就令人“惊艳”!——自此,黄永玉式的札记,就出到六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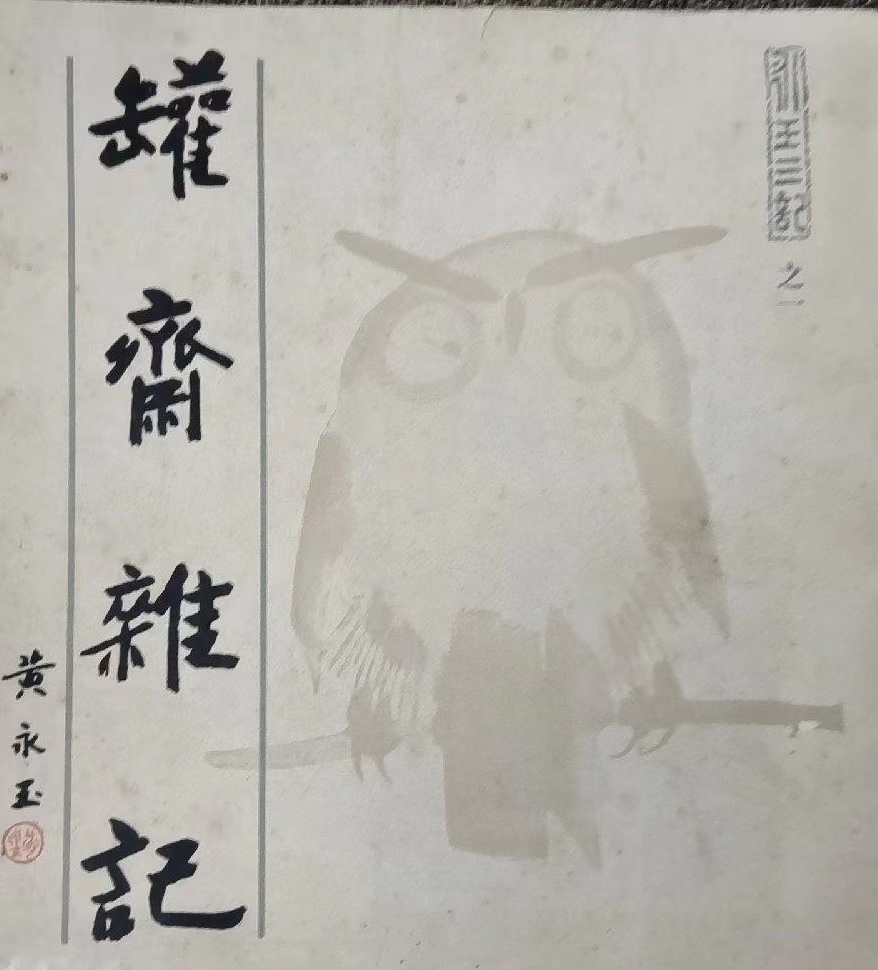
札记不是小说,没有故事的连贯性。如果说她的内在脉路“一以贯之”,那就是作者的心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果说旧三记有更多的愤世嫉俗,新三记则更多的是艺术家的深刻思考和对故国温馨的回想。高尔泰先生说过:“因为爱美,人们活得更多了。”读新三记,我强烈感受到了作者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与旧三记的又一区别是,新三记全是速写,线条流动旋转,读时眼到心随,“理出头绪”,更能感受到艺术家创作时的激情。
《往日,故乡的情话》
再差三十年,就是一世纪的浪迹天涯。故乡的闪念太多。
山水、生活,隽语,人物,情调,片断的哀乐,油然生发于朝夕。
对于朋友,我记下的这些东西不知他们喜不喜欢?明不明白?有无同感?有如泡一杯家屋山背后摘下的野茶敬客的意思,偷偷一瞥他的微笑吧!
——永玉四记
作者十几岁就离开了家乡——美丽的湘西凤凰县。但十几年在家乡的生活,竟给他一生极大的影响。作为一个人,他永远保持着湘西人的本色——淳朴、豪爽、乐观、好客、正直;作为一个艺术家,家乡的青山绿水、民情风俗,甚至空气、植物,成了他创作的源泉。他不是奉旨“体验生活”,而是自觉自愿地同生活血肉相连。在他不少的速写、油画、国画、散文中,“湘西”是永恒的主题。但你不要错以为他是地域性的艺术家。他是像宋儒说的“辞落枝叶,培植根本”。他是在与家乡的亲近中,浇灌培植自身的生命,艺术的生命。近年作画,他爱题“湘西老刁民”或“湘西刁民”这样的下款。我理解,这不是自嘲,而是保持独立人格的自白,迎对恶势力的抗议。
《往日,故乡的情话》,共117则(幅)。第一则就是作者记忆里的人声、犬声:“‘啊呜啊!啊呜啊!……’狗群顺着女人叫声跑。哪家的孩子拉屎了。”远离家国,于现代化大都市的机械声不闻,作者竟写出画出的是这样一幅旧乡村的图画!这是“生物链”,更是作者心灵的安慰。
家国远了,也更近了。作者在搜寻儿时的记忆。每一细微的声响、光点、印记,房屋的阴影。水波的皱痕,纤秀的叶脉,都从心中掠过,都能拨动心中的琴弦。
夕阳下的城垛上,苗孩子吹他的笛子哩!
秋天树叶一落,屋里宽多了。
几度夕阳红,谁能想象苗家孩子的笛子给作者留下多么高远的幽思?而叶落屋明的惊喜,分明也是我们的审美经验。家乡啊,童年啊,那才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童年就是美。
作者还记得:
哪家有人出远门或是从外地回来,都到城外五里“接官亭”去送迎。
看到这里,我的双眼湿润,仿佛听到了“长亭外,古道边……”的低回婉转,想起了自己当年初别家乡的情景。别离、还乡,是中国古典诗文里的重要内容,当然也是中国人实际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不知从何时起,这些生活内容淡了,远了,消失了。我们只能从艺术品中寻找失去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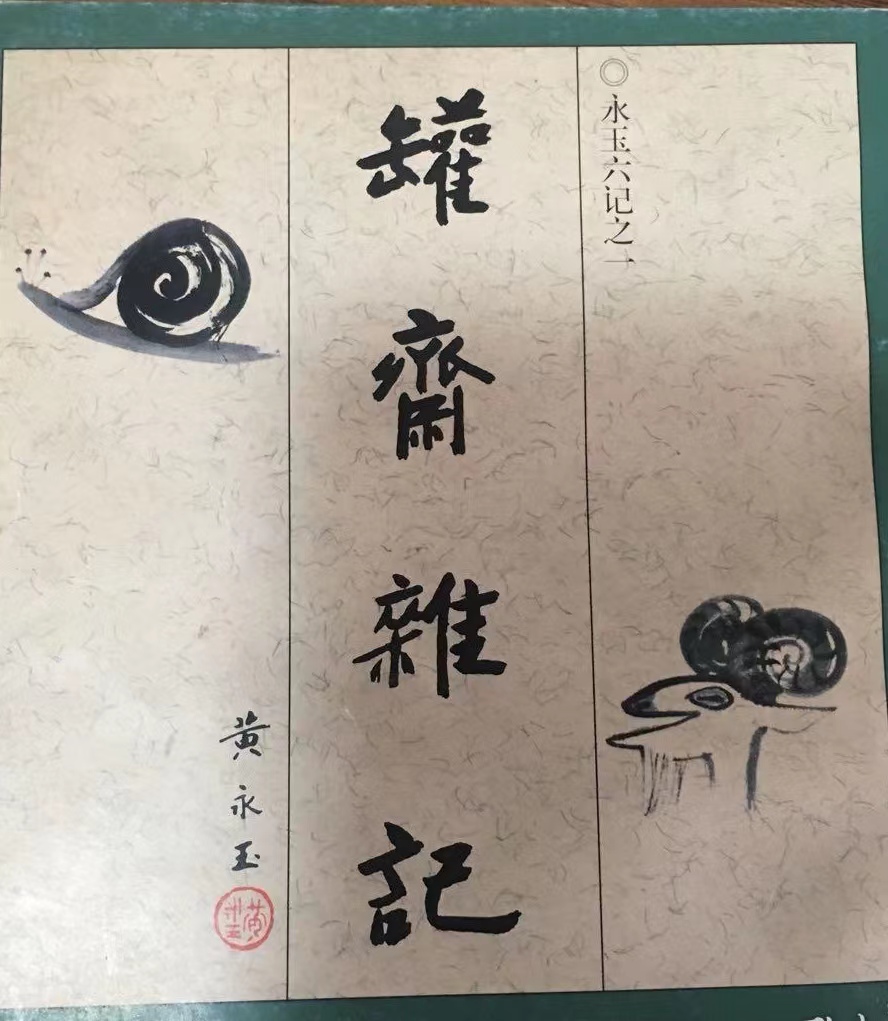
“永玉四记”记下了童年同伴的调皮,家乡异人的面孔,某次玩耍的乐趣……有一则记山村教师的文字是:
穷是师叫儿子:
“到村子口看看去,有没有学生来拜年?”
联想起今日人民教师的待遇,使人笑出了一把辛酸泪。
《汗珠里的沙漠》
一些文化艺术的札记。
不知别人是否和我一样感情的狭隘?
得意之笔只想到亲近的朋友,估计他们的喜欢。
没他们,这个世界有什么好“舞”的?
——永玉五记
这一“记”,“搞专业”的特别应该读。这是作者思想的结晶,艺术实践的真知,审美经验的记录。
看一幅好画,有如走进满堂通亮的大厅。读到这一句,我贮存在记忆里的“看画”经验马上就调动起来,像磁铁吸附起散乱的铁屑。为什么作者那灰色的、层次丰富的《起舞墨荷》,蓝色背景中的《玉兰》,以及其他国画、油画,才看一眼就为之一震,感受到一种古君子的气度?是的。许多画陈列在展厅里,每一幅杰出的作品都是一个灿烂的星座。许多雕塑陈列在展厅里,每一幅雕塑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它们在观者眼前起伏、呼吸,倾诉着艺术家的心灵之声。去年看罗丹艺术展时,我感到了这一点。看李可染画展时,我从黑色中感到了“满室通亮”。看弘一的书法时,我感受到了静定之后的明澈。
作者过去写《南沙沟札记》时,是用散文形式探讨某一艺术课题。《汗珠里的沙漠》同是谈艺,却更简洁凝炼,只用几个字、一、二句话讲谈自己的心得。这是思想成熟的标志。“真理总是朴素简洁的”。他的每一则札记,也可看作是一道命题;对艺术学徒来说,每一道命题都能作出一篇长文章。我愿意多摘录几条,以使读者更多品尝“永玉五记”的原汁原味:
把灰调子玩熟,算是懂得一点颜色了。
把感觉完美的铺开,就接近完成。
我常常专注交响乐中一二层的背景音乐,试着为图画中的背景寻找出路。
艺术家把坏脾气理解为风格,所以永远形成不了风格。
中国人懂得中国的打击乐。强弱、快慢、疏密、长短……,其实加上颜色,就是现代美术;加上西洋乐器,就是现代音乐。大家没试过而已。可以试试!
“永玉五记”共122则,都是上述隽永的短句;我已反复读过数遍。希望她能与更多的大陆读者见面,与旧三记配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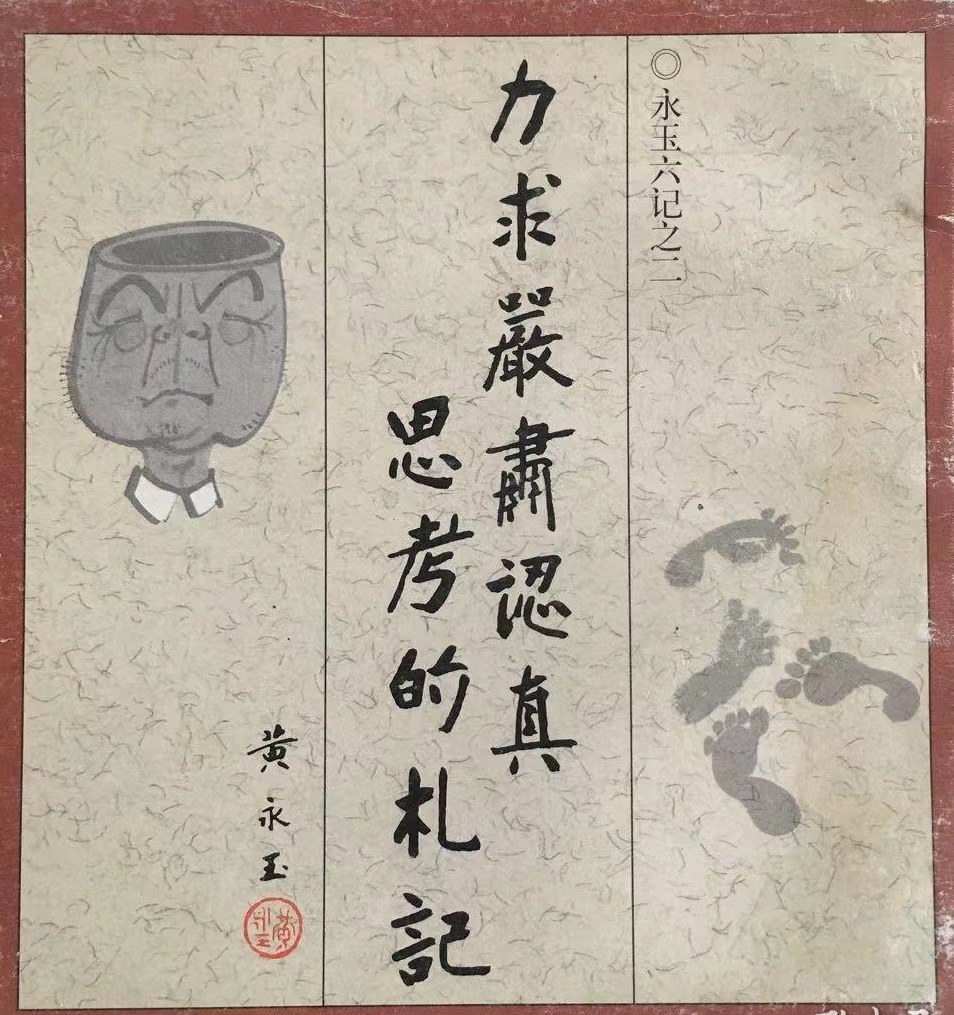
《斗室的散步》
从巴黎一路写到翡冷翠,口袋里放个本子,想到就记,像随街捡东西,像一路上跟朋友聊天,像疯子见谁骂谁。至于“斗室”这两个字,自己的局面而已。
——永玉六记
169则欧洲札记,不见一幅风光速写。人身是在异国它乡,人心却在祖国,所思所想也是苦难的土地上发生的荒唐事情。是牢骚,是关注,是批评,是不满。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也许,人人都说自己的话,社会才有活力。
报纸的“读者来信”版,只能反映“下水道堵塞”、“出租车司机斩人”一类的事,这怎么得了?
欧游路上,大概没有一个碧眼金发的旅伴能理解一个中国画家本子上写的是什么,画的是什么?
或许正是在巴黎的“圣贤祠”,在卢梭的塑像下走过时,作者想起了中国文学界的“个别现象”,于是,“想到就记”,记下一条感想:
“革命文学家”成了既得利益懒汉,怎么还能“文学”?还能“革命”?
了解文学界现状的人,都明白作者并非无的放矢。以作者之胸怀,决非攻击具体的人。而是批判一种可怕的社会现象。那种错把“文学干部”当“作家”,“作”不出受社会欢迎的作品又反过来埋怨社会的人与事,不仍是文学界的宿疾吗?
别的行当的人不敢说真话,也许被誉为“成熟老练”;艺术家若不敢讲真话,人与艺俱亡,是双重的损失。作者在旅途冥思,自由遐想,语句或失偏激,所想未必中的,但心却是真挚的。宽广雄强的土地,必能接纳消融吸收一切。
在第五记里,作者曾记下这样一条:
读万卷书,活一万个人生。
书本列队的漫漫路上,演示象征着人生的无限精神空间。我几天来“循环往复,从容含玩”(熊十力语)于黄永玉先生的新三记,沉浸在人生、艺术的甘美气息里,心头也像窗外的早春,惠风和畅,阳光明丽。
打开一本新书,就进入了一个新天地。
1994年3月8日夜
(本文原刊于1994年4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第9版)
作者:卫健民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朱自奋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